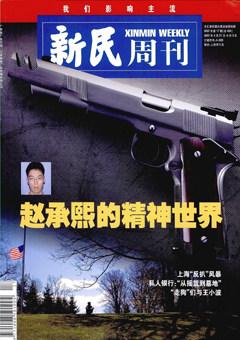“我不适合做英雄”
陈 冰

重走小波路行将结束的晚上,李银河再次面对记者谈起了王小波和她这十年。
新民周刊:十年了,不断有王小波的著作和纪念活动推出,有人戏称这是一阵风,每年都会准时刮到你身边。今年是十周年,风就格外地大。
李银河:我知道有人又在对这个活动(重走小波路)说三道四,不过我觉着挺好,来的都是一群有趣、有智慧的人。关于他的书也出得差不多了,今年还会重出一套王小波纪念册,算是告一段落吧。我总觉得小波是个文学家,不仅仅属于我,还属于很多人。
新民周刊:有不少人觉得您在利用王小波获名获利,说这是"李银河时代的王小波"。
李银河:其实生命到最后都是没有意义的。说这话的人把名利看得太重了。一位作家说过,周围人的评论就像一面镜子,你要是照了会吓一大跳,这根本不是你啊!所以对这些评价不必太在意。
但是对于小波的写作,我在其中的确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这么说,我的文学鉴赏能力是比较高的。我认识王小波的时候他就在写作,看了他的《绿毛水怪》,我就知道写作是他的宿命,他的东西不一般。他曾经说过,"自从认识你以后,我就觉得太应该做点什么了。"
1986年,王小波的哥哥王小平跟我很正式地谈过一次。他认为文学不能当饭吃。可我非常坚持,认为王小波能干这事。后来小波写的东西老发表不了,还问过我,要是我一直这样,你会怎样?我说,这样(指只要有爱情)就可以了。
新民周刊:小波生前寂寞,死后热闹。但这种热闹更多地体现在民间,主流文学界、批评界好像一直处于失语状态。
李银河:有人说王小波是横空出世,不属于哪一派,哪一流。主流的文学批评家可能找不到很合适的语言去描述和分析王小波的小说,所以他们只好不加评价。因为一个作品出来,从质感上你感到它很好,但这个很好的作品怎么去解释它,一落到具体的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里,你必须去尝试采用一种理论模型或什么的去研究,这样一说就大了,就空了,就会露怯。
新民周刊:人们一直很好奇,小说中的王二到底和王小波本人有着怎样的关联?
李银河:小说家的本事就是"无中生有"。王二和陈清扬在农场里的事王小波绝对没有。结婚时他是处男,这一点我很清楚。我认识他的二十年里,他没有情人,但不排除有人单恋他。当然,小说中的一些人和事也有真实的原型。比方说《似水流年》中有一个叫"线条"的女孩,她现实中的外号就叫"西单线条",在那个年代就敢跟男孩子一块出来玩。当年小说出版之后,她还买了几十本送人,感觉特高兴。小波去世,她还写了个挽联,上面写着"后会有期"。
新民周刊:这一两年您的言行引起了很多争议,您还会坚持下去吗?
李银河:其实我所有的观点早在十年前我的专著中就有论述,我的观点一点也不过激。我说有权利,并不代表我就支持、提倡你这么干。之所以这几年又被拿出来说,是因为一些偶然事件,比如说去年的"南京事件"。
当时也就是一学术报告会,有问有答,城里的年轻人都很赞同,有个老先生有些异议。结果到报纸上就变成了"惹众怒"。我不得不向更多的媒体解释。其实我本没有义务在公开场合宣讲我的观点,但有些事情不得不表示态度。
原来我也是比较理想主义,认为中国人的很多观念很扭曲,想传播正确的观念。但是现在存在两方面的压力。一是社会本身没有进步到这个层面,我再出来说,反而起到相反的作用。二是行政方面的压力。由于社会上反对的声音太多,相关方面很明确地让我闭嘴。我只能是犬儒主义。我不适合做英雄,这不符合我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