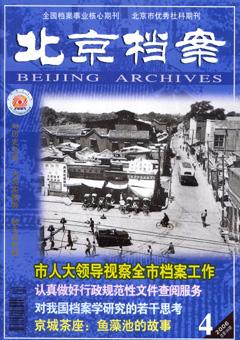营国匠意深 最美北京城
方立霏
朱祖希,笔名“左犀”,1938年生于浙江省浦江县,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毕业后长期从事城市规划和环境问题研究,现为北京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全国经济地理教学与研究会理事、北京史研究会理事、当代北京研究会理事;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北京应用文理学院客座教授。
认识朱祖希缘于春节前老先生的一封署名“左犀”的来信,信中对本刊前期刊登的一篇文章提出了质疑,编辑部辗转与他取得联系并表达了采访他的愿望。可朱老先生非常谦虚,他说自己是一般人,可以在一起探讨一些问题,但采访就免了吧,不过记者并未死心。节后的一天,朱老先生打来电话,说要去位于东直门的北京市园林局办事,顺道把他的一篇关于北京鱼藻池的稿子送到编辑部来。我劝说他把稿子寄来就行了,不用辛苦跑这一趟,老先生满不在乎地说:“没关系,骑自行车一会儿就到。”
半小时后,一位瘦高个、银发、大眼、精神矍铄、满面红光的老人出现在编辑部的门口,他就是已经68岁的朱祖希,我不由得对他的精神风貌、坦率性情和雷厉风行所折服。没有过多的寒暄,在看似随意的聊天中,我对老先生以及他对北京城的深情和研究有了些许了解。
“北京是世界上规划最美的城”
对老北京城的评价,朱祖希用了“最美”两个字。1955年,浙江省义乌中学第一届高中生、17岁的朱祖希考上了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当他挑着行李从杭州坐着长途慢车到达北京前门火车站下车时,高大巍峨的正阳门城楼给了他从视觉到心理上的双重震撼。时隔50多年后的今天,再回想那一刻,朱老先生还是忍不住要感叹:“这就是北京啊,这就是北京的气魄!大气魄!”
关于北京城的规划,朱祖希认为中轴线是它的灵魂所系、精华所在。对北京城的中轴线,朱老先生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演绎。他说:“有一次我到北京师范大学讲有关北京城规划的课,身上穿的是一件中山装。讲课的中间,有同学递了一张纸条子,说改革开放都那么多年了,您怎么还穿中山装呀?我就跟他们讲,我这身中山装其实就是北京城呀!请看这脖子下第一粒钮扣是紫禁城的午门,下一粒是端门,再下一粒是天安门,在这几粒扣子的两侧,左面是祖庙?熏右面是社稷坛,接下来的钮扣是正阳门,最后一粒扣子是永定门,在两侧则左边为天坛、右边为先农坛。”说到这儿,老先生自己哈哈乐了起来,我也不禁被他的风趣幽默给逗乐了。我猜想课堂上的学生们听他这一通解释,一定也是心中释然并欣欣然了。
朱老先生又说:“古代的规划师们通过对皇城建筑物之间的距离长短、空间大小、体量不同、形制互异进行巧妙设计,使行进在其中的人产生一种心灵感应,就是对皇权的无限崇仰和敬畏。关于北京城作为都城的规划,其中轴线的魅力及其用建筑的手段来控制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的设想和效果,还有一个更为生动的描摹,那还是当年侯仁之先生给我们上课时讲的,不过我讲起来可比老师差多了。”朱祖希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的嫡传弟子,侯先生早年间的授课和教诲至今还留在他的脑海里。“侯先生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也就是设想了中轴线的一个意境。说的是明朝时皇上召见一个县官,这个县官先从正阳门进来,高大的城楼给他一不小的震撼,进了前门,走过棋盘街?熏远远看见又大又敞亮的大明门(清时叫大清门,民国时叫中华门)。县官刚沉浸在对京城阔气的赞扬和景仰之中,大明门一过,视野忽地收缩在了两边千步廊黑压压一片高级衙门中间直通远处天安门的一溜大道上,县官的心也跟着一缩,刚刚仰着的头赶紧低了下去。好不容易来到了天安门前不大的宫廷广场,望着高大的天安门城楼他暗暗喘了口气,对京城的感慨和对皇权的敬畏在他心里来回翻腾。等进了天安门,迎面不远处又撞见端门,忐忑不安中他穿越了端门。远远看见午门在望,县官赶紧加快脚步,闷头赶路。待他紧赶慢赶来到午门跟前,再抬头一望,不由得吓一哆嗦。为什么呢?原来,周围的环境在他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巨大变化。远看平面呈“凹”字形的午门非常高大雄伟,城楼上有亭式建筑。可当你进入了这个凹形建筑,被两边伸出来的城墙包围了的时候,那种瓮中的感觉一下子就来了,不由得让人不战栗。等到战战兢兢过了午门,看见远处的太和门,县官脑子里什么也不想了,心智完全被皇权所摄。诚惶诚恐地来到太和殿,还没等看清皇上长什么样,双膝一软,先跪那儿了。”一口气不厌其烦地说了这么多,朱老先生若有所思地叹了口气,说:“这当然是封建等级制和皇权至上思想所致,但它也说明了建城者为封建等级服务的艺术之高超。今天我们欣赏北京城的中轴线和紫禁城当然不能从这方面去看待,但它作为一种建筑文化在封建时代的作用是我们应该了解和正视的。另外,也还有人从音乐角度去体认这条中轴线,感受到它当中的交响乐韵律,有序曲,有高潮,也有尾声。”
“整体规划的北京需整体保护”
朱祖希认为,老北京城的规划特别注重整体效果,整个北京城的平面布局由紫禁城、皇城、内城、外城层层拱卫,紫禁城是金碧辉煌的,四周的四合院民居是清灰色的;皇城是高大的,老百姓的房子是低平的。朱老先生说:“虽然这反映了强大森严的封建等级制,但从实际的观感上来说又是高低有致,达到建筑群落的一种和谐美。正因为有了灰色四合院的淡然平静,才更衬托出皇城的雄浑灿烂,才构成一幅有情致的图画。它所体现的其实就是红花更要绿叶扶的朴素道理。”
可现在谁都知道,整体的北京城早就不存在了,就是仅存下来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古建筑、四合院和历史保护街区,也在不断地受到来自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和房地产开发商的推土机的威胁。历史是不能重来的,朱祖希说:“现在我们好不容易划出的4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还有故宫北部的一大片缓冲区,那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回忆起北京城墙的被拆除,朱老先生还是十分痛心。那些年正是他在北大求学的时代,他说侯先生并没有过多地在课堂上谈论这件事,校园内的有关争论也比较少。尽管侯先生与梁思成是挚友,但朱祖希从来没见过梁先生,崇敬之意却一直在心。朱祖希说:“梁思成先生是了不起的建筑学家!可惜当年没人能理解他。”朱老先生还告诉我,1974年当他还在北京市规划局工作时,曾接待过一个瑞典城市考察团,在参观完规划局制作的北京城市发展新旧对比图片和介绍后,瑞典代表团的团长满怀狐疑地问他们:“北京城墙是谁让拆的?”规划局的一位领导说:“是上级让拆的。”人家又问:“是哪个上级?”领导回答说:“是上级的上级。”瑞典人一看问不下去了,就说:“你们不要以为北京城墙仅仅是属于你们北京,或仅仅是属于你们中国的,作为一种文化,它是属于全世界的!”朱老先生说当时他听了,又是感动,又是难受。
朱祖希说?熏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对遗产认定的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原真性,就是必须是历史上的原物,它们保留着原始的真实性;二是整体性,文物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古建筑尤其如此。高大的故宫必须要有四合院来做衬托,有主有从,四合院的灰土、绿树衬托出紫禁城的金碧。另外,北京城的规划和建筑设计继承总结了中国古代的都城建筑思想,是从建筑角度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在世界文化遗产和建筑史上都占有极重要的位置。我们为什么要提整体保护北京城,就因为它是在一个整体规划的思想下所营建的建筑产物。但现在整体是谈不上了,就是局部也芨芨可危。
“北京史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
朱祖希几十年来潜心研究北京的历史和城市规划,著有《北京城——营国之最》、《北京城历史演变的轨迹》、《维护北京城的整体格局是保护古都风貌的基础》、《北京的母亲河》、《北京的水资源——历史的回顾和反思》、《北京的“肺”在哪里》、《北京的山脉、水脉、文脉》、《先农坛——中国农耕文化的重要载体》、《礼治——北京城壮美秩序的本源》、《天人合一、像天设都——试论古都北京规划匠意的文化渊源》等文章和书籍,对北京史的研究颇多造诣,多年来频繁受邀到首都图书馆、首都博物馆等单位讲课。他是永定河文化研究的发起人之一,并曾参加了宣南文化、运河文化等研讨。
在当今的北京史研究和北京区域文化的一些研究中,朱祖希认为其中有欠妥当的地方。他说:“就比如运河文化研究,运河的南端在杭州这没问题,有人提出来其北端在通州的张家湾这就有问题了。我们说积水潭码头才是大运河的北端点,要不然通惠河的开凿就说不通了。前些年有人撰文说北京城的源头在房山琉璃河的董家林,那么燕、蓟二城谁分封在先?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的分封是逐步的,先有蓟后有燕,后来燕强大之后灭了蓟,但北京城的形成之源还应在蓟。关于这一点,侯仁之先生早有定论,在广安门外滨河公园内还立有侯先生撰写的‘北京建城记碑文。”
说到这儿,朱老先生又提起了他信中质疑的那篇有关京西韭园村的文章。文中说,韭园村有人认为此村为元代词曲家马致远的故乡,并有一民居挂牌为“马致远故居”,门前即为“小桥流水”;村外另有一古堡,相传为宋徽、钦二宗被囚之地,有“坐井观天”之境。朱祖希认为此大不足信。他说:“我曾去过该村考察,我认为这两个典故是凭空杜撰的,或者说是为了吸引游客而编出来的故事,既无史实作依据甚至连传说都不曾有过。当时我曾与该村党支部书记开玩笑。我问他:‘您贵姓?‘您为什么不姓马?‘如果您姓马,您不就可以说您是马致远的第几代孙了吗?他听了之后并没有在意,也知道我是在与他开玩笑。”目前,有关京西韭园村有马致远故居之说早已不胫而走,网上还有网民赴故居一睹真容的游走文章,至于其真假,有人信之有人不信。朱祖希认为,历史上有关马致远的记载中,只留下他乃“大都人”一词,但没有留下其他任何可供进一步考证的资料。至于这里曾是宋徽、钦二宗被俘后囚禁之地,更是无从谈起。
“研究北京史是我一生的幸运”
朱祖希在家排行老五,上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父亲早故。1955年当他高中毕业考上北大地理系时,母亲身边就只有他一人陪伴,哥哥姐姐有的在香港,有的去了台湾。家里没钱,母亲也舍不得他离开。在这紧急时刻,朱祖希七个姑母中略通文墨的三姑母知道后,力劝其母让其上学。后来,朱祖希靠着杭州市招生办公室提供的路费,在火车站吃了一碗一角钱的阳春面,挑了一只薄皮箱、一个铺盖卷、一领凉席,坐着慢车去了北京。到前门火车站,前门楼子给了朱祖希最初的震撼和对北京城的第一印象,成为他大半辈子热爱北京、研究北京的滥觞之一。
朱老先生回忆,开学第一天,时任系主任、风华正茂的侯仁之先生给全体新生讲“北京”课,这一课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地植入了他的心田。第二天侯仁之就带着他们上西山考察。直到今天,朱祖希还牢记着老师的教诲:搞地理研究一定要到野外去考察,既是发现新的信息,也是对原有材料的一个考证。这是一个做学问的最起码的严谨。联想到如今社会上的浮躁风日重,朱老先生感慨万端。数十年来,只要有侯先生的课,朱祖希必定不远十里八里的赶去听。他说侯先生的课讲得太好了,百听不厌。朱祖希认为侯仁之先生开创了北京城研究的一代先河,对北京史研究中的许多重大课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他的弟子,应该继承老师的研究思想并将它们发扬光大。令朱祖希聊以自慰的是,近年来,他的探索北京城市规划建设文化渊源的研究已取得很大成果,近日,他有关这方面的专著《营国匠意——古都北京的规划建设及其文化渊源》将要付梓出版。朱老先生说,中国有句古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新书出版之际,他要在书前写上:“谨以此书献给我永远的老师侯仁之先生”。
当年初入燕园、初涉地理研究的朱祖希是一下子就爱上了这门学科的,可以说是从事了自己喜欢的事业。朱祖希说,搞地理研究,平常需要出外考察。当时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一个书包,书包里一个水壶、一把锤子。又因为老师侯先生是研究北京地理的,所以朱祖希就从北京城的胡同跑起。朱老先生说,每逢周末,他就进北京城串胡同,到后来甚至胡同里哪里有厕所都门儿清了。不过,在燕园的学习生涯也不平静,1956年元旦刚过,好动的朱祖希在未名湖练习滑冰时摔断了腿,不得不休学一年。考虑到地理专业经常需要野外考察,学校准备让他转系。得知消息之后的朱祖希万分焦急,他觉得自己与地理专业已经分不开了。他与学校力争,并以康复后的身体为强有力的理由,终于留在了自己喜爱的研究领域。因了这一事故,朱祖希与两届学生都熟悉了,并且成了好朋友。如今,这些师兄弟们都活跃在地理研究或北京史研究的前沿,与老先生互为呼应。
时间匆匆流过,老先生侃侃而谈。除了谈古建筑,他还谈前门大街的老字号,谈“头顶马聚元,脚踩内联升、身穿瑞蚨祥、腰缠四大恒”,六必居、张一元、德和园、大观楼;谈西琉璃厂的书店伙计、同仁堂的老药工;谈风水、谈风沙;谈密云水库、谈南水北调;谈忠贞不渝的老伴,谈健身秘诀……谈历史要真实,档案更要真实。
对自己钟爱的北京古建筑,朱祖希说他最欣赏的一句话便是:历史是根,文化是魂,建筑是历史文化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