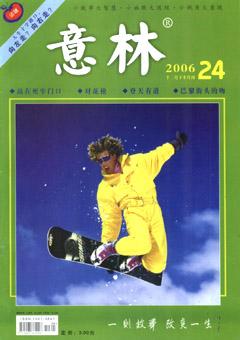疤痕
[美]乔安娜·史蓝
整形医生的手揉着我脸上扭曲的疤痕。医生的年纪大概比我大十几岁,长得十分英俊,他的阳刚之气与激烈的注视似乎太有力了。
他低声说:“嗯!你是模特儿吗?”
他是在开玩笑吗?我这样自问,并审视他英俊的脸,看看他是否强忍着笑意。绝对没有人会把我误认成时装模特儿。我很丑,我母亲通常会说我姐姐是一个漂亮的孩子。毕竟,我有一个疤痕来证明这些论点。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遇到了一场意外——邻居的小男孩抓起一把水泥向我的脸上扔过来。急诊室的医生将我破碎的皮肤缝合,用羊肠线穿过我的脸皮外部,然后再缝合我嘴里碎裂的肉。以后的一年里,我必须用大片绷带——从面颊骨到下巴——将发炎的伤口贴住。
意外发生数周后,我又患上近视。现在我难看的绷带上加了一副又大又厚的眼镜。我蓬乱的卷发让我的头看起来像是发霉的黑面包。母亲为了省钱,带我去美容学校,让那儿的学生帮我剪头发。那个帮我剪发的学生热心过度,一把将我的头发剪掉,一时间只看到一团团的头发堆在地上,老师走过来的时候,我的头发已无法挽救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我们拿到一张免费剪发的代用券,留待下回消费时使用。
那晚我的父亲叹气说:“算了!对我来说,你永远都是漂亮的,”他顿了一下然后又说,“即使对世界上其他人来说,你并不漂亮。”
是啊!真是多谢了!好像我没听见同学对我的嘲弄;好像我不知道自己跟学校老师疼爱的小女孩不一样;好像我不会偶尔瞥见自己映在浴室的镜子里的脸。在一个重视美丽外表的社会里,丑女孩根本没人要。我的外表为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每次家人收看儿童选美比赛或才艺比赛的节日时,我都会躲在自己的房里哭泣。
最后我决定,虽然不能让自己变漂亮,但至少要永远让自己保持整洁的外表。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学会整理自己的头发、戴隐形眼镜、使用化妆品。我观察别的妇女如何适当地装扮自己,学习穿着最能凸显自己优点的衣服。现在我已经订婚了。我脸上的疤痕虽然随着时间的变化而缩小、淡化,却依然成为我与自己新生活之间的障碍。
“我当然不是模特儿。”我略带愤怒地说。
整形医生双手抱胸,看着我说:“那你为什么还要去管脸上的疤?如果没有什么专业上的理由非将疤痕去掉不可的话,你今天来这儿干什么?”
突然间,在他身上我看到了所有我认识的男性。那八个受我邀请去参加舞会却拒绝我的男孩、我上大学时偶尔约会的男孩、那群长久以来忽略我的男性、我的未婚夫。我将手举到脸旁,我脸上的疤痕证明我很丑。我的眼眶盈满泪水,视线变得模糊。
医生拖了一把凳子在我身边坐下。他的膝盖几乎碰到我的,他的声音缓慢低沉。
医生轻声地说:“让我来告诉你我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虽不是个完美的女人,但却很美丽。萝伦·贺顿的两颗门牙中间有一条缝,伊丽莎白·泰勒的额头上有一个小疤,”他停了一下,拿了一面镜子给我,“我常想:出色的女人都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我相信她们的不完美之处只会更突出她们的美,因为,由此我们确定她们也是人。”
医生将凳子向后推,然后站了起来:“我不会动你的疤,别让任何人用你的脸来愚弄你。你用自己的方式散发魅力,真正的美来自一个女人的内心。相信我,我的专业知识让我知道这点。”然后他就走了。
我看着镜子里的脸,医生是对的,多年以来,那个丑孩子已经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女人。从整形医院走出来那一天起,我就成了一个职业演讲者,以对着成百上千的人演说为生的我,常常听到很多人(男女都有)赞美我,说我很美丽。而我对此知之甚详。
当我改变审视自己的角度时,别人也被迫改变看待我的角度。虽然整形医生没有移除我脸上的疤痕,但他却移去了我心里的疤痕。
(黄胜利摘自《激励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