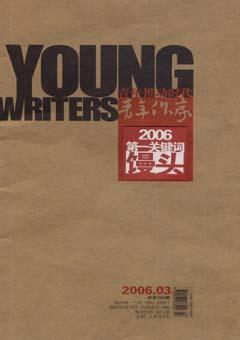春天没有阳光
1931年1月2日。清华同学会馆。破庙般的房子,空洞发霉,一走动地板就铮铮响,如同有人呻吟。大雾。上海沉浸在锯齿一样的寒流和黑幕一样的雾霭里。沈从文坐在床头,给远在美国的朋友王际真写信。打开压抑的内心,才感觉到孤独、艰辛和些许的迷茫。昨天,得到两种消息:父亲的死,张采真(他最好的朋友)的被杀(在武汉码头)。而此时此刻,九妹还病倒在医院。也是昨天,书商用两块钱一千字买断了他的小说版权——钱已经用了,只有听别人的处置。想到做了这么多年的文章,沈从文感到再也做不下去了。然而有什么别的出路呢?怄过气,还得找人卖稿子。想到隔壁老人通宵的咳嗽,早上刚刚透出的天光突然又变得暗淡起来。
“跳下去,跳下去也好!”
没有什么心情,沈从文草草写完信,呆呆地站在窗前,回想起自己在北平的那些年,在上海的这些年,其间还去过武昌,他有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而这梦这幻又大都是噩梦。当初从湘西出走,不就是为了“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为了走进一个生疏的世界,赌一注看看,在一些危险中使尽最后一点力气,咽下最后一口气?现在虽是痛苦不堪,但还远不至吐最后一口气。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生于湘西凤凰,苗族。1917年小学毕业,从军,随当地军阀部队辗转湘、川、黔及沅水流域。1923年独自去北京,开始写作。1928年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编辑《红黑》《人间》1931年5月回北京,转青岛。1933年主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京派作家”之首。1934年至1939年在北京主编全国中小学国文课本。1939年_1947年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1947年至1949年在北京大学教书,10月后进北京历史博物馆。1988年5月去逝,失去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大量作品描绘了不受“近代文明”玷污的朴真人性,在古老的生活节奏与情调中塑造了一系列没有阶级烙印的自然人。以湘西为背的小说最引人注目。中篇小说《边城》为其代表作。想起过去的一年,也是元月,1号就流鼻血,血流不止。公学学堂又不开饭,不生火,只好每天用铺盖包脚坐在桌边教九妹念书。学生4次借给他们木炭。那些日子天气也极为讨厌,落雨不落雪,阴郁。大风吹来吹去,也全是徒劳,只能成天拿铺盖包了脚坐在桌边发呆。唯一的希望就是盼着天气好、身体好,做点想了好久的文章。
差一岁就30了,在北平也混了好些年,写了一些文章,交了一些朋友,挨了一些饿受了一些冻,怎么也有了一点沧桑。记得1929年12月28日,走到黄浦江边,突然生出一个危险的念头:“跳下去,跳下去也好。”同样是寒流,同样是雾霭,还下着冻雨。雨点打在灰暗的江面,沈从文的眼睛有了湿润。他抓住石栏杆的手在颤抖,有一瞬间,他几乎悬空了双脚。他想起了1925年鲁迅对他的责难,本是一场误会,真相也大白了,鲁迅却没有道歉或做一个解释。灰色的黄浦江唤起了他对湘西的记忆,对沅水的记忆。“跳下去也好!”为什么?他发现很有踌躇的必要,他想至少要为女人这样的事投江才有意思。现在,他再不想去死了。他已经在上海爱了一个女人,一个穿黑布衣、黑脸的女人。但这爱,几乎还停留在暗恋阶段。偷偷地,时而在孤独中想起,滋生—些妄念,或者偶尔面见,心脏猛烈地鼓荡,弄出一阵眩晕。但这眩晕又只是自己血液的事,别人是万难察觉的,包括那个黑脸、穿黑布衣的女人。
1月17日发生的事
上午10点半。沈从文收拾出门,打算先过法租界看好朋友胡也频(他叫他海军学生),回来再去四马路(12点,中国公学的同事储先生请他吃饭)。没有雾,也没有太阳。空气里少了往日的潮湿。干冷。
跑下楼,听得公役锁门的声音。邮差迎面过来,提着大包邮件。算定里头有自己的,便又转身爬上四楼。沈从文的信件果然不少,其中有胡也频从法租界寄来的,说自己急需搬家,再不能在那个地方住了,还要沈不必去看他,因为他的住处现在似乎不适宜他常去。后一句话令沈从文疑惑,却也让他想起了一些事。
翻书报的时候,沈从文老是搁不下胡也频的那句话。在沈看来,“现在似乎不适宜他常去”有两层意思,一层是那地方危险,不能去,一层是那地方有了秘密,不适宜去。凭直觉,沈从文认定是后一种。认定是后一种,沈从文的疑惑似乎在干冽的空气里融化了一角。他想起了胡也频这两年的变化,越来越瘦,越来越忙,总像是背着他做起了大买卖,还有说出的话,总是带有所谓革命的浪漫,充满了某种理想主义的激情,还有他的妻子丁玲,也有了微妙的变化。
时间倒转7年。1924年初春。北平。西城庆华公寓。一间窄而霉的房子。“海军学生”和另外两个“天涯沦落人”与沈从文说着空话,吃着开水,让沈从文感觉到了一绺日照。第二天海军学生再来,仍然是“窄而霉的斋”,仍然是说空话、吃开水。春天,却没有春天的暖意,可以给两个20出头的青年提供暖意的惟有窗外萌芽的草芽。
11点,沈从文心不在焉地翻着书报。四楼楼道上响咚嚓咚嚓地皮鞋声,急促还带点拖沓。沈从文知道是胡也频来了。在侧门看见胡也频,他说:“我正想过法租界去,问你们决定了一种啥子计划,下楼看见这么多的信,就耽搁了。”胡也频说:“我还以为你出去了!”“你什么时候动身?”沈从文把胡也频引到了客厅。“我自己也不知道,动身之前我得搬个家,那边实在不能再住了,第三街昨天又捉了一个……”胡也频诉了一大堆的苦:没钱,房东的儿子死了,明天就得腾出房子悼念,还得花钱送幅挽联。
为了节省钱,胡也频要沈从文帮他写幅挽联,沈推辞说不在行,要他找李达。胡也频不让步,赖着沈从文,说了一箩筐的好话。挽联说妥,他们又谈到上海文学界的烂事。沈从文是迷惘的,迷惘中却又清晰。为了说服沈从文,胡也频像是隐约透出一点组织,一点计划,一点希望,但沈从文总觉得那个协会能做到的,同理想相去太远。
分手的时候,沈从文的目光在胡也频的脸上停留着。7年了,眼前的这个人,在成熟的同时也在发生着畸变。他显得更为消瘦,更为憔悴,他的眼睛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坚毅。然而在沈从文看来,正是这坚毅在吞噬他的才华、他的健康。
晚上7点左右,沈从文从万宜坊回转北京路宿舍,见到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瑟缩在楼角的阴影里。“沈先生,有人找你,等了两点钟了。”伺役开了门,对沈从文说。于是,沈从文得到了胡也频的便条:
休:“我遇了冤枉事情,昨天过你住处谈天,从住处出来到先施公司,遇女友拉去东方旅馆看个朋友,谁知到那里后就被他们误会被捕了……”便条揉皱了的角边上,还写着一行很小的字:“事不宜迟,赶快为我想法取保。信送后,给来人5块钱。”
目光飘到了1942年北平的春天
说是初春,实际还是严冬。打听到胡也频随同被捕的25个人一同关在龙华警备司令部,沈从文便带了丁玲去探监。
不到7点就到了龙华,天刚下过小雪,又在酝酿大雪,灰色的铅云堆满天空,风也刮得猛。阳光是连想象都不能提供的了。这样的初春,早上便如同傍晚。沈从文和丁玲站在司令部大门前的风口上,等着挂号。
漫长的等待中,人们都不敢互相招呼,沉默着,最多走到熟人面前交换一个仿佛无意挂在嘴角的微笑,像是替代了—种语言。
11点挂完号。直到下午1点半,才见一小军官把字条送出来。两个多小时里,都在那里等,身体都早被冻僵了,肚子也闹过了革命。沈从文和丁玲好不容易领到字条,上面却是两个字:“不准”。在人群里站着挤着,他们并不甘心,尽管都感觉到自己在被风干,在被割裂,但同样也感觉到心头微弱的火苗在闪烁。一个是纯洁的友谊,一个是信仰和爱情。
经守门班长的默许,沈从文和丁玲趁混乱挤进了一道门,见有人被打得吐血,又敏捷地混入了很多的探监人中。到了里面,他们走过正拥挤着无数人头的铁窗,寻觅着那张瘦削的有些苍白的面孔。除了看见人头在窗里窗外窜动,嘴里大声地嚷着吼着,便一无所获。但他们还没绝望,他们晓得虽然没见到那熟悉的面孔,但已经接近了关押他的监狱。
在昏暗的光线里,沈从文始终跟丁玲在一起。他们呼吸着恶浊的空气,血液检测到了死亡的恐惧。磨蹭中,沈从文的目光越过丁玲的头顶,飘到了钢筋水泥的堡垒外面,飘到了1924年北平的春天。
那一年,沈从文21岁,“海军学生”20岁,丁玲19岁。礼拜天的早上,沈从文坐在窗前看天井里没有融化的雪,“海军学生”带来了一个圆脸长眉的年轻女人。海军学生已经进屋了,女人站在房门边不动。女人穿一身灰布衣,系一条青色绸裙,什么话也不说,只望着沈从文笑。“你姓啥?”“我姓丁。”女人进了屋,坐下来还是笑。沈从文心里想:你一个胖女子的神气,却姓丁,倒真好笑咧。话匣子打开,沈从文与圆脸女子谈了很多,都从湘西来,曾经喝着同一条河的水,颇有几分“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的意趣,要不是“海军学生”已经爱上她,要不是“朋友妻不可妻”的道德在,很难说他们不会一见钟情。
那一次,以后的很多次,沈从文与丁玲谈话时,“海军学生”便坐在窗户的桌边,带着稍稍显得痴呆的微笑,望着那个圆脸长眉的女孩。那样的望,简直就是一种迷恋和臆想。
一个厨子模档的大胖子走过来,用油腻的手擦着眼睛。丁玲见缝插针地挤上去,递过手里的字条。胖子接过手,看了一下,又抬眼看了看丁玲,摇摇头,一句话没说,还了字条,走了。
过了一阵,人更少了,这一次挤上去的是沈从文。他递过字条,那胖子又看看他,明白了他们的意思。胖子没有高抬贵手,反倒问:“既然明明白白写了‘不准,还来这里做什么?”沈从文说不能见面总可以送点东西。这时来了个军官模样的人,看了那字条,同胖子说了几句话,便过来很和气地告诉他们,这个人上面有命令不能见,也不能送东西,但身上要是带了钱,可以送一点,有5块就够了,钱多了没用。
当军官把钱拿进另一铁门,沈从文和丁玲站在指派的窗口等着收发票的时候,突然听见一阵金属脚镣的声响。他们慌忙跑进第二道小门,一眼看过去,正是胡也频的身影。沈从文把胡也频刚刚出现的地方指给丁玲,那个戴脚镣的影子正走了回来。
“频!频!”丁玲叫起来。
戴脚镣的影子听见了丁玲的叫喊,停顿了下来,把戴着铁手铐的双手举起,很快乐地扬了一下,随即就消失在了门背后。夜幕降临,落起了大雪。铁手铐放出的光亮是沈从文在1931年春天看见的唯一的光亮。
绝望的南京
2月8日,一位朋友专程从南京赶来,同丁玲商量营救胡也频。谈话时沈从文在坐。9日,沈从文携丁玲搭了早车过南京。天气没有多大变化,只是更冷,更阴郁。快过年了,车厢里特别拥挤,特别的脏、乱。
上车前,看见街上全是兵,扁头扁脸,见了人就逞凶。这些天,他们看了很多,杀人,杀青年,19岁,17岁,都牵出去杀,还有女学生。记得1年前的这时节,世道还不都是这样。沈从文还时常到街上去,停留在那些肮脏的小铜匠铺前面,看黑脸的铜匠打水壶,麦秸杆一样的细脖子,鸡蛋大小的脑壳,圆溜溜的眼睛。看着那些人,他总是忧愁。还有天天目睹的小剃头匠,挑了担子满街走,敲着铜锣,或者在街的角落,按住一个又大又圆的脑壳,用刀刷刷地刮。太阳照在他们的背上,感觉特别温暖。而今,太阳到哪里去了?
火车开了,江南的田野在雾气里也藏不住她的美丽。
车过苏州,沈从文想起了她的黑脸好,但因为铺天盖地的阴郁,这想念并没有勾起他曾经有过的美好冲动。这样的天气,这样的坏情绪,就是走近她,又能有什么感觉?火车在苏州停靠的片刻,沈从文的眼睛一直望着虎兵斜塔的方向,琢磨着它真的倒下会是怎样一种情景。在心头默念过黑脸女子的名字,沈从文的眼角有了些许的碎泪。
一到南京,沈从文便去找胡适。在胡适家中,丁玲见到了从前在北平补习学校同宿舍的曹佩声和一位姓钱的女士。曹是主妇,钱是寄居。3人多年不曾见面,见了,也不再有先前的亲密,各人的生活思想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想起“海军学生”如何将丁玲从她们中间抢走,又望着她成为当红女作家,曹、钱自然感既万千。
丁玲与老朋友叙旧,沈从文跟胡适出门找人,半夜才回。
就在下午沈从文跟胡适为营救胡也频,在一个个楼上的小房间里见到了一个“大人物”谈了两个时辰,却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在谈“民族主义文学,还谈到一些有关树种的知识。胡适坐在一旁搓手,间或插两句闲话。“大人物”说累了,沈从文这才老老实实说了自己的立场,以及这次为了胡也频过南京的意图:政府不该不分青红皂白把作家捉去当土匪治罪,这样和过去用3块钱一千字的办法收容作家是一样的愚蠢;虽然政府杀个把人不算啥大事,但是政府里有见识的人应该明白,让一个知名作家永久蒸发是既不明智又不名誉的;这个人如果真犯了罪,就把他交给法院;另外,还想知道一点这个人的近况。
沈从文说了10钟,得到了一个勉强算是预约的信息,胡适做了个手势,他们便告辞了。三个人都没有忘记古老的传统礼仪,拉拉手,点点头。
在胡适1931年2月24日的日记里,附有蔡元培1931年2月20日给他的复信,内容便是关于沈从文奔波于京、沪之间,营救胡也频的事。蔡元培在信中说:“……沈从文君到京,携有尊函,属营救胡也频君,弟曾为作两函,托张岳军设法,然至今尚未开释也。”
事实上,沈从文和丁玲在胡也频被捕后的第3天、即1月20日已来过南京。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记有:“沈从文来谈甚久。星期六与星期两日,上海公安局会同公共租界捕房破获共党住所几处,拿了廿七人,昨日开讯,只有两女子保释了,余25人引渡,其中有文学家胡也频。从文很着急,为他奔走设法营救,但我无法援助”。
带着一身寒气和夜幕回到胡适家中,沈从文有了那么一点点的放心,但当他读过丁玲递给他的一封从上海寄来的快件,他一下子就瘫软了。信上只有一句话:“7号共匪案内已有23人业已在此枪决,不知你们在宁所得消息如何?”
一阵枪响过后
回到上海,大风吹散了铅云,但阳光还是终不露面,阴郁薄了,却也更尖锐了。丁玲仿佛获得了自由,与婴孩照旧住在那幢3楼的房子里。婴孩哭哭啼啼,她每夜都要爬起来两三次,白天又得调奶粉搓尿布,文章自然是做得更少。沈从文时常过去,帮帮孤儿寡母。看见丁玲一副沦落的模样,沈从文想起了当年北平那个圆脸朋的女子。
事情一步步被证实。从别处也得知,龙华警备司令部有23人被枪毙,说是6日午夜,每个人脑壳上都被套了麻袋,装上卡车麻运到了黄浦江边的小汽轮上,再把汽轮开出吴凇口,将麻袋投到江中。也有说是在12日的雨雪中,23个人被押过南京,再枪毙的。还有说是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外的荒地上就地收拾这帮年轻人的,时间是在7日与8日之间。
不久,沈从文从一位姓郭的女士嘴里得到真情:胡也频等25个青年被租界移交给公安局的当天,就有电文给上海市长,令择日全部枪毙。考虑到里面有几个知名作家,上海又不比内地,国际影响大,市政府方面自然有了思量与踌躇,犯人也都转到了龙华。其间,有两人被取保。2月7日是“左联”预定开会的日子,南京再次来电,令当日全部秘密处决。
据当事人讲述,事实是这样的:7日黄昏,23人从监狱被提出,说是要押过南京审判。结果却只改押狱旁的小兵营。晚上9点4分,被提去过堂,说过了堂就上火车。犯人被一一点名,接着宣读南京来电,接着诵读这群青年的政治企图如何反动、违法,最后是死刑宣判。
夜已深。光线暗淡。胡也频站在中间,衣裳还未见褴褛,胡子长出来了,面色出奇地白,眼睛里是不易察觉的悲戚。听说立即要枪毙,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向左右两侧的柔石和殷夫凄惨地微笑,且转动着头,希望把微笑带给每—个同伴。他的目光在冯铿的身上停留了片刻,发现自己已在微弱地颤抖。
军工厂堆积材料的旧房子。23双脚镣。23双手铐。23张被布片塞住的年轻的嘴。12个荷枪实弹的兵。一个排长。一个狱官。37个人的沉默。土墙。23个人排成的不甚标准的队列。12个兵退后十步走,举枪,瞄准。一声呼哨。响起87枪。23个青年倒下。慢镜头。没有口号。死一般的沉寂。完事。几个兵拿手电晃着,解了手铐,解了脚镣,一个个拖进事先挖好的土坑,再拿柔软的泥土盖上。落了雪的泥土,润滋滋的。春天已经明显了,但依旧没有阳光。胡也频死了,孤儿寡母还得活下去。沈从文天天都要来看丁玲。丁玲在湖南的母亲对女婿的事似乎也依稀晓得一点,催着他们返乡。开始是沈从文为胡也频代笔。但很快,老母亲等不及了,说如果他们3月还不回去,4月她一定要来上海。无奈之余,沈从文只有硬着头皮装成胡也频,拿了徐志摩帮忙给中华书局卖稿的钱,携了丁玲和孩童,“夫妻”双双把家还。
3月中旬,沈从文和丁玲从湖南回到上海。丁玲接受了一位美国女记者的采访,并为日后与美国女记者的福建籍翻译同居埋下了伏笔。5月16日,沈从文听徐志摩的话去了北京。丁玲开始筹划《北斗》,去信要沈从文组稿,沈从文在回信中表明了自己的文学观:“……我不轻视左倾,却也不鄙视右倾,我只信仰‘真实……争持谁是正统原近于精力的白费,毫无裨益事实。把文学附属于经济条件与政治环境之下,而为其控制,则转动时代的为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文学无分,不必再言文学。否则文学受两者控制,文学实有其独创性与独立价值,然则文学论者所持论,仍无助于好作品的产生。不问左右,解决这问题还是作品……”
责任编辑纳若
阿贝尔,上世纪6O年代后期生于四川平武。80年代后期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现居岷山东麓。近年散文受到关注。代表作有《怀念与审判》、《1976:青苔,或者水葵》。有较为独立的写作意识和生活准则。获第二届冰心散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