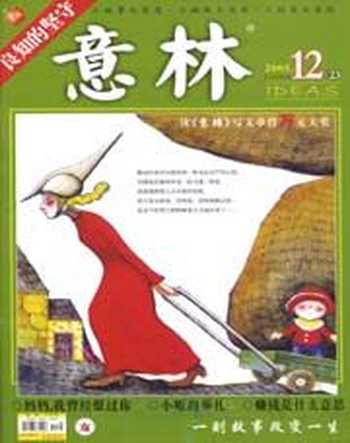尊严地离开
宇 虹
1995年12月的一天。
霍贝特·莫维斯正开车在回家的路上。“汉内罗尔已变成个老太婆了,”看着搭在座位一旁的那条毛茸茸的围巾,临出门时,老伴汉内罗尔坚持着把它塞给自己,“整日唠叨这个,操心那个,她忘了她的丈夫一直像二十年前那么棒吗?”霍贝特吹起了口哨。
突然。他嘴唇一哆嗦。口哨戛然中止,一阵剧痛从腹部撕裂般传开。
车子停住了。霍贝特趴在了方向盘上……
医院。诊断结果出来了。“喂,伙计,你那大啤酒肚里藏了个家伙,”詹姆斯医生手里拿着张X光片,眼睛定定地盯着他,“我们想打开来看看那究竟是个什么。”
“亲爱的,怎么了?”汉内罗尔不安地凑过来。
“没什么,”霍贝特晃晃肚皮,“詹姆斯说这里面有个小家伙,”他夸张地拉长了声音,“他要把它拿出来。”
手术台上。霍贝特拍了拍妻子的手,“亲爱的,别担心,手术后,你会看到我苗条的身躯,我会重新变成一个美男子。”
汉内罗尔出去了。霍贝特收起了笑脸,“喂,大卫,”他扯了扯站在他旁边的麻醉师,那是他的老朋友,他们常一起出去打猎,“请你帮我一个忙,如果情况良好,你就把大拇指往上翘,否则,就往下。”霍贝特轻声地说。
手术结束了。
霍贝特苏醒过来,汉内罗尔俯在他身边。
那个该死的大肚子,仍那样旁若无人地高高挺起。霍贝特闭住了双眼,稍一会儿,他睁开眼睛,抱歉地对妻子说:“汉内罗尔,大概没什么希望了,这家伙太大太累赘,我没法带着它挤过鬼门关。”
霍贝特说,人一生下来,就在向死亡走去,现在该考虑最后一步怎么走了。
接着,他又说,最后一步他要在家中而不是在医院里过。
情况很不妙。据医生预测,他少则只能活两个月,最多也不会超过六个月。
然而,霍贝特度过了严冬,又度过了炎夏,并且,他还举行了多次夏季晚会。
霍贝特像他所自诩的“永远是个小伙子”那样,爽朗地笑着、跳着。
苦恼的仿佛是死神,它不知该如何下手。
就在此时,BBC(英国广播公司)正在策划一部奇特的电视片。
一个摄制小组跑遍了英伦三岛和爱尔兰,打算找一个愿意接受他们采访的人,以便向观众展示死的科学。
1996年秋季,制片主任克利斯·斯潘瑟登门拜访莫维新夫妇。
霍贝特却一口答应了对方的采访拍片要求。“这不挺有趣的吗?亲爱的,”霍贝特拉着妻子的手,嘟囔道,“我不能成天只守着癌症啊,与他们在一起多有意思呢,何况,”他顽皮地向妻子挤了挤眼睛,“谁能像我这样以这么一种坦率的方式告别妻子和人间呢?”
1996年圣诞节前夕,BBC的摄制组开始拍片。
此时,霍贝特肚内的癌症肿瘤已扩张成两个足球那么大。“比分多少了?”霍贝特躺在椅子上,“快吹终场哨了吧?”他疲惫地笑了笑。汉内罗尔在一旁用毛巾替他拭去额头上的汗珠。“这家伙可真厉害,它把我的草皮吃光了。”
“他还是那么聪明幽默。”汉内罗尔一阵恍惚。
霍贝特出生于德国,从事古玩生意,却梦想当一个农民。
这么多年了,汉内罗尔还记得她接到霍贝特急急打来那个电话时的情形。已深夜了,她刚拿起话筒,耳边就炸开了霍贝特的大嗓门,他激动地告诉她,他在农村买了座“新居”。
“新居”是一间快要倒塌的茅草屋,不过周围倒还有几英亩荒地。没有自来水,厕所在屋外,很不方便,可霍贝特却乐在其中。他一边做他的古玩生意,一边抽空修葺他的“新居”。日子过得如此悠然惬意,他们养鸡、养猪,还自制果酱酿酒……
摄制小组和霍贝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一起聊天、开玩笑,有时汉内罗尔想加进来,霍贝特会大模大样地向她挥挥手,眼睛里却充满爱意:“一边去,在谈爷儿们的事呢。”
在最后的日子里,霍贝特搬到外客厅,这样他就可以看到季节的变化。“我喜欢大自然,喜欢树木,喜欢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霍贝特的眼睛眯缝起来,专注而喜悦。
1997年4月8日早上5点。汉内罗尔被霍贝特惊醒。“我痛得实在受不了了。”霍贝特呻吟着,他甚至要求护士给他打一针,让他死掉算了。通常,只要给他打一针止痛针,一切就会过去。然而,这次却不同,霍贝特边哭边对妻子说:“请帮帮我。”
汉内罗尔惊恐地感到某种事将真实地发生。跟大多数人一样,她没有接触死亡的经验,然而,忍住恐惧,像往常的每个早晨一样,她开始为丈夫清洗身子。他全身除一张皮、一把骨头外,只剩下一个大肚子。
清洗过后,霍贝特恢复了平静。可过了一会儿,他的嘴唇又动了——他在对汉内罗尔说:“今天天气多好,是死的好日子。”
实际上,他的生命又延续了28小时。死神慢慢地挨了上来,霍贝特呼吸困难,全身抽搐,他在进行最后一次战斗……
最后一刻,汉内罗尔用胳膊紧紧抱住了丈夫,用德语轻声地对丈夫说:“太阳出来了,我们一起去森林散步吧!”
冬去春来的日子里,霍贝特告别了人间。
他虽未能活着看到他爱尔兰式的花园里玫瑰盛开的景象,但他遗言,一定要把他的骨灰撒在花丛里,“这样我的灵魂将永远跟大地在一起。”
其实不止如此。霍贝特的灵魂还将永远跟活着的人在一起。BBC摄制小组将他最后的日子制成《生命的最后一刻》系列片,播出后深深吸引了广大观众。
自然,这样的片子打破了英国人所公认的禁忌,反对它的人当然有。一般英国人很少在日常生活中谈论死,更不用说把它作为娱乐的题材拍成电视片,这等于把个人的隐私暴露在公众面前。然而,霍贝特根本不去理会社会上的种种争议,他说:“我知道我生前永远看不到这部片子,但我希望大家都看到像我那样跟病魔作斗争的全过程,看到怎样才能最好地利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
(黄飞摘自《心灵鸡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