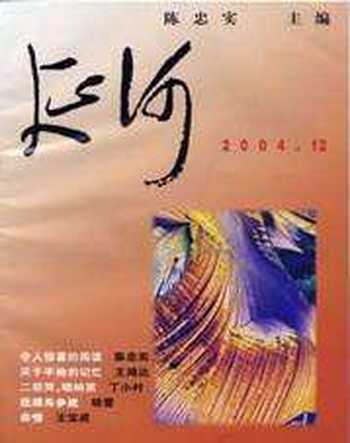去城里看电影
1
坐在自家屋檐下的三子,聚精会神地看着走廊上的几只麻雀在叽叽喳喳地抢食。这时,突然听见有人喊他,三子,到城里看电影去———
三子的家门口是条砂石马路,那是通向邵阳城里的,至于到邵阳之后,马路再通向哪里,三子就不知道了。三子抬起头一看,是窑山的一群朋友,喊他的是个叫五佗的人。五佗这时又朝三子用力地挥了挥手,然后继续往前走。
马路上,陆续地出现了许多窑山里的大人,当然是一帮年轻的男女,他们肯定也是去城里看电影的。窑山里的人,通常消息灵通得多,比如说,城里有什么好电影了,发生了什么武斗事件了,甚至于有什么好的布匹卖,他们不用多久就知道了。三子就是经常从五佗他们那里,知道城里发生的许多事情。
窑山和农村其实是混在一起的,错落交织,又没有围墙,所以,你很难用清清白白的框框划分开来。三子虽然是农村孩子,但是他经常和窑山的孩子在一起玩耍。三子禁不住诱惑,犹豫地往屋里看了一眼,母亲愁眉苦脸,正在给父亲熬草药,屋子里弥漫着刺鼻的药味。父亲在农校教书,被揪了出来,打断了一条左腿,哼哼叽叽地躺在床上已经两个月了。
三子迟迟疑疑地说,娘,我跟五佗他们去城里看电影……他担心母亲不同意,母亲也许会责备他,你父亲伤成了这副样子,你还有心思看电影?
母亲在光线黯然的屋子里唔了一声,三子的心情顿时高兴起来,他知道母亲同意了。紧接着,三子站起来,飞快地朝马路上跑去,在后面大喊,五佗,等等我,我来了———吓得那几只麻雀噗地一声飞走了。
三子气喘吁吁地追赶上五佗他们,满脸兴奋地问,什么电影?
五佗高兴地说,《卖花姑娘》,朝鲜片子。
三子看看那些同伴,个个脸上也是兴高采烈的,便激动地说,朝鲜片子我还没有看过呢。
三子是第一次跟着人家去城里看电影。
五佗接着说,谁看过?都没有看过的。五佗指着那些大人,他们也没有看过。又擦了擦鼻涕。五佗的鼻涕像是下粉条似的,不断地流下来,鼻孔下面流出了两道红色的浅浅的槽。
马路上三三两两地走着许多人,个个都很兴奋。有些大人把烟抽得滋滋响,猛猛地抽上一阵,便用手指头重重地一弹,烟屁股便在空中飞了出去———这里面有兴奋加上抵御寒冷的双重因素。大家扯开步子,劲鼓鼓地一边往前走,又一边议论道,听说很好看的,那些女演员长得非常乖态,看的人很多,如果能够买到票就好了。还有人非常有把握地说,听说在邵阳演三天,应当说票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人跟着说,我听说没有谁看完之后不哭的,电影院里充满了一片哭声,像死了老娘一样。马上就有人提醒说,莫乱说啊。那个人立即就闭上了嘴巴。
三子他们跟在大人们的后面听。三子突然想起自己身上没有钱,没有钱怎么买票?没有票又怎么能够进去?他想问五佗带了钱没有,如果带了,便向他借,以后再还。但三子终究没有问,他想,他们肯定有钱的,到时候再借不迟。
五佗侧过脸,问走在身边的三子说,你会不会哭?
三子说,会哭,你呢?
五佗说,肯定会哭。
走在一起的那些小同伴也说一定会哭的,又说,到了那时候,电影院里一片哭声,你不哭都忍不住的。
三子加入了看电影的队伍之后,就完全忘记了断腿的父亲还躺在床上,母亲坐在灶边熬草药。他一边奋力地走着,一边尖着耳朵听人家说话。他而且想像自己在电影院里嚎啕大哭的情景,影片中的人物对话以及音乐完全听不清楚了,都被观众的一片哭泣声淹没了。他还想像坐在身边的五佗哭起来的时候,鼻涕肯定像永远也流不完,似长长的粉条一样,分不清楚哪是眼泪哪是鼻涕了,不时用手揩来揩去的。想起五佗那副邋遢样子,三子情不自禁地笑起来。
五佗问,你笑什么?
三子连忙搪塞说,没笑什么。
五佗满有把握地说,你还笑?到时候,你哭都哭不赢的。
窑山离邵阳四十里路,路途要经过老龙潭,范家山,高崇山,黄陂桥,火车站,双坡岭,然后再进入城里。通往邵阳的汽车也是有的,只不过每天下午两点才有一趟,人们都等不及了。大人们走得很快,恨不得几脚就走到城里。三子他们生怕跟不上,便听不到那些有趣的议论了,所以几乎是小跑。还有一个原因,只有大人们才知道究竟是城里的哪家电影院。不跟上他们,一旦进了城,三子他们就会像一群无头苍蝇四处乱窜,找不到地方。
他们出发的时候,大概是上午八点多钟。天气不太好,北风呼呼地吹来,虽然没有下雨,但那风却很厉害,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生痛。阴沉沉的空中不时地飞扬着被风吹起的纸屑或枯叶或稻草。三子他们的脸上红红的,尤其是鼻尖,红得更是厉害,简直成了紫色。一半当然是因为激动。
三子戴着父亲的一顶破旧的呢帽子,有点大,帽檐软塌塌的,遮住了眼睛。所以,三子干脆将帽子歪歪地戴着,软塌塌的帽檐便在脑袋的一侧不断地摆动着,有一种滑稽的效果。寒冷的天气一点也没有影响他们的情绪。他们的精神非常饱满,没有因为路途远而产生一丝泄气。
马路两边的田野,空空荡荡的,显出满目凄凉。不时地飞起一只寒鸟,哆哆嗦嗦地便很快消失了。农舍飘出的炊烟,弱不禁风,一股股黑黑地吐出来,立即被风吹得无影无踪了。汽车不时地来去,摇摇晃晃,便掀起漫天的黄色灰尘。所以,等到汽车一过,无论大人或小孩,都要反转身子,咬牙切齿地朝着汽车屁股大骂,你要死了——
骂上一阵,又心满意足地大笑起来,然后继续往前走。
2
三子他们走到邵阳城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钟了。大家的肚子饿了,咕咕地叫起来,可是,谁也没有提出来先吃点东西,包括那些大人。可见眼下吃东西似乎不是太重要的事情。
大人们的心情似乎更加迫切,目不斜视,马不停蹄地朝桥头走,三子听他们说是红色电影院。他们顾不得看街上的风景了,三子即使是第一次来城里,也没有对城里表示出一种惊奇之感,只是感到那街道是水泥的,实在好走多了,又没有那么多的灰尘。三子紧紧地跟着人家往前走,认为看完电影之后,再慢慢地看街景也不迟。
过了一座大桥,等到他们匆匆地赶到红色电影院,天啦,简直人山人海,一片喧哗之声。黄色的灰尘似薄雾一般,若有若无地飘荡在上空。连大街上也站满了人。根本看不见售票窗口,窗口已经里三层外三层地被人墙包围了,就连一只狡猾的鸟也插不进去。在外面等着看电影的人,急切切的样子,埋怨上一场电影怎么还没有放完,并且不停地看手表。还有一些已经看过的人便站在一边,好像舍不得离开,滔滔不绝地说起电影怎么怎么好看,说着说着,居然就流泪了。围在身边的人也跟着流泪,希望早点看到的心情就更为迫切了。当然,还有一些买到了票的人,坐怀不乱,脸上得意洋洋的,站在一边耐心地等候着,但隐隐地,那脸上又流露出一种担忧,这么多的人,到时候怎么挤得进去?
三子紧张地问五佗怎么办,五佗说,跟着那些大人。可是,那些一起来看电影的大人,一眨眼,就全部不见了人影子,通通地消失在人群之中了,看样子是都去各显神通了。
五佗愤愤地骂了一句,这些人……真是像叫化子烤火,只顾往自己的胯里扒。他是骂那些大人,一进了城就丢下他们不管了。又说,我们既然是一起来的,就要一起进去看,然后一起回家。
三子和同伴们都点了点头,不由紧紧地挨在了一起,他们的确有点看不起那些自私自利的大人。
五佗看了看这个混乱的阵势,深思熟虑地说,我们只有等到这场电影放完之后,进场的时候再混进去,这么多的人,我就不相信混不进去。
三子听五佗这么说了,悬在心上的那种担心才噗地落了下来,这下好了,不要借钱买票了。
三子跟着五佗他们退回到人不多的地带,忧心忡忡却又耐心地等待着。那是大街上了,一群一群的人也在等待。有人还悠然地嗑着葵花子,将瓜子壳吐得满天飞舞。
五佗擦了擦鼻涕,左右看了看几个同伴,叮嘱说,进场时,我们就不要讲客气了,一个跟着一个,不要掉队了,一起拼命地挤,挤进去就是胜利。
大家又点了点头。
三子看着这么多的人,像蚂蚁一样,本来是没有多少信心的,听五佗这么一说,信心又像炊烟一般地慢慢地升了上来。他不由地紧紧地握着拳头,暗暗地在给自己鼓劲。他想,五佗他们既然能够挤得进去,自己也一定可以挤进去。
那个破旧的电影院,被一片黑鸦鸦的人像铁桶一样地紧紧地包围着,说不定会被人们挤垮,如果一旦倒塌了,肯定会砸死砸伤人的。三子不免想起父亲被人打断的那条腿,浑身一阵颤抖。他暗暗地保佑电影院千万不要倒塌。
这时,人流突然骚动了起来,肯定是散场了,人们像潮水一样地涌进涌出。那些从电影院里好不容易挤出来的男男女女,脸上还残存着看电影时流下来的泪水,嘴里却在尖声大骂,挤死啊———,你娘手里没有看过电影啊———。而外面的人却充耳不闻,齐心协力地往电影院的大门口挤去,脸上充满着兴奋和渴望,眼睛炯炯发光,居然还异口同声地起哄,嗬嗬嗬———好像在不断地给自己鼓劲。
五佗见机会终于来到了,果断地说,跟着我。五佗非常机灵,飞快地贴着一群大人的屁股后面,插进了汹涌的人潮之中。
三子便紧紧地扯着五佗的衣摆,其他的同伴依次地跟在三子的后面,也抓紧着衣摆。他们也情不自禁地兴奋地叫喊,似乎需要不停地叫着挤着,就能够挤进电影院。前进的速度十分的缓慢,有时进一步,又潮水般地退了两步,那是因为观众还没有完全走出来,便急于往外冲。进出双方的阻力都相当大,真是人挨人,人挤人。三子觉得像困在了一只巨大的铁桶里面,憋得要死,呼吸十分困难,前后左右的力量,像钢铁一样残酷无情地向他单薄的身子压迫过来,似乎要将他压成一个肉饼。三子突然产生了一个不好的念头,我如果挤死了,我父母肯定会伤心死了。
三子这时突然感觉到头上的帽子被挤掉了,赶紧腾出一只手来摸了摸脑袋,帽子果然不见了,他在肩上背上摸了一下,也没有发现帽子。蹲下去在地上摸,三子是没有这个胆量的,搞不好,人就会被踩死。三子不敢再找帽子了,腾出来的那只手又紧紧地抓着五佗的衣摆。但三子还是非常担心,母亲如果知道他的帽子丢失了,会不会骂他?
叫骂声,吵闹声,哭喊声,尖锐的声音不绝入耳,简直要将耳朵震聋了。三子想,我如果是个大力士该有多好啊,只需轻轻地一挤,便会将周围的人通通挤开,让五佗他们跟在后面,轻轻松松地向电影院的大门走去。或者说,是一个会飞翔的人也是很可以的啊,只需向上纵身一跃,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向门口飞去。可是,自己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可怜的小孩,任凭人家挤来挤去。
三子心里其实有了一丝后悔,如果早知道是这样拥挤而混乱的场合,他就不会来了。但是,他却又无法抵御这个电影的诱惑。三子鼻子里痒痒的,那是灰尘在捣蛋的缘故。三子觉得那些干燥的灰尘沿着鼻孔进入了喉咙,然后走到肺里去了。
三子他们都紧紧抓着衣摆,像一根牢不可破的铁链。偶尔被人冲断了,又赶紧死死地扯着,就像扯着一丝希望。人流仍然在艰难地进出,三子他们不屈不挠,终于渐渐地向电影院的大门口靠近了。
大门口有两道狭窄的铁栏杆过道,大约六七米长,刚刚只能容一个人走。由于人太拥挤,结实的铁栏杆也是摇摇晃晃的,似乎会被人挤垮。看来,电影院也早就预料到了这场空前的拥挤,便做好了准备的,将大门半关着,仅仅留下狭窄的缝,让观众们进出。十来个守门员穿着黄色的军大衣,戴着红袖筒,年轻而又人高马大,一脸凶气,一个个地仔细查票。若是没有票的,丝毫也不讲客气,像抓小鸡一样,高高地抓起一提,就往一边丢去,也不怕摔伤了人,而且破口大骂,你再打偷票,老子打你不死?所以,就经常听到有人哎呀呀尖叫的痛苦声。
三子他们眼看着就要进入了铁栏杆过道了,心里激动不已。这时,五佗却突然不再往前走了。三子刚刚缓过一口气来,便惊讶地问,五佗,怎么不走了?
五佗绝望地说,看样子进不去了,人家好凶的。
他们这帮人便停滞不前,后面的人大吼起来,挡路做什么?灾狗!
五佗他们急忙往边上站,站在了铁栏杆的外面,但是,想出去一时又出不去,人真是太多了,他们只好紧紧地站在一起,被人们挤来挤去的,眼睁睁地看着有票的人挤进去。当然,也看着那些像他们一样没有票的人,沮丧地站在一边。这时,经过三子他们身边的一个女人,嘴里含着票,嘲笑地说,小屁股也想打偷票混进去?说得他们脸上泛起一阵难言的羞愧。
一直挨了半个多小时吧,该进去的已经进去了,外面才渐渐地松散一点,但这种松散也只是相对而言,其实仍然是比较拥挤的。许多的人,还在等着下一场电影,有些人则抱着侥幸的心理,希望能够有人退票。还有一些人就挤近大门,递烟给守门员,媚笑着,千方百计地跟人家套近乎,希望人家会高抬贵手放他一马。
三子他们便赶紧趁机挤了出来,重新来到了大街上,一个个垂头丧气的,似乎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了。
五佗突然发现了什么,对三子说,你帽子呢?
三子摸摸压得紧巴巴的头发说,挤掉了。
五佗大方地说,没关系,回去老子给你一顶。
三子怯怯地问五佗,我们……回去吧?
五佗好像没有听见三子的话,铁着脸,仍然不心甘地望着眼前这一片混乱的场面,突然说,我们走。
三子他们以为是回家了,也就跟在后面。谁知五佗并不是往回走,而是绕过了一个很大的弯子,来到了电影院的另一侧,他是想从窗子里爬进去。
可是,他们来到电影院的另一侧一看,顿时呆住了。天啦,那一排窗子上全部站满了人,大人小孩都有,但没有女的。三子数了数,总共有八个窗子,每个窗子上起码挤了五六个,姿态各异,但一律是弯曲着腰背的,因为窗口不高,不弯腰便看不见银幕。窗户上安着很粗的木栏杆,一格一格的,人们的双手就紧紧地抓着它们,不敢松懈一丝,时时刻刻地充满着紧张。窗子下面,还站着许多眼里充满着希望的人,他们巴不得那些站在窗子上的人支持不住了,只好无可奈何地跳下来,他们便可以立即补充上去。
三子紧张地看着挤在窗子上的那些人,十分担心木栏杆会被人攀断,因为窗台非常狭窄,仅仅只能踩脚,何况,又有那么大的力量全部聚集在木栏杆上面,只要一断,肯定会有人猝不及防地摔下来。
三子正在惶惶地想着,这时,只听见啊地一声大叫,有人果真摔下来了。三子居然没有听见木栏杆攀断的声音。仔细往地上一看,那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跟三子他们的年纪差不多,人很瘦,头上带着一顶棉帽子,看样子是摔断了腿,他抱着左腿喊天喊地地叫,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三子再往窗子上一看,木栏杆并没有攀断,那肯定是这个小孩没有力气支撑了,却又不愿意下来,一不小心,松了劲,于是就摔了下来。站那一排窗子上的人全都听见了,转过头来,惊讶地看了看,然后,又漠不关心地返过头去,继续看电影。电影的吸引力显然要比摔下来痛哭的小孩大得多。
站在离三子不远的几个男人,便像百米赛跑一样,匆忙地朝小孩掉下来的那个窗子跑去,企图占领那个空闲下来的位置。那几个大人挤在窗子下,互不相让,用力地推搡着,凶凶地吵骂,结果,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终于战胜了对手们,他能够凭借着身高,死死地抓着窗子上的木栏杆,然后艰难地爬了上去,甚至还回过头来,朝那几个没有竞争力的灰头灰脸的男人嘲笑了一下。
三子的心脏一下子紧了,不由地打了个寒颤,又想起了可怜的父亲的那条断腿。他和五佗他们一样,瞪着大眼睛,惊恐地看着那个小孩。
那小孩抱着左脚,痛得哇哇大哭,却没有任何人来帮他。从他那乞求的眼光可以看出来,他是多么希望有人来帮帮他。可是,大家的眼睛时而淡漠地看他一眼之后,更多的则是盯着窗子,渴望另一个机会突然降临。
站在另外一个窗子的男人,肯定被小孩这哭声闹烦了,转过头来,一脸凶相,大声地吼道,你哭死啊,吵得我们都听不清。
小孩显然吓坏了,哆嗦了一下,泪眼蒙眬地望着那些站在窗子上的人们,哭声便收敛了一些。但那种尖细的哭泣声,在冬天寒冷的大风中,像刀子一样地钻心。
三子暗暗地扯了扯五佗,低声说,我们是不是去帮一下?
五佗犹豫地说,我们又不认得他,怎么帮?
三子说,那我们干脆走,这么多的人怎么看?三子其实不再忍心看着那个小孩了。他觉得再这样无所作为地看下去,无疑是对那个小孩的一种残忍。
五佗想了想,无可奈何地说,走吧。
三子这帮人立即穿过了热闹的街道,简直像一群丧家之犬,根本无心看城里的风景了。他们的肚子已经饿瘪了,也只能在一家家面馆门前站站,闻一闻从里面飘出来的肉汤香气,口水直往肚子里咽。三子以为五佗他们身上带了钱的,谁料他们跟他一样,没有一分钱,只能看看罢了。然后,又继续走。那些一起来城里的大人,始终也不见了,他们只好匆匆地往回赶,因为天色的确不早了。
他们在回来的路上,再也没有来时那股兴冲冲的劲头了,情绪非常低落,不太说话,即使要说,也是愤愤地骂道,没想到有这么多的人,蚂蚁一样多。他们本来不想走得太快了,但是,寒冷的天气和空空的肚子,又逼迫着他们不得不走快一些。五佗的鼻涕流得更加厉害了,不时地狠狠擤一下鼻涕,甩了出去,并大声地恶骂,流流流,流你的娘啊!
三子却一直没有说话,他害怕一开口说话,北风就会毫不客气地灌进肺腑,那就更加的寒冷了。但他的眼前,总是恍恍惚惚地出现那个被摔断了腿的小孩在不停地哭泣,他那痛苦的样子,曲卷着的身体,以及无望地叫喊,弄得三子心里酸酸的。
三子有点后悔,要是帮帮他就好了。
我以后再也不来城里看电影了。三子又想。
4
三子回到家里,已是精疲力竭,全身发软,这时,天已经大黑了。昏暗的灯光下,只见母亲坐在灶火旁边,低低地哭泣,那哭泣声像寒冷的北风一样,令三子浑身不停地发抖。母亲红着眼睛看了三子一眼,又继续抽泣,显然没有注意到三子头上的帽子不见了。
三子想看看父亲,便一声不响地走进父亲的屋子里,床铺上,父亲却不见了,三子惊慌地喊道,娘,爸爸呢?
又……抓走了……
姜贻斌湖南邵阳人,下过乡、当过矿工、教师、编辑。现居长沙专事写作。著有长篇小说《左邻右舍》,小说集《窑祭》《白雨》《黑夜》《女人不回头》《姜贻斌卷》,散文集《漏不掉的记忆》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