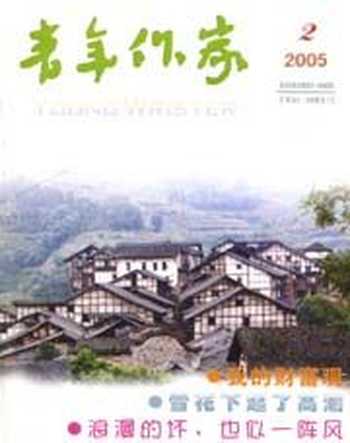乡赌
马步升
血色黄昏
吾乡地处僻远,三面临河,一面是险峻黄土高坡与外界沟通。乡亲日出作日入息,别无什么娱乐活动,赌博便为一大乐事。除妇女外,老少男子大多参赌,一个赌场,赌客中可能同时荟萃了爷孙父子兄弟亲戚朋友。赌场无父子,来的都是客,谁输谁赢,一律照赌场规矩办事,没有谁给谁讲情面这一说。乡亲们农忙赌,农闲赌,无钱时赌,有钱时赌,农闲时,无钱时,赌兴尤浓,赌风尤炽。一代代人赌下来,便赌出了一方民风,赌出了无数的恩怨。
我第一次知道赌博这种事是在四岁那年的冬天。我们那里外甥给舅家拜年是在正月初二。我家与舅家隔一条马莲河,此时河水还在封冻,冰层很厚。刚满十岁的三哥领着我,手提礼物,踏冰而过。中午时分,到了舅家。舅和舅母坐在热炕上,我们进门,二话不说,纳头便拜。舅和舅母像那年月所有的长辈那样摆摆手说:算啦算啦,新社会啦。话虽这样说,头非磕不可,话是时代话语,磕头却是老规矩。外甥不给舅磕头,那是忘本的罪过。三哥和我上了炕,舅母飞快下炕去,一会儿,饭端上来了。吃罢饭,舅严肃了脸,对几个表哥表姐说:你们几个给我好好在家玩!说完,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舅母也这么说了一句,端起一面盆油饼出门而去。又过了一会儿,三哥和两个大些的表哥说要去上厕所。过了很久,还不见他们回来,我与两个小表姐不熟悉,玩不到一块去,便闹着要去找三哥,她们劝我不住,也便不再劝了。
出了舅家门,我却不知道该到哪儿去找三哥。舅家是一座孤庄院,四周都是黄土山丘,几里方圆没有人烟。寒风一阵阵刮过,山川尘埃喧天,一片混沌。第一次一个人处在这样的境况,我感到了极大的恐怖。我觉得满世界都向我大睁着明溜溜的眼睛,都向我伸出了森森利爪,我一边惨声哭号着,一边没头没脑在山丘间奔窜。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眼泪哭干了,嗓子哭哑了,我爬上一个孤山包,突然看见一条大沟里,一片柏树高可摩天,在四棵树下,各围裹着一群人,居高临下,远远看去,人头攒动,隐隐有喧哗声。看见人,恐惧感消失了,不管是什么人,我得和人在一起。一派黄土陡坡,没有路,没有人踏过的脚印,我认准方向,叫号着,连爬带滚,来到了树下。没有人注意我,也没有我认识的人,我只听见人们在高喊着:押单!押双!揭啦!每一轮喝喊过后,便是一片惊叹声,欢笑声,叹息声,咒骂声。我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人群密不透风,我人小,从人的腿缝钻了进去,张眼一看,天,满地的钱。一个人手捧一只瓷碗,碗里装着两颗镶有黑红圆点的方形骨块,盖上碗盖,双手捧碗,一阵猛摇,只听碗里铿铿锵锵如打铃,摇一会,将碗放在面前,高喊道:押,押,快押,要吃牛肉牛滚沟,押!人们纷纷掏出钱来,堆在碗的两边。那人再喊几遍,看看再无人掏钱,便高喊一声:揭啦!人们大睁眼睛盯住碗,碗盖揭开,一片惊叹声过后,一些人欢笑,纷纷往怀中揽钱,一些人边叹息咒骂,边摸索着往外掏钱,天寒地冻的,脸上却流着汗,铁青了脸色,厉声喊:再来,我就不信狼是麻的!有人回嘴道:你来,你来,牛不顶牛是熊牛,瓦罐不离井上破,只要你来的回数多!
场面热烈,一沟沸腾,我沉浸其中,忘了害怕,也忘了找三哥的事。不知过了多久,忽听得沟口人声嘈杂,几个人群一片声呐喊,眼前的人迅疾各揣钱入怀,一人抓起碗,四堆人各发一声喊,犹如炸弹爆裂,又如羊群突遭狼袭,亦如山洪暴发,只听得一沟的嗡嗡营营,只见得眼前都是纷纷乱乱的人腿,我不知所措,瑟缩在地,只怕被哪只脚踩上。正惶恐无着,只见一个不认识的妇女,一把提起我,冲过人群,将我扔在沟坡上。此时,天已黄昏,一颗浑黄的太阳挂在天边,随时都要跌落山谷,斜阳余晖,寒风卷尘,天地苍凉。所谓站得高,看得远,定下神来,放眼一望,满沟都是人。有一片已打了起来,众多的人哗地围过去,还没打起来的地方,人们在互相争吵着,推搡着,不知争吵些什么,只见嘴皮飞动,唾沫喷溅,又一个地方打起来了,又有一个地方打起来了,满沟都打起来了,人们有的手抡木棒,有的手挥镰刀,有的解下了扎在腰里的皮带,一沟的咒骂声,一沟的吭哧吭哧声,一沟的惨叫声。我看见了父亲,看见了大哥二哥三哥,看见了舅和几个表哥,看见了几个叔叔,看见了好几个我认识的乡邻。我还看见了舅母,她手中的面盆已空了。父亲离我很近,他隔在两火气冲天的人中间,那二人一人手持镰刀,一人手提皮带,父亲似乎在劝架,忽见那个手持镰刀的人一把豁开父亲,顺手一挥,一道白光划过,而手提皮带的人顿时脸上红血溅起,我看见,一块红肉从他的脸上跌下来,落在地上,还奔跳了几下,才轰然寂灭。我看见,那人捂了脸,委顿在地,而我的父亲夺过那人手中的皮带,朝那个拿镰刀伤人的人的头上抽去,皮带挟着劲风,那人扔了镰刀也委顿在地。我看见很多人开始是和父亲一样,在给别人劝架,劝着劝着,也打起来了。
那一场混战是什么时候结束的,怎样结束的,我已想不起来了,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文革中的两派旧怨未平,一方借抓赌之机报复另一方,又让更多的赌客卷了进去。那一场混战,没有人死亡,但在场的,差不多都受了程度不同的伤。
摇麻糖
我正式参赌是在六岁那一年冬天,赌的是摇麻糖。我们那儿把麻花叫麻糖,摇麻糖,就是赢麻花吃。
冬闲了,离家很远的一个大村庄过庙会,请的是一个很有名的戏班子,父亲是秦腔戏迷,他要去看戏,顺便带上了我。父亲爱看的是传统秦腔剧目,我们称之为老戏,那年月老戏名列四旧,不准演的,只准演新戏,父亲不爱看新戏,还是去看了,聊胜于无吧。日场戏是《三世仇》,看了一半,父亲不愿看了,便领我逛会。我很高兴。时已过午,肚子早饿了。随身带有粗面干粮的,可又冷又渴,食之难以下咽。一棵大柳树下,围了一大群人,爆笑喧哗,声闻远近,我要去看看,父亲说,那是摇麻糖的。我不知道这是干啥,听上很热闹,便心向往之。看了几分钟,我已明白了其中机关。主人手捧一竹筒,内插若干竹签,将某根签摇出来一次,赢一根麻花。一根麻花本来标价一角钱,客人花五分钱摇一次签,摇中了,得一根麻花,并再赏一次摇签机会,摇不中,五分钱算白花了。看来是很难摇中的,许多人已花很多个五分钱了,还未尝到麻花味儿。顾客多是小孩,人们都没多少闲钱,每从大人手里索到五分钱,就得机关算尽。主人对自己生意的宣传也颇费苦心,有的孩子好不容易安定下来了,他便使劲摇几下手中的拨浪鼓,张口唱出一段谣儿来:
当当当,摇麻糖,
盘腿坐在了热炕上;
喝米汤,吃麻糖,
你看吃得香不香。
孩子的肚中馋虫就这样被他反复引出,大人恨得牙痒痒,却也无奈。我也耐不住了,问父亲要钱,父亲倒没为难我,但他掏出五分钱后,决然道:就这五分钱。主人看我拿到钱了,几步跨上来,拨浪鼓猛摇几摇,向我高声唱出一段谣儿来:
就看你这个乖蛋蛋,
签子摇得端不端;
一根麻糖香又甜,
老汉吃了香断肠,
娃娃吃了忘了娘。
接过签筒,我的手有些抖。我双手抱住,闭了眼睛,使劲摇几摇,一签落地,主人捡起一看:哇,中了!满场一片惊叹。主人一边给我取麻花,一边乘机大肆鼓吹生意,张口又是一段谣儿:
当当当,摇麻糖,
三请茅庵诸葛亮;
诸葛亮,本事强,
坐在炕上吃麻糖。
奖励的一次机会我又摇中了,再奖一次,还中了,一连摇中六次。每中一次,全场欢声雷动,大多都是花了冤枉钱没有吃到麻花的,主人输得越惨,大家越解气。摇中第六次时,我看见主人的脸失了血色,他不再摇拨浪鼓,也不再唱谣儿,往外取麻花的手有些抖。他是常年做这生意的,明白这是遇到了怪签。幸好,第七次我没摇中,主人解脱了,我也长出一口气。
五分钱换得六根麻花,按获利的比例计算,恐怕是我从小到现在,占别人的最大一桩便宜,几十年过去了,至今还颇感得意。占便宜和吃亏,确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父亲也很高兴,他毅然将我领进羊肉馆,慷慨地摸出两角钱,大言道:咱也喝羊肉汤!两大碗热腾腾的羊肉汤端上来,里面虽然没肉,可那是煮了肉的,是有浓烈的肉味的。父子俩每人两根麻花泡进热汤里,那个香。麻花个儿很大,一根足有三两重,以那时的饭量,我与父亲每人一顿吃掉四根是正常饭量,各吃掉两根后,都同时说:饱了。我不舍得吃了,父亲更是舍不得。福是要悠着点享的。
太阳落山了,朔风怒号,满天飞扬着枯枝败叶。父亲不想看夜戏了,这正合我意。离家还有几十里山路呢,得连夜赶回去。肚里装上了肉汤麻花,既熨帖又温暖,走起夜路来,脚板无比轻捷。走出一段路后,碰上父亲的一位熟人,他也是逛会的,说了一会话,他说今夜哪里哪里有场合,问父亲去不去,父亲看看我,黯然说:不去了吧。场合是当地人对赌场的说法,我是知道的。我也知道父亲是想去的,他担心我小,累赘。我说,咱去看看吧,没事的。父亲和那人看着我这么一个小不点,对赌博也有兴趣,都笑。我也跟着傻笑。
场合在一条黄土大沟边的一座独立土庄院里,进出只有一条路。在路口,我忽地发现一截断墙后隐隐有人,我小声说给了父亲,父亲的警惕性很高,便去墙后侦察。墙后藏着几十人,有的挎着步枪,有的手执木棒和红缨枪,个个精神抖擞,严阵以待。他们都是公社的基干民兵,根据内线情报,准备将赌徒一网打尽的。其中的许多人与父亲很熟,有的还与我家沾亲带故,一个人笑道,你还是党员,又是当过干部的,还带着这么小的娃,又是天寒地冻深更半夜的,居然也来赶场合,我先把你父子抓了!夜幕下,我看见父亲的脸色极是尴尬,他不回嘴,只一个劲傻笑。那人一只手一划拉,豪迈地说,算你运气好,四周都是我的人,今晚,哼,一个也跑不了!明天,一个个串起来,挂上牌子,游完村,一伙押到水利工地改造去!
侥幸逃脱天罗地网,父亲和那人一路走,一路嗟叹连连,为自己庆幸,为那些即将遭难的人担忧。父亲说,你看这悬不悬,要是把父子俩绑在一起游村,那还得了,这么小的娃跟我丢人丧德,人咋骂我都不说了,老先人都饶不了我的。这话他一连说了多少遍,走一会,总要说一回的。父亲当然不会公开夸我的,他要背着我走,我却不愿意。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鼓舞着我,那一夜,我特别爱走路,脚上也格外有劲。
游村
父亲与我侥幸逃过一劫,另一劫却在悄悄等着他与我的二哥。正应了一句俗话:将军合应阵前死,瓦罐不离井上破。二哥读初三时正赶上闹文革,他是远近闻名的尖子生,家里穷成了那样,父亲仍然坚持供他读书,希望有个出息。世道一乱,家庭成分又不好,书没法读了,他失学在家。与所有读书不成的农村少年一样,回到家,所受的教育立即化为无形,大家怎么活,他也怎么活,而且显得有些出类拔萃。
劳作之余,二哥也迷上了赌博。没有本钱,好在也没人验本,也没规定多少钱一注,钱多大赌,钱少小赌,没钱还可以观赌,挺善解人意的。二哥天生聪明,赶一趟场合,身上仅有的三五角钱,往往会变成几元钱。这在当时,实在是一笔可观的财富。乡村抓赌抓得很严,再严,还有人赌。被抓一回,游一趟村,或被狠揍一顿,劳改几天,放回来的当天,又去赌。大队生产队干部一边带民兵抓赌,忙里偷闲也亲自赌,民兵也赌。这一切,要根据风头形势判断,要是政治任务,就狠抓,抓别人,自己是要远离赌场的,要是一般的例行公事,那就自由多了。赌得多了,苦头吃得多了,大家都成了有经验的政治家,也学到了对付抓赌的真本事。场合一般都选择在荒僻的废弃土窑洞里,多少年没人住了,窑洞顶上土块伶仃,随时都有可能坍塌,这种土庄院都是依地势修造的,面朝黄土深沟,进出只有一条路,是旧时代防土匪用的,一遇土匪,人可以一头从面前的沟里扎下去轻松脱逃,生人不熟地理,怕摔坏了,不敢往下跳,其实没事的。沟里都是疏松的黄土,跳得得法,至多摔个鼻青脸肿,不会伤筋动骨的。村干部和民兵当然是熟悉地理的,但他们不会往沟里跳,都是乡里乡亲的,谁跟谁有多大的过不去呀。再说啦,万一跳下沟追别人摔坏了自己,不但没任何益处,乡亲们还会骂你是个二杆子,拿鸡毛当令箭了。任务只不过是任务,完了任务,任务就完了,脑子没毛病的人,早都成完任务的专家了。
父亲和二哥出事那回,是他们把政治风向判断错了。那天,村干部和民兵都去公社开会了。黄昏时分,有人在山头唱了一曲信天游,唱完就朝一座荒山走了。这是乡亲们发明的一种招赌方式。这一次,场合很大,几个生产队留在家里的男人差不多都去了。管事的人开会去了,大家便放松了警惕。其实,干部和民兵开会只是幌子,半夜时分,他们腰里拴上绳索,缀入庄院,包围了几只窑洞,又在沟边设了一层埋伏。一声尖利的哨音响起,抓赌开始了。几只窑洞的赌客束手就擒,而父亲和二哥所在的窑洞是有山墙和门的,被抓赌的人堵在了窑洞里,他们从里面顶死了门,外面的人一声声喝令他们投降,不知谁出了一个主意,里面几个年轻人暗里铆足了劲,喊一声一二,一齐用力,生生地把一面山墙推倒了。抓赌的人没防备,猛地看见山墙倒下来,吓得四散奔逃,里面的人趁乱冲出去要往沟里跳,却被伏兵抓个正着。
这次抓赌是因为国家出了什么大事,为了防止阶级敌人趁机捣乱才大搞社会治安的。父亲他们不知道这个情况,他们的反抗让大队支书大为震怒,被推倒的山墙差点砸了支书。被抓的人实在太多,支书将乖乖就范的人训斥了一顿,放了。他喝令民兵将父亲他们捆起来,关押在这座庄院里。第二天,押回队里,给每个人胸前挂上一块大木板,写上各人的名字,用红墨水将名字叉了,用绳子串成一溜游村。全大队共有五个生产队,分散在几十座山包上,方圆几十里。这一次,是要游完五个生产队的。每到有人的地方,每个犯人都要说一句:我叫某某某,我是个坏分子!参观的人都笑,祖祖辈辈生活在一起,用不着自报家门,谁不认识谁呀,谁没因为赌博被游过村呀,谁笑话谁呀。日子过得寂寞,这是难得的热闹。父亲被定为重点专政对象,因为他是老资格的党员,又是当过公社干部的。要知道,他这个党员是多么有分量吗,五个生产队长都是条件不够入不了党的。父亲自报家门时要比别人多说一句话:我是共产党员,我对不起组织。
父亲遭到了沉重打击,回家后,他大病一场。乡亲们都来解劝,大队支书也亲自上门来给他说了不少宽心话,可他的心宽不了,他一遍遍说:丢了先人了,父子两个同时丢人现眼,把先人的脸丢尽了。病好后,父亲在公众场合郑重宣布:大家看好了,我要再弄这事,你们就往我脸上吐唾沫。
父亲再也没进过任何形式的赌场。二哥也彻底金盆洗手了,工余,他复习功课,自学中医。过了一年,他参军走了。他是一名优秀的军人。
人生一场赌
我有一位远房姑父,王姓,名字我不甚清楚,我从小就叫他王家姑父。他是乡土名人,名声来自于他的赌。他是有一手不错的木工手艺的,人都叫他王木匠。可他很少出门做工,实在为生计逼得不行了,做一趟工,一分钱拿不回来,有时连行头都会输得涓滴不剩。据说,他拿到工钱的那一天,必定是要进赌场的,他也有忍住不去的时候,可赌友的消息是十分灵通的,三勾两引,他就去了,去了,输不干净是不罢休的。赌友不罢休,他也不罢休。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有老父亲,有妻子,有一儿五女,妻子很漂亮贤惠,儿女也都很聪明可爱,多年来跟他一直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日子,他也不放在心上去。他不知道娇惯妻子儿女,老爹却一直在娇惯他,年近半百的人了,老爹还是很不正常地宠着他,他做事无论如何出格,老爹都是嘿嘿一笑,怜爱地说一声:这狗日的。人们把王老爹都叫王老汉,他也是有影响的人物。他很早就参加了陕甘宁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特别能打仗。可他立一次功,就要当一次逃兵。他逃回家了。队伍上舍不得他,就派人来叫,去了,打一次胜仗,又跑回家了。据说,他前后逃跑过十几次。最后一次逃跑,新中国已经成立多年了,不打仗了,可他还跑。这次,再没人来叫他了,他回到原地,当了农民。他的逃跑是有原因的,他家从高祖手上,一直都缺男丁,盈盈一线血脉,维持了几代人。打了几十年仗,恶仗硬仗打了不少,他又是个一马当先的好战士,可他连花都没挂过。他是要为家族留后的,可几十年下来,也只获得一个儿子。儿子要不沉浸赌场,十天半月不沾家,回家了,不是整日昏睡,便是搜罗家产变卖,偿还赌债。他啥话也不说,儿媳间或埋怨丈夫几句,公爹倒先不高兴了。我记事时,王老汉大概已年近古稀了,他白天要为生产队干活,给全家挣工分,挣粮食,下工回家,要伺候自留地,晚上还要下深沟挑水。可他整日乐呵呵的,没人见过他发脾气长吁短叹过。他爱跟小孩玩,我们这一帮半大小子,经常一哄而上,压住将他的裤子脱了,挂在树梢上,大天白日,人来人往的,他双手捂住羞处,期期艾艾求我们给他上树拿裤子。其实,我们心里都是清楚的,要是真动手,别说脱他裤子,三五个精壮小伙也是近不了他身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了身达命永远快乐的老人。
王家祖居之地离我家很远,由于王木匠的豪赌,日子过不下去,在那里他家又是单门单户,没人肯照应,便借重我家势力,迁到了我们村,我家把一座废弃的老庄让给了他家。
王家还没迁来时,我已见过王木匠了。我也真正见识了这位赌客的风采。我们村靠河边有一条荒沟,长满了枣树,名为枣树沟。那里经常有人聚赌。在我上小学的前一个冬夜,大雪飘飞,天冷得出奇,我早早上炕睡了。半夜突然被惊醒,王木匠坐在炕上,父亲一边跟他说话,一边在地上给他熬茶做饭。王木匠见我醒了,从身边一只黑皮包摸出几角钱塞给我,慷慨地说:给娃买糖吃去。我伸头一看,包里塞满了钱,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王木匠披着一件崭新皮袄,眉飞色舞,在大谈他在赌场上的风采。父亲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娃他姑父,你半辈子不学好,婆娘娃娃跟你受够了艰难,这次你得见好就收,回去置点家产,过几年正经日子。王木匠答应了。可喝茶吃饭毕,他手提皮包,一跃下炕要走。父亲急忙拦住他,他手一扬,决然说:狗日的手里还有钱哩,今晚上要是刮不干净他们,我誓不为人。父亲拦他不住,天快亮时,他回来了。大雪还在下,北风还在刮,王木匠满身只有一条短裤,身上全冻青了。父亲啥话都没说,急忙将他掀上炕,用棉被捂住。王木匠将赢来的一皮包钱倒得一分不剩,连赢来的皮袄、石头眼镜,还有他自己的棉衣内衣旱烟锅都顶了赌债。我长大后,父亲给我说过王木匠那晚赢得的钱的数字,真是太可怕了,那可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钱啊。
王家搬到我们村后,我第一次失学在家,年龄太小,实在干不了生产队的重活,父亲想让我再去上学,可无学可上。王木匠得知后,手一扬,大言道:这么点小事有什么难的!二中校长是我的好朋友,一句话的事嘛。二中离我家九十里山路,王木匠带上我半夜出发,午后赶到了二中,校长正在操场转悠,王木匠赔上笑脸疾步而前,自我介绍后,校长冷然道:我不知道这个人。说完,转身就走。王木匠挡住去路,忙摸出一根九分钱一包的烟卷,往人家手里塞,校长激烈地摆着手,不接。王木匠还没来得及说事情,校长已回了房子,哐的一声关了门。原来王木匠所说的好朋友,只是多年前,他给二中做过几天活。
天快黑了,我俩身上一分钱都没有,随身带的干粮吃完了,在小河里喝了几口冷水,又困又乏又冷又饿,王木匠突然想起他曾给附近一家居民干过活,去后,那家人还勉强认得他,吃过喝过后,就住在那家。早上起来再不好打扰人家了,只得空肚子往家赶。走到街上,农副公司来了一车货,没人搬运,王木匠带上我,还有另外两个人,整整一个早上,把货全部从车上弄下来,搬进了库房。下一车货一元二角钱,每人分得三角。三角钱够吃一顿饭了,可身上没粮票,正在四处找偷卖馒头的人家,在一个背巷的一棵榆树下,看见有一堆人在赌博。王木匠顿时眼里迸放金光,三脚并作两步,挤进人圈,摸出三角钱,拍在地上,高喊:押单!碗子揭开,果然是单。王木匠手里有六角钱了,他喜气洋洋,将六角钱一次拍在地上,大喊:押单!碗子揭开又是单。他赌得兴起,见我也挤进来了,伸手向我喝道:拿来!他将我的三角钱和他的一元二角钱,一次拍在地上,又是一声高叫:押单!碗子揭开,却是双。他脸不变色,啥话也不说,起身拍拍手,高叫一声:回家喽!
我俩饿着肚子走了九十里山路,回到家,已是午夜时分。
我第二次失学时,已到了改革开放的前夕了,王木匠因为赌博受了半辈子穷,家人也跟他遭了数不尽的殃,他也没少受政府的惩治和乡邻的鄙薄。可他在这一年的腊月二十八夜里,一举扳回了金钱、名誉和人们对他应有的尊重。快要过年了,别人年货都办齐了,可王家一穷二白,别说什么年货了,吃的粮食还是乡亲周济的,几个孩子穿着破单衣熬了大半个冬天,王木匠要借两元钱置办年货,全村几十户人家借遍了,一分钱都没借到。没人敢给他借钱,倒不是怕他不还,怕他钱一到手就去赌,这是害人,不是帮人,人们宁愿帮衬他粮食日杂用物。太阳落山时,王木匠朝县城方向走了,上山时,一路还在吼着秦腔。家人也不管他,反正他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村子离县城有二十里山路。第二天日上三竿时,他甩着手回来了。刚进家门不久,人们就听见王家吵成了一锅粥,男人吼,女人叫,乡邻以为打架了,都远远近近赶去解劝。原来是王木匠赢了很多的钱,留下办年货的钱,又要去赶场合。这次,一辈子对儿子百依百顺的王老汉不干了,他顺手抄起一根顶门杠,双手高举,堵住大门,喝令儿媳和孙子孙女抢钱,有老爷子撑腰,姑姑率领六个儿女呼啸而上,将王木匠扑倒在地,将钱抢得一分不剩。为了不出变故,王老汉决定,由他在家看守儿子,让儿媳带着孩子,拉上架子车上县城采购,急用的不急用的,把钱花光。夜幕降临时,姑姑和儿女兴高采烈地从县城回来了,拉了满满一车东西,有布匹衣物,吃的用的,应有尽有。王老汉手不离顶门杠,儿子睡着了,他依然紧握木杠寸步不离,他怕儿子逃脱追到县城抢钱。儿媳回来了,听说钱全部花完了,他才解除武装。人们问王木匠是如何赢到这么多钱的,他无限风光地给大家宣讲了他的辉煌经历。
那天,他赶到县城,找到了在县卷烟厂上班的我的五哥,五哥带他吃了饭,他还要借两元钱买年货,五哥不给,他赌咒发誓不去赌博,五哥还是不给。磨到天黑,五哥给了两元钱,但不准他出门,意思是只要他晚上没机会出去,明天一大早买上货,就安全了。王木匠睡着后,五哥上夜班了,临走又给门卫做了交待。五哥下班回来,王木匠还没睡醒,五个哥暗自得意。他哪里知道,王木匠在他上班后,悄悄翻墙出去,在县城边的一个村庄找到赌场,他将两元钱一次拍在单上,赢了,他没有往回抽注,一连押了十三次单,揭开都是单。按行话说,宝跌进了单槽。他本想再押一次单,却临时收手了,抽回了注,这次是双。他惊出一身冷汗,揣上钱,推说撒尿,出门拔腿就逃。王木匠这次到底赢了多少钱,很好算的,是二的十三次方那么多。这一场豪赌,也就半个小时吧。听了王木匠的赌法,人们好半天缓不过气来,都说这真是大赌家才敢这样赌的。
在我离家远行的那一年夏天,王木匠惟一的儿子病了,治病需要很多钱,他没有钱,也借不到钱,一再延误,终于不治而殇。他从此不再赌博,什么事也不干,整日昏睡,过了两年,他家迁走了,又迁回了祖居的村庄。
赌场无父子
在我出门远行的前一年,国家改革开放了,我们那儿也在酝酿包产到户,神圣了几十年的大集体,一时处于风雨飘摇中。一些好动的年轻人走了,他们都不曾学到什么手艺,文化程度都很低,人们都担心他们出门做何生业。过了半年,不好的消息便联翩传回,有的劫财害命被政府枪毙了,有的被强人杀了,在家蠢蠢欲动要去闯社会的另一些年轻人,有的畏难而退,有的被父母管住了。在家又不想过正经日子,便没黑没白聚赌,那段时间,已没人抓赌了,于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有人张罗,场合便有了。那个时候的农村已破败到了极限,谁也没有闲钱去赌,又不知道社会要朝哪个方向走,没心思干活,又闲得无聊,便人心思赌。真可谓穷则思变,村里便兴起了摇洋糖包。洋糖者,水果糖也。一毛钱八颗,公社在村里设了百货代销店,九叔高中毕业回家,当上了营业员。天晴的日子,就地在商店门口聚赌,老少妇幼,赌的,看的,叫喊哭闹,里三层外三层,热闹非凡;天阴下雨,赌场便挪入生产队库房,妇女和太小的小孩不许入内,场合便整肃了许多。赢洋糖和赢钱的规则相同,还是摇碗子,揭单双。
九叔给大家现场卖洋糖,间或,也亲自赌几把。手风正顺的人,赢了糖,随手抓起几颗,扔给自己的儿女,高声大气地说:吃去,管饱吃,看你能吃多少。把眼睛盼绿了的儿女,顿时一脸灿烂,手捧洋糖,竟也显出趾高气扬相;正走背运的人,看见他们的儿女也不会有好声气,喝儿骂女之声直冲云霄,有那些不懂眼色的儿女,却在这时向老爹讨糖吃,自然是讨不到的,讨到的常常是顺手一巴掌。那些得到老爹赏赐了洋糖的小孩,剥开糖纸,三番五次要吃,又三番五次舍不得,流着涎水,终于还是忍住馋,挤进人圈,很内行地,大呼小叫着押单押双。八岁的天锁是赵六的独生子,赵六是一代名赌,和王木匠一样,赌得家里要甚没甚。赵六这一阵手风正顺,眼前堆满了赢来的洋糖,他一下给天锁扔过来十颗糖,天锁抓糖在手,并不像别的孩子那样,脸上露出馋相,又舍不得吃,他毫不迟疑,腰一猫,钻进人圈内围,将十颗洋糖一次拍在单上。赵六刚将两大把洋糖拍在双上,见儿子与他斗法,便一瞪眼,喝道:拿回去!天锁说:你押你的,我押我的,少管我的事!赵六抬手要扇天锁,被人喝止了,人说:赌场无父子,各赌各的运气,这是老先人定的规矩。赵六是知道这规矩的,便不再干涉天锁。这一宝揭开是单,天锁有了二十颗洋糖的本钱,气势大增,他挽挽袖子,准备大干一场。
在赌场,财力胆力不济的赌客都自觉地站在离碗子稍远的地方,一般都押游注,这会儿,揭出的单多,便跟着押单,出的双多,就转押双。也不跟人争强斗狠,如果色子较乱,没什么规律可循,便不下注,站到一边看别人赌。小孩一般都选择这种赌法,输不了多少,也赢不了多少。大赌家就像大领导一样,一上场,中心的位置便是他的,傲然往那盘腿一坐,先抓过碗子,等人把注上齐了,也不卖单不卖双,高喊一声:扯啦!一把接开碗子,单双互赔,抵过,有盈余,自己收,有亏欠,自己补。而且,前三宝不卖,借此震场子立威。赵六盘腿坐在左边,天锁人小,在右边很容易地挤出一个位置,也盘腿坐下。父子俩头脸相对,各具风采。天锁坐在了赌头的位置,但他却只押游注,而且,赵六押单,他便押双,赵六押双,他一定押单,更离奇的是,天锁押什么,揭出来便是什么。大家看天锁手顺如神,便跟着天锁押,这一头赌注便很重,赵六那一头当然很轻,每开一宝,赵六就要赔出大把洋糖。天锁越赌越顺,赵六越赌越背,却又不肯认输,眼前的一大堆洋糖眼看没了。
这一宝,天锁将一大堆糖押在双上,赵六要押单,但他已经没糖可押了,又没有钱在九叔那儿买糖,九叔是声明不赊账的,赵六便要揭碗子。这是一种破釜沉舟的赌法,自己已没赌注了,揭开碗子,如果赌赢了便罢,赌输了,或者卖房卖地卖儿卖女卖老婆,或者当场让人打残打死,老辈人遭此命运的人很多,新社会了,是不敢这样做的,但打是得挨的,赌债也得认,父死子还,不可赖账。在人生地不熟的赌场,如果有人要这样赌时,早有人环立其四周,戒备森严,怕他赌输逃跑。村里的老周就干过这活,在离家很远的一个地方与人豪赌时,一把掀开碗子,输了,大略要给赢家赔几千元注的,他一分钱没有,在第一时间,他一跃而起,冲倒几个监视他的人,夺门而出,顺势跳下深沟,脱身而去。他是当过多年特种兵的,身手不凡。即便这样,多年以后说起这事,他仍心有余悸。当然眼下这一赌没有如此凶险,顶多是丢脸罢了。赵六已是满脸稀汗,揭碗子的手抖得厉害,天锁坐在那里,神定气闲,他不屑地说:看看你的本钱再揭,这是赌洋糖,不是赌命!赵六火上来了,大喝一声:我就不信马能生出骡子!揭开是一双四点子。天锁嘲道:马偏偏生出了骡子。赵六的脸红了,又紫了,他沉声喝令儿子:把你的注拿回去!意思是不给儿子赔注了。天锁不应声,低了头,在一五一十数洋糖。共是五百颗。赵六又低喝一声:拿回去!他的喝斥声现出了气急败坏。天锁仍低了头,不撤注,也不说话。意思是再也明白不过的,上一宝清不了,下一宝就不能开。赌兴正浓的人不耐烦了,对赵六连声喊,过注过注,赌场无父子哩,不能坏了规矩,你都是大赌家嘛,输赢是个啥,脸要紧!赵六无奈,只好求九叔给他赊五百颗糖,九叔死活不肯,有人出面担保,他也不肯。这时,天锁把刚当做赌注的五百颗糖推给赵六,说你把账记牢,欠我一千颗洋糖。赵六居然接受了儿子的借贷,坐那儿继续赌。
天锁一战成名,名声几乎盖过了赵六。洋糖宝摇了一年多,除了小孩吃掉一些糖,这次赢了糖的,下次还拿这些糖赌,经过多次揉搓,糖纸溃烂,糖块化水,污迹斑斑,不可再度登场时,方才万分不忍地赏给孩子吃。天锁不上学了,小小年级,整日出入赌场,多大的场合他也敢去,多大的注他也敢下。赵六不敢赌了,父子俩赌掉了家里所有多少值点钱的东西。大约十年以后,天锁被人杀了,全裸的尸体撂在一条深沟里。据说,那一晚,天锁威风八面,全场让他一人席卷一空。在哪赌,和谁赌,都一清二楚,但怎么死的,赢的钱哪去了,却查不出来,最后,公检法给定了一个失足摔死,结了案。赵六在结案文书上签了字,尸体也火化了。这时,赵六又后悔了,年年月月日日上访,找遍了所有与法律有关的机构,把与法律没关的机构都找害怕了。后来,上级法律部门派员复查过,可有用的线索一概没有,这已是铁案。其实,杀人凶手是谁,人们都知道,赵六也知道,赵六翻案不成,曾多次手持利器去杀那人,人没杀了,反倒挨了几顿暴打。赵六已经很老了,不适合做这种英雄事了。赵六知道主管这起案子的都是我的同学和朋友,多年以后我回老家,赵六老两口来我家,跪在我面前,求我帮他翻案。我问过我的同学,他说了一些情况,我便想起了美国审理辛普森杀妻案的法官说的一席话,大意是:全世界的人都看见了辛普森那双杀妻的手,惟独法律不能说,它也看见了。法制社会,法律原则高于一切,不冤枉一个好人,大概是可以做到的,不放过一个坏人,如果没有铁证,还不得不放他一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