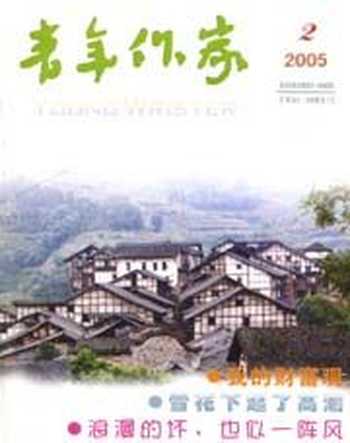狗日的婚姻
毛永健
一
深夜两点,整个喜鹊县县城全都沉浸在绝望的黑色之中,而我家的门铃却像疯狗一样叫个不停。老婆安逸用脚使劲踢我瘦小的屁股,没好气地说:“张嘴,你去看个究竟,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说:“看球个啥,它想叫就让它叫个够,直到全城人都骂他老娘才好。”
安逸说:“你这人怎么了,是去还是不去?”
我态度比较坚决地说:“不去。”
安逸说:“好,你能干。我老实告诉你,你不去我去,可是如果我被人强奸的话,你就得给我老老实实的在人前当乌龟王八蛋。”
我一个大男人怎么能够心安理得的在人前当乌龟王八蛋呢,于是我只得十二万分不愿意地从热被窝里爬起来,披了件外衣去开门。夜晚的凉风直往毛孔里钻,我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寒颤。门前站着的是满身泥污的吴聊,他穿着一双不伦不类的女式拖鞋,脸上还有几丝被抓伤的血痕。
吴聊强装笑颜地调侃说:“老兄,实在对不起,深更半夜的,打搅你和嫂子的好事了。”
我笑笑,把吴聊让进屋里,反问他:“你怎么了?这副熊样,就像老蒋手下溃败的国军。”
吴聊脸上满是尴尬:“这个时候到你这里来避难,还能怎么样,你就不要洗涮我了。我和安心的这场婚姻,看来是没法救药了。”
我说:“问题有这么严重?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我看你两口子最多是由局部战争升级到全面战争罢了。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你一个大男人,让着她点不就什么事情都解决了。”
吴聊哭丧着脸说:“张嘴,你小子是坐着说话不腰疼。如果问题有你说的这样简单轻松,那早就没有问题了。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我和安心之间就像伊拉克的战事,整个局面已经一塌糊涂,无法控制了。”
我说:“怎么会这样呢?安心其实是个不错的女人呀。”
吴聊说:“你我都是进了围城的人,女人是他妈的怎么回事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说:“如果说婚姻真是一双鞋子的话,那我只知道自己的老婆合不合脚,至于别人的鞋子,我又没有穿过,怎么会清楚它到底蹩不蹩脚呢。”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最近看过的一则笑话:农夫说:“我晚上上床后常感觉发冷。”医生说:“我也有过,那时我会搂着我太太,就会暖和了。”农夫说:“这办法不错,但您太太什么时候方便呢?”想到这则笑话,我就忍不住笑了起来。
吴聊莫名其妙地问:“你傻笑什么?”我就把这则笑话讲给他听了。
吴聊听过之后,不但没有笑,反而重重地叹了口气,说:“老兄,你就不要拿我穷开心了。我这狗日的婚姻,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了。”
我说:“你和安心不是谈过两年的恋爱吗?本来就有感情基础的,怎么一下子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呢。”
吴聊抽出一支香烟点上,烟雾顿时弥漫开来,笼罩了他瘦削疲惫的脸。
我给吴聊泡了一杯苦茶。打开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放新闻。
吴聊说:“要是喜鹊县也能像耶路撒冷和巴格达,经常出点乱子就好了。这样就可以将我和安心的注意力转移,我和安心的注意力转移了,我家就可以暂时太平了。”
我说:“你就不要痴心妄想了,还是先转移你的注意力吧,专心看电视。”
我给吴聊续满了茶水,再回头看电视,里面的图像像突然断电了似的,一片彻底的黑色。瞬息之后,才现出两个红色的行楷大字:再见。
二
吴聊在乌鸦市念书的时光,距离现在已经有好几百天了。那时喜鹊县为了匹配师资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教育局便和乌鸦市教育学院签订培训合同,一下子从喜鹊县各乡镇选送了两百名小学教师到乌鸦市教育学院进修。吴聊和安心原本在地处喜鹊县南北两端的乡下当孩子王,因了这次培训的缘故,两人居然有了同班且同桌的零距离接触。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吴聊和安心初次见面,彼此间就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切之感,加之两人坐在同一张凳子上,身体的某些部位难免会越过“马其诺防线”,有意或者无意地互相摩擦一下。而每次身体接触之后,吴聊总会偷窥见安心白皙的脸上浮起一片健康的红晕,灿烂如三月的桃花一般,撩拨得他的心里痒痒的,像无数的虫子在爬动,十分的难受。安心偶尔会穿那种前胸开得很低的裙子,据说刚好开到让男士失眠的高度。吴聊不经意的一回头,便能窥见安心裙子里面躲藏着的两座乳峰,倔强地对抗着纯棉乳罩的束缚,惨白得触目惊心。吴聊的目光往往像脱缰的野马被拴住了似的,想让他马上挪开,那简直是一件残酷至极的事情。但吴聊不会长久地把目光盯在安心的胸部,他以为那是一种罪恶的勾当,是即将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子,一旦败露将会使自己名誉扫地,万劫不复。因此,吴聊把自己怀春的心思捂得很紧。
那时,全国上下正在流行老狼的那首破歌:《同桌的你》。老狼的嗓音略显嘶哑,但充满了蛊惑人心的磁性。吴聊没趣的时候,也会扯出自己的破嗓子,歇斯底里地在无人处干吼几句。同班同学开玩笑,问吴聊是不是想同桌的安心了,吴聊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脸红脖子粗地结结巴巴地替自己辩护,往往弄得问话的同学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不就是开一个玩笑吗,没猫腻你小子敏感个啥。都觉得吴聊这小子有些神经质。
这天下午的太阳像烙红的铁锅,覆盖在乌鸦市的上空。吴聊坐在教室里,也能感觉到身上的汗液沿着脊背往下蠕动,吴聊甚至嗅到了潮湿的盐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窗子开着,教室里却没有一丝风,只有数学老师张望教授讲授高等函数的声音,在教室四壁的反弹之下,显得干涩而空洞。吴聊环视教室,发现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在张望教授的催眠曲里与周公约会,另外至少还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即将在张望教授的催眠曲里与周公约会,于是悄悄拿出了新买的《卡拉OK金曲精选》,翻到第七十九页,照着《同桌的你》小声哼唱起来: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昨天你写的日记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
曾经最爱哭的你
老师们都已想不起
猜不出问题的你
我也是偶然翻相片
才想起同桌的你
……
吴聊正哼得忘乎所以之时,同桌的安心用手轻轻碰了他一下,然后指了指讲台。吴聊抬头一看,张望教授正表情严肃地向自己所坐的位子走来。吴聊知道大事不妙,赶紧把歌书藏在屁股底下,等待张望教授的审讯。
张望教授问:“你在下面干什么?”
吴聊回答说:“听张教授您讲课。”
张望教授问:“我讲的是什么内容?”
吴聊回答说:“只知道是高等函数,但具体内容我没有听懂。”
张望教授听了吴聊的回答,使劲地摇了摇花白的头,叹息一声说:“汝等不可教,吾后继无人矣。”一副大失所望悲天悯人的神情。
终于捱到了下课,吴聊把书从屁股底下拿出来,对安心说:“谢谢你救了我。”
安心笑着说:“举手之劳而已。”
吴聊说:“对你是举手之劳,但对我却是事关重大。”事实上,只要在乌鸦市教育学院进修的人都知道,张望教授的课程能不能及格,关键看三点:其一、是否缺课;其二、是否做笔记;其三、是否在课堂上有违规违纪现象。以上三点,只要有谁胆敢越雷池半步,恨铁不成钢的张望教授便会让你为自己的不良行为付出惨重的代价。
安心说:“既然你这样在意我的帮忙,干脆就感谢我一下吧。”
吴聊说:“安心同学,你要我怎样感谢你呢?”
安心说:“你一个大男人,怎样感谢难道还用我教你吗?”
吴聊说:“那我们到‘再回首饭馆撮一顿,先解决全民温饱问题再说。”
“再回首”饭馆位于乌鸦市的中心地段。吴聊和安心在三楼找了个雅致的包间,刚刚坐下,身着长裙的服务小姐便尾随而至,将菜单递给吴聊,说:“先生,请点菜。”
吴聊将菜单放在安心的面前,对安心说:“你点吧,喜欢吃什么就点什么,我希望你能恨恨地宰我一次,因为被你宰是一种幸福的痛。”
安心照着菜单就点了一个“喜鹊县特色羊肉火锅”。
喜鹊县特色羊肉火锅不但在乌鸦市非常有名,而且在整个斑鸠省都有相当的声誉。听人传言,喜鹊县特色羊肉火锅以良种黑山羊为原料,辅以喜鹊县羊肉火锅元老吴法的祖传配汤秘方,不但能够除尽羊肉的腥味,而且能使羊肉色鲜味美。籍贯在喜鹊县的人,到外地时常以本地的羊肉火锅为荣。吴聊也曾经向同寝室的同学吹嘘过几次:“你们吃过我们喜鹊县的羊肉火锅吗?没吃过,太遗憾了,那味道,简直没说的。”不过吹了几次之后,同学们就有些厌烦了,那不留情面的甚至会抢白说:“有什么遗憾的,不就是一点破羊肉吗?”弄得吴聊十分的尴尬。后来,吴聊也就不再在同学们面前提羊肉火锅的事了。
吴聊没想到,自己第一次请安心吃饭,她居然坚决地要点家乡的羊肉火锅。看来安心这个小女子,倒是有些特别的。
火锅上来之后,吴聊要了两瓶乌鸦啤酒,倒满了两杯,端起其中的一杯说:“安心,这一杯酒算我谢你。干。”
安心没有推辞,端起一杯啤酒喝了。
吴聊又将两个杯子倒满。不多时,两人就将两瓶啤酒平均消费了。
吴聊又向服务小姐要了两瓶乌鸦啤酒。
安心说:“怕不能再喝了。”
吴聊说:“再喝两瓶应该没问题。”
安心强调说:“说定了,这可是最后的两瓶。”
吴聊发现,安心的两颊因为酒精的作用升起了几朵绯红的桃色,而她看自己的目光,也变得潮湿而虚无缥缈起来。吴聊内心的冲动就不可遏制地撩拨着灵魂,像翻腾的喜鹊县特色羊肉火锅。
吴聊伸手揽住了安心的细腰。安心想挣扎,却无力地倒在了吴聊的怀里。
吴聊说:“安心,我爱你。”
安心说:“我知道。”
吴聊吃了一惊问:“你怎么知道的?”
安心调皮地说:“除了女人的第六感觉外,还有今天数学课上你哼唱的那首《同桌的你》。”
吴聊就不再说什么,将滚烫的唇紧紧地贴上安心樱桃般丰满性感的小嘴。
三
我关掉电视,看见吴聊张大了空洞的嘴巴,之后是一个中气不足的不断拐弯的哈欠:哈……哈……哈……嚏。
我说:“是不是感冒了?我这里有‘白加黑。”
吴聊说:“不会吧。可能是太疲劳了。妈的,我千万不能倒下啊。”
我说:“那我们洗脚休息吧。”
吴聊摇摇头,抱歉地说:“我心里有事,肯定睡不着。我们干脆出去找家酒吧坐坐吧。”
我向卧室的方向指了指,说:“但愿我老婆安逸能够睡得像一头愚蠢的猪才好。”
吴聊笑笑,说:“现在的男人大都英雄气短了,不是精神上的‘气管炎,就是精神上的‘阳痿,真他妈的活得无滋无味,窝囊至极,一点男人的阳刚之气也没有。”
我说:“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牢骚也没有用,反正大家都是彼此彼此。”
吴聊就不再说什么。
我和吴聊像做贼似的蹑手蹑脚出了家门。麻雀小巷里空空荡荡的。路灯洒下的黄光和发廊门前左顾右盼招徕客人的发廊妹,使小巷里的空气显得灰暗而暧昧。如果偶尔偷窥时虚掩的帘子恰好被风轻轻掀起,便会看见男女调情的镜头。至于嬉笑和夸张的尖叫声,像一匹匹正在被暴力撕破的布,盘旋萦绕在弯曲的麻雀小巷,让不经意的听觉承受着某种难以言说的隐痛。除此而外,整个麻雀小巷就仿佛沉入了凝固的死寂之中。
我们穿过麻雀小巷,来到灯光相对明亮的燕子大街。燕子大街据说是喜鹊县十年前就享有盛名的腐败大街,如今成了喜鹊县的商业中心,林立着各种名牌专卖店及星级酒店。因此,燕子大街白天人流如潮,熙来攘往。而到了晚上,各式古朴典雅别具风情的酒吧便会延续着白天的热闹。尘世中奔波劳碌或者不甘寂寞或者失意潦倒的人们,趁着这浅浅的夜色,都喜欢到酒吧里小坐,让蒙尘的灵魂得到片刻的休憩。
我们走进了“唐朝酒吧”。
吴聊选了一个临河的包间,要了一碟瓜子,一碟甜枣,一碟杏仁,一扎冷冻乌鸦啤酒。吴聊打开一瓶递给我,又为自己开了一瓶。
我说:“慢慢地喝吧,早着呢。”
吴聊说:“慢什么慢,今晚咱哥俩就英雄一回,男人一回。”
我还想说什么,但吴聊已经拿起了酒瓶,要和我碰。我只得拿起酒瓶,和吴聊碰了一下。吴聊说:“干。”然后把一瓶啤酒像牛马喝水似的倒进了肚子里。
看着吴聊喝完了,我也只得硬着头皮将自己的一瓶啤酒倒进了肚子。
我和吴聊就这样你一瓶我一瓶地喝完了一扎乌鸦啤酒。我感觉自己肚子冰凉,脑袋沉重,膀胱胀得生疼。再看吴聊,他仆倒在吧桌上,眼光迷离,口齿不清地要吧台小姐再来一扎乌鸦啤酒。
我说:“不能再喝了,再喝就要误事了。”
吴聊把手举起来向我挥了挥,说:“喝,谁不喝谁就不是男人。”
我说:“什么男人不男人的,现在有的仅仅是男性,已经没有男人了。”
吴聊突然就用手捂住自己的脸,呜呜地哭了起来。
我说:“吴聊,你怎么了?”
吴聊说:“我怎么了?老子带绿帽子了,老子当乌龟王八蛋了。”
我说:“安心偷野男人,这怎么可能呢?会不会是你弄错了。”
吴聊说:“弄错个鸡巴。半年前学校派我去省城考察学习一个月,结果我提前了一个星期回家,当我满心欢喜地打开防盗门之后,安心正被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压在沙发上。狗日的安心,她居然像一只发情的母狗一样一边折腾一边发出快活的呻吟,而那个野男人,身体则像拉锯一般,不停地来回。那一刻,我真想用斧头劈了这对狗男女,可是我不能把自己也悲壮地搭进去啊。这么一想,我就没有太大的愤怒了。我轻轻地咳嗽一声,当然这一声对我而言只是轻轻的,而对于那个野男人,应该如同晴天霹雳。他从沙发上抖索着滚下地来,抱起衣服撒腿就往外跑。我冲上前去,使尽吃奶的力气在他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那个野男人就一个饿狗抢屎,扑了出去。我骂道:‘下次你这个畜生养的再敢来,看老子不一刀宰了你。等我关好防盗门,安心已经穿好了衣服。她说:‘你全都看见了,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还是离婚吧。我说:‘离什么离,只要你下不为例,过去的事就算了。可是安心这臭娘儿们像铁了心,自己偷了男人却反而大闹着一定要和我离婚。因此从半年前起,我家就硝烟弥漫,没有过一天安稳的日子。”
我说:“安心怎么会偷野男人呢?”
吴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结婚后不久,我那玩意突然就不争气了。我不是一个男人啊。”
看着悲悲切切的吴聊,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猛刺了一下,无比的生疼。我提起一瓶啤酒,对吴聊说:“不要想那么多了,吴聊。来,我们喝酒。”吴聊提起酒瓶,我们使劲地碰了一下,“砰”的一声,吴聊的酒瓶碎了,啤酒全都倒在吧桌上,像无数泛着泡沫的河流,成辐射状流淌开去。
吴聊迷茫地盯着碎了的啤酒瓶,长长地叹了口气。
四
从“再回首”饭馆回到乌鸦市教育学院之后,吴聊和安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乌鸦市教育学院的背后,有一个名为“灵山秀水”的公园,虽为人工雕琢而成,但其景致之宜人,建筑之经典,在整个乌鸦市绝无仅有。特别是公园按照王羲之《兰亭集序》里的描绘设置的一条饶有趣味的“流觞曲水”,更是令游人大开眼界。闲暇或者不太闲暇的夜晚,吴聊都会邀约上安心,到“灵山秀水”浪漫一回,干一些未婚男人和女人该干或者不该干的事情。
临近毕业的时候,安心的肚子突然毫无预感地大了起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安心有些心慌,她没有一点做母亲的思想准备。她甚至还没有想好,到底要不要和吴聊结婚。
安心到寝室里找到吴聊,十分生气地说:“你是怎么防范的,我让你小心,小心,你却糊里糊涂地把我肚子弄大了。吴聊,你让我怎么有脸去面对别人。”
吴聊笑嘻嘻地说:“每次我都是全副武装的,你又不是不知道,可是即使天网恢恢,终归会有漏网之鱼啊。”
安心冷着脸说:“你正经点行不行。现在出麻烦了,你看怎么办?”
吴聊说:“既然怀上了,那就生吧。”
安心说:“婚都没结,你就让我生孩子。你是不是神经有问题。”
吴聊说:“那就先结婚?再生孩子。”
安心说:“说得轻松,结婚?你拿什么来结婚?房子?票子?既然什么都没有,那就别结婚了,我看我干脆去医院将孩子打掉算了,大家都是个解脱。”
吴聊伤心地说:“这是我们共同的孩子呢,安心,你就忍心?”
安心的眼泪就扑簌簌地流了出来。她哀怨地扫视吴聊一眼,车转身,逃逸似的跑出了吴聊的寝室。吴聊想喊住安心,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妈的,感情咋了,没钱照样得当孙子。”吴聊独自发了句牢骚,像一摊烂泥一样倒在铁床上,眼睛失神地盯着墙角网上的一只蜘蛛。那只蜘蛛逍遥自在地端坐在军帐的中央,悠闲得仿佛拥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一只挣扎的蚊子最终放弃生的念头,然后再以胜利者的姿态饱餐一顿。
“妈的,”吴聊自言自语道,“生活怎么就成了一张法力无边的网呢!”
“我算什么东西呢?”吴聊问自己。
那个阳光略显斑驳的春日的下午,吴聊的心境糟糕得像被人践踏的烂茄子,他那由琼瑶、岑凯伦、玄小佛等人炮制的言情书上建构起来的山盟海誓、卿卿我我的爱情观,在现实无情的敲打下,粉碎殆尽。“一切都是骗人的”,吴聊想,目光又不自觉地投向阴暗的墙角。那只蜘蛛依旧潜伏在网上,微风轻轻地拂动,蜘蛛便警觉起来。吴聊想:“它是在等待下一只自投罗网的猎物。而自己,到底是谁的猎物呢。”
整个下午,吴聊就死死地盯住那只蜘蛛看,直至眼睛酸疼得流出了眼泪,视线里一团模糊,没有了蜘蛛,没有了网,甚至没有了尘世中的爱恨情仇。
离开乌鸦市教育学院,吴聊通过在喜鹊县教育局工作的姑父的关系,留在了喜鹊县四中教书。而安心,则回到了从前的小镇。
日子像流水一样,经历了一些波折和跌宕,最后又终归恢复到平静。吴聊像小县城里的一只灰头土脸的甲壳虫,整天夹着营生的书本,穿梭在阳光或者风雨之中,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而这种毫无新鲜感的如同复制的日子,让吴聊真实地感觉到内心的空洞和压抑。
吴聊想:“如果安心在自己的身边,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景象呢。”
这样想着,吴聊就随手拿起了电话,按下了七个熟悉的号码。
吴聊说:“安心,你什么时候到我这里来呀?我们一起去重温一下喜鹊县特色羊肉火锅。”
安心淡淡地说:“我哪里消受得起。”
吴聊知道安心心里不痛快,对他有怨气,于是就说:“过去是我不对,你就不要生气了。即使你不为我考虑,也该为肚子里的孩子想想吧。”
提到孩子,安心在电话里就抽噎起来。安心说:“你这没良心的,还知道我肚子里有个孩子。”
吴聊说:“我心里其实一直都挺惦记你和孩子的。”
安心说:“就你那副德行,怕又是猫哭耗子。”
吴聊说:“天地良心,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安心说:“如果你说的是真心话,那就星期六来接我。”
吴聊忙说:“行,绝对没问题。”
星期六那天,吴聊将安心接到了喜鹊县城。他们一下车就去了羊肉火锅店解决温饱问题。吃完饭后,两人才回到吴聊的住处。吴聊租住在麻雀巷里,只有一间陈旧不堪光线极差就像老鼠洞般的屋子。屋子靠窗处是一张写字台,上面摆着凌乱的书本,以及梳子、镜子、香皂等杂物;中间是一个已经熄灭了的蜂窝煤火炉,火炉上放着一个烧水用的铝壶,铝壶盖上落满了灰尘;再往里看,便是一张用来睡觉的单人木床,床上没有蚊帐,被子像猪拱过的窝,被汗浸透得发亮。墙上贴着两张明星画:一张是仅仅穿着裤衩戴着乳罩的钟楚红写真,另一张则是一头长发一身牛仔打扮抱着吉他作摇头晃脑状唱歌的老狼。
看着吴聊邋遢的住处,安心不由得皱了皱眉头。
吴聊尴尬地笑笑,调侃说:“没有老婆的日子,简直不是人过的。”
安心说:“街上这么多漂亮女人,找一个不就得了。”
吴聊说:“我怎么舍得你呢。”说着,嬉皮笑脸地把安心抱到床上,急不可耐地去解安心裤子上的皮带。
安心说:“我肚子里有孩子,你小心点。”
完事之后,吴聊感觉有些睡意。安心将头枕在他的怀里,不停地用手挠吴聊的腋窝,弄得吴聊心里痒痒的。
吴聊坐起来,笑着将耳朵紧贴在安心的肚皮上。安心说:“你在干什么?”
吴聊说:“我听听孩子在你的肚子里捣蛋没有。”
安心没有接吴聊的话,眉头紧皱着,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吴聊说:“你怎么了?”
安心就紧紧地抱住吴聊,流着眼泪说:“吴聊,为了孩子,我们结婚吧。”
吴聊的心里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的。他机械地点点头,说:“那就结吧。”
五
离开“唐朝酒吧”,我和吴聊醉得像两摊烂泥,身上的骨头化掉了似的,一点力气也没有。我想扶住吴聊,吴聊也想扶住我。我们两人就你拉我扯地纠缠不清,最后两个都摔倒在大街上,爬不起来。这时一辆的士急驰而至,我心想这下完蛋了,见阎王去吧。狗日的吴聊,你戴绿帽子自己去死不就得了,偏要拉我垫背,老子冤啊。这样想着,的士一声刺耳的急刹停在了我和吴聊的面前,车上的司机怒气冲冲地跳了下来,指着我们俩破口大骂:“他娘的,活得不耐烦了,找死啊。”吴聊看着司机稀里糊涂地傻笑。司机以为碰上了疯子,骂骂咧咧地把车开走了。
我被吓出了一身冷汗,酒就醒了大半。
我使劲儿站了起来,伸手去拉吴聊,可是吴聊笨重得像一头死猪,在我的拉扯下纹丝不动。幸得几个巡警的帮忙,才将吴聊移到了大街边上。
我坐在地上喘气,吴聊含混不清地说:“刚才骂我们的司机是我孙子,你信不信?”
我没好气地说:“你才是他孙子。”
吴聊嘿嘿地笑,说:“张嘴,我们都是孙子。其实,全世界的男人都是孙子。”
我一下子无话可说。是啊,这大千世界上,又有几个人不是孙子呢?即使有几个不是孙子的,不也是在假装孙子吗?
夜色黑得像铁锅底似的,看不见一丝可疑的亮色,偶尔有风吹在脸上,带着几点雨星,那凄清的凉便一直浸透到心底,让人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惧。街上除了那些做皮肉生意的“鸡”们和那些不怕得害羞病的嫖客们而外,已经几乎没有行人。
我扶起吴聊,说:“我们回家吧,吴聊,我怕我老婆醒了担心。”
吴聊说:“要回家你自己回,我回家没意思。狗日的安心,她让我戴绿帽子了还要离婚,要不是看着孩子可怜的份上,老子王八都当了还怕离婚。”
我说:“你这样拖着也不是办法,问题总得解决。”
吴聊说:“孩子倒没什么,跟我不就行了。主要是安心将奸夫带到家里来乱搞,我觉得窝囊啊。”
我不说话,看着吴聊笑。吴聊使劲地给我一拳,也哈哈哈地大笑起来。吴聊说:“妈拉巴子,离就离吧,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双破鞋吗。”
吴聊想清楚了,心情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说:“张嘴,我们再去喝两杯庆贺一下,等明天我和安心到法院离婚之后,我就把酒彻底戒了。”
六
吴聊和安心结婚之后,依旧住在麻雀巷里,只不过不再是从前吴聊所住的那间老鼠洞般的破屋。他们租赁了一个套房,在三楼,采光极好。房间虽然不大,但布局合理,功能齐备,对于吴聊和安心而言,这种房间既经济又合算。
日子像流水一般地流失,而安心的肚子随着胎儿的生长,如同吹胀的气球,甚至可以清楚地看见分布在皮肤下面的毛细血管。安心穿着宽大的孕妇服,挺着大肚子在吴聊的陪同下,一天要在麻雀巷里走几个来回,两人脸上都闪动着幸福的光芒。
到了预产期,为了安全起见,吴聊和安心坐一辆三轮车到医院住下来。住进医院的当天晚上,安心的肚子就疼痛起来。吴聊非常着急。值班医生用戴着橡皮手套的手伸进安心的裆部检查之后,说:“还没有开始宫缩呢,还有一段时间,耐心等吧。”安心像猪嚎一般地叫唤了一夜,却依旧没有半点要生的征兆。
第二天凌晨,不知怎的羊水突然就破了,决堤一般地奔涌而出,将床铺打湿了大半,弄得吴聊又一阵紧张。羊水破了之后,安心的肚子却不疼了。吴聊问医生情况,医生说:“先观察一阵再说。你用卫生纸把你妻子的屁股垫高起来,避免羊水流完影响胎儿的呼吸。”医生们观察来观察去,到了下午,终于发现胎心不正了,才对吴聊说:“需要动手术,你赶快到财务室去把钱交了,到化验室去验血和尿检,以备需要输血时用。”
吴聊在许多份医院制定的协议上签了字。吴聊深知医院的协议是不公平的,但没有办法,时间不容延误,不得不签。这样,安心才被抬进了手术室。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在手术室外走来走去的吴聊终于听到了孩子“哇”的一声啼哭。吴聊的心一下子落回到胸腔里。“生了。”吴聊对身边的母亲说。紧接着手术室的门也随之打开了,医生将婴儿递给吴聊,说:“祝贺你,手术非常成功,母子均平安。”吴聊端详着手上的孩子,歇斯底里地喊道:“我当爸爸了!”声音在挂着“安静”牌子的医院楼道里回响。
在医院里整整呆了九天,安心的伤口才基本愈合。办完出院手续,吴聊有一种农奴翻身做主人的感觉。吴聊当然不知道,作为父亲,这其实仅仅是一个开始。作为丈夫,这也仅仅是一个开始。接下来的日子,吴聊依旧整天晕头转向地奔忙:忙着给孩子洗尿布,忙着哄孩子入睡,忙着给安心做饭,忙着招呼应酬来家里吃满月酒的亲戚和朋友。吴聊有时真恨不得把自己撕成两个人来用。吴聊甚至恍惚觉得,自己已经失去自我,变成卡夫卡笔下那个可怜的葛里高尔了。
在给孩子取名时,吴聊和安心发生了一点分歧。安心说:“孩子是个女孩,和我性别一样,应该改姓安。我已经想好了,就叫她安然。你知道吗?安然无恙,有祈求孩子平安之意。”
吴聊反驳说:“你这种观点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相悖,孩子历来跟父姓,如果和你姓安,那我变成什么了?”
孩子取名的事就因意见不一而搁置起来。转眼间,孩子已经满三个月了。吴聊想,家里长期冷战也不是个办法,这不仅伤害夫妻双方,而且还会伤害到无辜的孩子,便对安心和解说:“孩子已经满三个月了,今天天气不错,我们去凤凰山庄玩玩吧。”
安心也想和解,便说:“那就去吧。”
晚上回家,吴聊感慨地说:“我们俩大概有半年时间没有亲近了吧?”
安心说:“确切地说应该是半年稍多一点。”
吴聊说:“我们以后再也不要吵架了。我们即使不为自己想,也应该为孩子想想。”
说着说着,两口子就抱在一起了。等两人都赤身裸体之后,吴聊就气喘如牛地骑在了安心的身上。在要进入之时,吴聊却突然发觉自己刚才还雄赳赳气昂昂的物件这时就像疲软了的茄子,不争气地耷拉着脑袋。吴聊的内心倒抽了一口凉气。“我怎么能这样啊,”吴聊想,“怕是长期性压抑造成阳痿了。”安心等了半天不见吴聊的动静,便问:“你怎么了?”
吴聊像是回答又像是自问:“我怎么会不行了呢?”
安心气得大骂了一句:“狗日的没用的东西。”
七
我和吴聊头重脚轻地穿过燕子大街,沿着喜鹊河河岸走回麻雀小巷。我们俩都喝醉了,风吹在脸上,像蚂蚁在爬行,痒痒的,让人直想扇自己的耳光。吴聊想扶住我,我也想扶住吴聊,我们两个就你拉我扯地相互纠缠着往回走。
吴聊说:“张嘴,我明天就去离婚。”
我说:“离了好,离了你就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了。”
吴聊说:“离婚之后我就把酒戒了。”
我说:“酒戒了好,酒是一个勾魂的魔鬼,喝多了会要人的命的。”
吴聊说:“我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我说:“想哭你就哭吧,哭不哭与是不是男人没有关系。”
吴聊就撕心裂肺惊天动地地哭了一场。哭过之后,吴聊说:“我心里好受多了。”
我说:“我们回家吧。”
吴聊说:“回家。”
我和吴聊依旧相互搀扶着。喜鹊河的河水静静的,从漆黑的云层里漏出的几缕如丝的月光洒落其上,像镀了一层银粉似的,看起来很美。我心里其实明白,这夜间的美,不过是一种假象而已,没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就像生活中的许多物事,人是没有办法认真的。也没有必要太过于认真。
吴聊的身体越来越沉,越来越沉,快要崩溃了似的,我简直不堪重负。吴聊说:“张嘴,我想要呕吐。”
我说:“想吐你就吐吧。吐了感觉会好一些。”
我想将吴聊使劲扶住,吴聊也想努力站住脚步,但还没有等到站稳,吴聊就翻江倒海地呕吐起来。我说:“吴聊,你给我悠着点,免得把肝胆都吐掉了。”
吴聊说:“我的脑袋沉重死了。”
我说:“再重你也得给我忍住,坚持就是胜利。明天的新生活在等着你呢。”
吴聊说:“我简直受不了了,张嘴,我操……”
吴聊话没说完,我就感觉到自己的手里空空荡荡的。我突然意识到什么,绝望地叫了一声吴聊的名字,但吴聊没有任何回音,有的只是他的身体像炮弹一样落水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