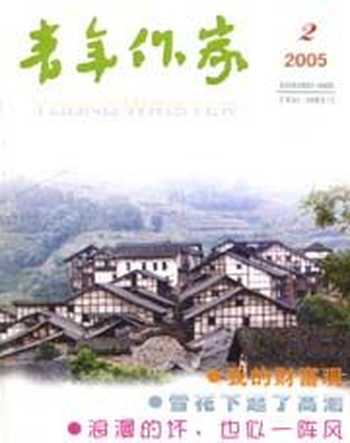生命伦理的诗性阐释
杨传珍 杜紫微
当写够了那些闪闪发光的思想随笔之后,摩罗的文学生涯才真正开始。他的第一部小说就写成了思想、信仰、学养与诗的结晶体。
杜紫微:我是摩罗思想随笔的忠实读者,反复研读过他的《耻辱者手记》、《自由的歌谣》、《因幸福而哭泣》、《不死的火焰》等随笔、评论集。我一直认为,摩罗能把思想随笔写到这个高度,就此封笔,在文学史上也会拥有不朽的地位了。没想到,他又拿出了这部名叫《六道悲伤》的长篇小说,在浮华的中国文坛上立起了一座青铜般的不朽丰碑。
杨传珍:《六道悲伤》的问世,说它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重大事件,可能为时尚早,但一点都不为过。我可以作个比喻,如果我们把中国新文学的先驱鲁迅先生比作俄国的果戈里,那么摩罗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六道悲伤》与老陀的《被污辱与被损害的》相比(我坚信,有朝一日,摩罗会写出他的《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无论是艺术高度、思想深度、信仰亮度还是作品之于作家的意义、对民族文学的贡献,前者都不比后者逊色。
杜紫微:在阅读这部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时,我完全沉浸在作品所营造的艺术氛围之中:她有着厚重深沉的血土气息,也有着清凉淙淙的怜溪水的气息,有着大鸣山神秘哭声的悲凉气息,也有着每天清晨浓郁而温暖的烟火气息。作者带领我们走进的是一个既特别又普通的南方村落,她坐落在鄱阳湖边上,几经兴衰,曾经被突如其来的蛇阵、虎阵灭绝,也曾被战火洗劫一空。故事就发生在这么一个名叫张家湾的村落里,那看似静谧的氛围之下正孕育着一场空前的浩劫。因为读第一遍时,完全被作品的内在力量所征服,我不得不读第二遍,以便站在一个适当的距离来欣赏评析。
杨传珍:你认为《六道悲伤》所表达的核心是什么?
杜紫微:核心是对所有生命的敬畏,是对一切尊严的肯定,对人类、对自然界的一切生灵、对社会、对文化、对善恶、对信仰、对生存、对宇宙、对过去现在未来,以及这些畴区之间的交叉关系的深层思考,并把这些思考提升到生命伦理的高度进一步审视,用存在论(而不是辩证论)的美学观作艺术本体意义上的阐释。《六道悲伤》是一部思想者、信仰者、学者的作品,也是一部诗人的作品。它的深度、高度、厚度、密度自不必说,仅作品所具有的诗性,就使得《六道悲伤》成为一部长篇小说经典。而且,它的诗性不仅表现在语言上,更表现在结构布局、人物塑造、环境描写、氛围营造上。当然,说它具诗性,并不是说它的思想性低于艺术性。
杨传珍:摩罗是以思想者的身份在中国文坛出现的。他已经发表的超过百万字的思想随笔,多是以理性态度对社会政治伦理某些方面的置疑,而不仅仅是对某些社会丑恶现象的批判。所以,摩罗在思想文化界刚一亮相,就和那些风云知识分子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体现出的是一个责任伦理主义者的高贵品格。而且,他早期的思想随笔,就隐含着由文化到哲学,由思想到信仰,由关注社会到关注生命本身的质素。到了创作《六道悲伤》时,这些潜在的质素走到了前台。我们不妨说,摩罗的随笔,虽然是汉语写作难得的精品,却是《六道悲伤》的铺垫和预演,是为了打造出这部大书而进行的创作心态和心力的准备。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人在去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之前先去处理的零碎事物。当写够了那些在思想文化界闪闪发光的随笔之后,摩罗的文学生涯才真正开始。所以,对摩罗的小说,我们不必担心其思想性,只怕思想的深刻与密集影响了诗性。可他毕竟是一个诗性化的思想者,第一部小说就写成了思想、信仰、学养与诗的结晶体。
人,喜鹊,蛤蟆,鸡,猪,狗,泥鳅,山,水,树,石,这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都有着活泼泼的灵性。
杜紫微:中国的文学,沉寂了半个多世纪。在鲁迅、沈从文之后,长篇小说创作一直是乏善可陈。再不出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五四新文学所倡导的精神就要脱气、断档了。
杨传珍:摩罗的出现,不仅续上了鲁迅、沈从文等文学大师的血脉,而且使得这一文学传统有了新的生长点。
杜紫微:什么生长点?
杨传珍:鲁迅是思想大家、美学大家、小说大家,勇于面对黑暗、承担痛苦,是心灵黑暗的在场者。他勇于把荒诞的存在还原为荒诞,从而彻底击碎了瞒、骗、躲的传统,穿透了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也穿透了中国美学。可是,鲁迅用阴、冷、黑、沉、尖、辣、烈的心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他那里,温煦和悲悯的比例太小,占主流的东西是敌意、荒寒、冷漠。究其原因,是鲁迅在面对丑恶时,采用的是“以毒攻毒”的策略。他企图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控制,结果反被他所憎恨的传统文化所伤。他的精神深处,缺少信仰之维、爱之维。而摩罗就没有这种局限,在他的作品里,那叙述者的声音虽然同样是大地荒寒在场者的声音,但字里行间弥漫着温柔、善良、宽容、纯洁、灿烂、坚强,罪恶之上,有爱、有信仰。摩罗超越了最初滋养自己的文化,也超越了自己。在超越中,不仅仅是批判、扬弃、否定、清算传统,而是向传统中注入新质。这种新质就是新的生长点。
杜紫微:《六道悲伤》中的男女主人公张钟鸣和许红兰,是作者倾其全部创作热情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我认为,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画廊里,都是新的成员。张钟鸣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怀有一颗异常善良而柔弱的心,在他的世界观里,一切生灵都应该受到应有的尊重。人,喜鹊,蛤蟆,鸡,猪,狗,泥鳅,山,水,树,石,这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都有着活泼泼的灵性。虽然这些人类之外的生命无法用人的语言与人的世界交流,但是,它们是人类不可忽视的同伴,同是自然的造化,享受着同一片阳光。人类与自身与周遭生灵的相处,应该是互相尊重互相关爱的,而不是互相残害。《六道悲伤》里的爱与恨不局限在人类自身,它还展示了人与人之外的生灵的关系,展示了人之外的不可忽视的生命存在和力量,展示了人作为人应该具有的美好的精神境界,由“人伦之理”扩展到所有生命之理。张钟鸣是一个弱书生,可他的弱却让他不能容忍任何生命受到不该遭受的伤害和欺侮。这种弱是一种高贵的品格,是基于对他类生命的认同与尊重之上的爱。同时,张钟鸣也具有另一种弱,那就是在面对冷酷无情的现实生活时,不由自主地被外在强大势力所左右的软弱,这是让人心疼的软弱,为了自己的这个弱,张钟鸣的内心充满了无限痛苦。他直面自己的软弱,与自己的灵魂进行斗争,因而,他的痛苦是常人难以体会的。
杨传珍:福楼拜有一句自白,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自己。”我认为,张钟鸣是一个彻底的生命伦理主义者。这个人物,有作者自我审视的因素,从他身上,可以发现作者的影子。普通读者心目中的摩罗,是一个血性十足的知识分子,他敢于面对黑暗,揭露丑恶。但是,那只是他内在精神的一个方面。如果你细细品味摩罗的随笔,透过表层向深处看,他那些关于社会结构、政治道德、秩序伦理的追问与审思,其底色和根基是利他、尊严、敬畏、信仰,他没有将自己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停留在对各种不合理社会现实的抨击、批判上,甚至也没把改善政治源头作为自己的目的,他的思索和言说,是为了安置“更大的秩序”,即“造物主的记忆”,最终,通过建立生命伦理,实施对茫茫宇宙间一切生灵的保护、悲悯和拯救。而现实生活中的摩罗,也是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从他的随笔中读到的那个写作主体形象,正是作者真实内心的流露。而张钟鸣,则是随笔摩罗的丰富和延伸。
整个文本充满了宗教情怀,对所有苦难而又罪恶的生灵怀着深沉的爱和悲悯。
杜紫微:是的,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在《六道悲伤》里,摩罗不止在张钟鸣这个人物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另一个人物——许红兰,也是经过作者精心塑造,是世界文学人物的画廊里第一次出现的形象。许红兰原先是上海滩的妓女,为了爱情,为了寻找一个归宿,嫁给了纪文波,来到张家湾这个血汪汪的湖畔村庄。可是,没过多久,恩爱的丈夫就被人暗算。作为一个世俗中的女人,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安全感,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全部。在这种情况下,她仍然是善良、美和爱的化身。因为有了这个光彩照人的女子,张家湾这个冷硬荒寒的村庄里才有了温暖的色调。她承担了作为女人应该和不应该承担的全部苦难,却用女人能够付出的善良和仁厚呵护着别人。作者给他安排了一个乡村医生的角色,村里的人,谁有了小伤小病,马上想到去找许红兰。有一次,许红兰自己的手碰破了,站在一旁的张钟鸣竟脱口而出“去找许红兰!”我认为,让许红兰担当“医治者”的角色,这是一种象征,她在用自己微弱的力量,不仅疗治人们身体的伤痛,也疗治人类心灵的伤痛。她的爱,就像她家旁边的悲忻潭水一样,清澈甘甜,滋润着一颗颗受伤的心灵。只是,这种力量太微弱了。
杨传珍:许红兰身上体现出来的这个光明与爱的生长点,并不微弱。正如美学家潘知常先生所说,“光明与黑暗并不对等,而是远在后者之上;爱与恨也不对等,而是远在后者之上。”作者明写这种力量的微弱,实质上,是暗示这种力量的韧性与强大。
杜紫微:许红兰这个人物很值得认真分析。她身上有着丰富的人性,仁厚的母性,慈悲的佛性,普世的神性。在大队书记章世松对她实施强暴时,没有真正反抗的许红兰闻到一股强烈的狐臭味而呕吐起来,表面上不可一世而内心深处极度自卑的章世松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地要拿别人出气。许红兰预感到了这场恶作剧将会伤害无力反抗的无辜者,于是,她不顾尊严忍受委屈去安慰章世松。此时,她甚至在潜意识里为自己无意中对章世松造成的伤害而忏悔。由于章世松还没能从挫败中走出,怒气未消,他用训斥和轻蔑拒绝了许红兰的献身。然后,以“专政”的名义,杀害了在石壁上画圣像的知识分子何幸之。这个时候,小说呈现的是这样一幅画面:许红兰以虚弱之躯,背着死去的何幸之从圣母像前走过,倾其全力安抚一个不可能复活的生命。这个场景,实在撼人心魄!而当张钟鸣实在不能容忍章世松的恶行,想去告发时,许红兰却又劝戒张钟鸣放弃这么做,她认为,冤冤相报,只有增加更多的伤害。许红兰的这种态度,发自她的生命本性,而这本性,天然地具有宽恕一切的宗教情怀。
杨传珍:小说里还有一个重要人物——章世松。对章世松这个“坏人”的塑造,作者既写了他借助权利作恶多端,又写了“精英统治”的传统社会给这个卑微者的心灵深处造成的伤害。他的恶行,是一个受尽屈辱的无知者在反抗、报复情绪处在高涨时突然被赋予神圣权利之后的所作所为。作者是用耶稣的心肠来对待这个人物的。这是一个被精英传统、流氓政治、等级文化、势利社会、谎言风潮、暴力统治扭曲出来的怪胎,他的人性深处,勤劳、坚韧、忠诚、责任的成分大于流氓、无赖、残忍、偏执的成分,是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急剧扭转,把他推到一个让他作恶的位置上。其结果,不仅害了一方乡亲,而且害了家人,葬送了自己。
杜紫微:《六道悲伤》的整个文本充满了宗教情怀,对所有苦难而又罪恶的生灵都怀着浓郁的悲悯之情。这让我想起一句话:“不能原谅和悲悯犹大的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听你对章世松这个人物如此一番的分析,是不是可以说:不能悲悯章世松的读者,还不能理解摩罗。
杨传珍:正是这样。我觉得,作者通过张钟鸣这个人物,将自己的当下承担推到了前台,而许红兰,则是作者的期待自我或理想自我,作者把她的忍让理解成更高远更形而上的承担。在章世松这个人物身上,则集中了几千年来的弱势群体的血泪。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之后,章世松这种人并没有获得文化、道德、心理、名分意义上的翻身,自认为高贵者(其实与他并无根本区别)仍然视他为卑贱者,他自己也没摆脱掉卑微者的心态,他承担不了时代强加给他的历史使命。作者站在这样的历史高度审视章世松,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同情。作为生命伦理主义者的摩罗,对章世松这个人物的悲悯,远胜于对其他生命的悲悯。
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当中,存在一种强盗逻辑,小说真实揭示了这种强盗逻辑给无数小人物、小生灵带来苦难的悲剧。
杜紫微:小说中还有一个小精灵一样的女孩张若雨,那么善良,聪慧,心灵丝毫没有受到功利社会的污染,凭着生命直觉,她经常说出一些常人想不到却直逼天道核心的话语。这个小女孩,可以说是善良的化身,是天使降临人间。可是,她却死了,无辜地为有罪的人承担了苦难。作者如此安排,实在令人心痛。
杨传珍:你回忆一下《被踩死的屎壳郎》那一章,就会明白了。
杜紫微:那一章主要是一场讨论,发生在张钟鸣与常修文之间。常修文看到一只勤劳的屎壳郎费了好大力气,团了一个粪球朝自己的窝里推,另一个不愿出力的屎壳郎却闯过来打劫,勤劳本分者与强盗争夺起来。常修文因为还要接着劳动,没有耐心和时间等着看结果,可他又不愿留下悬念,就一脚踩死了那只勤劳本分的屎壳郎,让强盗获取了粪球。之后,常修文就此向张钟鸣发表了一番宏论。这个细节,我认为是塑造常修文思想、性格的一段重要笔墨,也是张钟鸣剖析人性的一个精彩段落。
杨传珍:但是,从另一个方面,作者是要通过这个细节告诉读者,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当中,存在一种强盗逻辑,这种逻辑会侵入到社会无意识、政治无意识、历史无意识之中,导致张若雨死亡悲剧的发生。
杜紫微:揭示了这些残酷的无意识,是否就能唤醒人们去努力改变呢?
杨传珍: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说:“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力量还重。”作家没有能力消除罪恶,但有责任真实地揭示罪恶。因为,第一,罪恶能够导致悲剧,掩饰罪恶或对罪恶视而不见,导致悲剧的概率就会增大。让麻木者、偏盲者、概念化的惯性思维者正视罪恶,可以减少苦难,减少悲剧发生。作家的良知和社会责任,往往要通过揭示罪恶体现出来。第二,苦难本身固然是悲剧,世人对发生在身边的苦难一无所知则是更大的悲剧。要使苦难为人所知,让苦难有出声的机会,就不能从表层揭露,而要从深层揭示。这必须借助于审美文体,用虚构表现真。在这个意义上,审美是通向真理的捷径。第三,一个人早年受了苦,若后来成为强者,那么他的苦涩和苦难自然就转化成了财富,甚至甘美。若当事人始终是个弱者,他就没有诉说苦难和悲剧的勇气和机会,许多苦难和悲剧就会被历史的风烟尘埋。文学是为小人物立传的(王鼎钧语),揭示强盗逻辑给无数小人物带来苦难的悲剧,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的使命。我想,摩罗就是出于以上考虑,才作出这种揭示的。
杜紫微:只是,这些真实的文字实在太残酷,读来让人心酸。
杨传珍:作家杨烽说过,“真实的东西常常是残酷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真实;谎言往往是美丽的,但我们不能相信谎言。”作家的责任是写实,包括残酷的真实。
杜紫微:《六道悲伤》就准确地揭示了那场大动乱之前人们的心理状态,让我们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揪心。
《悲忻潭》一章的性爱描写,是能够进入艺术殿堂的经典,其气氛、感受、激情、欲火,都用高密度的诗性文字表现了出来。
杨传珍:摩罗是一位诗性思维的思想者。在出版了四五部随笔集,成为文坛翘楚之后,安下心来,历时五年打造一部长篇,表现他的生命伦理,其沉稳的精神品格让人敬佩。这部作品,将汉语的审美写作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杜紫微:你是指形式和语言吗?
杨传珍:在形式上,《六道悲伤》是真正的复调小说,而且是结构匀称的浑厚复调。语言的诗化,让我联想到《当代英雄》和散文译本的《神曲》。但它不是欧化的,而是纯正的汉语气韵。这些,还都不是最重要的。《六道悲伤》对汉语小说的贡献,是它内在的精神,是弥漫在字里行间的那种逼人的美。整部作品简直就是一团晶体,处处闪射着美与善的光辉。书中的任何一个细节,任何一处铺垫,都是塑造人物性格的活生生的器官,都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链条,都是表达作者思想和信仰的火花,浑然一体,无一处游离。而每一个小的单元,都蕴涵着丰富的内容,让人处处都能见到大的境界。《悲忻潭》一章中的性爱描写,我现在就敢说是能够进入艺术殿堂的经典。英国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有几处美不胜收的性描写,但那太单一,只能说是唯美主义的。还有几位大师级的作家,写性时,有的是为了表现罪恶,有的则暗示性即肮脏。而人类的性行为,既不是罪恶也不是肮脏,而是美,是感情和精神力量的飞升。因为前有劳伦斯,摩罗在呈现张钟鸣和许红兰的那场惊天动地的性爱时,加进去苦涩与悲凉。那样的社会大环境,那样两个对生命、对美有着形而上理解的苦命人,在那个月光如水的悲忻潭边,体验那样的身体与灵魂的碰撞,其气氛、感受、激情、欲火,都让作者用高密度的诗性文字表现了出来。那种境界,那样清澈的美,说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光辉的篇章,一点都不为过。
杜紫微:摩罗对人性的挖掘、把握、展示、表达,都具有直逼核心穷尽内蕴的力度与厚度。在《大呕吐》一章里,写章世松强暴许红兰未成的场面,其丰富性、合理性,不仅是对过去此类描写简单化、模式化的警告和超越,更是对人性的昭示。此时此刻的许红兰,被权势者威逼的女人,被作者还原成了人,不再是作者拉来利用的符号。左拉说:“我把作家看作是上帝之后使一个世界诞生的创造者。”在这里,摩罗站在一个女性生命的心灵深处,伴着她的酸楚与期盼,生出对这样一个孤苦女性的无限的同情,创造出一个苦命但完整而真实的女人。作为一名女性读者,我认为,摩罗是真正读得懂女性世界的作家,他赋予许红兰的尊重和同情,是来自男性写作者的一种难能可贵的真情。如果作家本人缺乏这种真情,他是很难深入到人物内心的,又谈何打动读者呢?
杨传珍:是的。摩罗小说的张力很大,当你读到激烈场面,总是感到心酸,读到苦涩的描写,又让你心中充满希望。这是大手笔的标志,大境界的体现。当然,大手笔、大境界来自作家的大胸怀,即信仰者的胸怀。
杜紫微:我也能感受到作品里弥漫着《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宗教情怀。
杨传珍:以“五四”为发端的中国新文学,一个重要的源头是俄罗斯文学。鲁迅先生就直言不讳地承认,他的小说受到果戈里的影响。之后,俄苏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始终没有间断。但是,我不得不说一句让很多人不舒服的话:《六道悲伤》是第一部俄罗斯文学内在精神在中国落地生根的作品。它吸取的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善的和恶的)的丰富营养,沐浴的是俄罗斯精神中最高贵的阳光,结出的是中国气派的果实。
你无法分辨是写实还是魔幻,这不是从外国文本中摹仿来的魔幻,而是直接来自生命体验的、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式魔幻。
杜紫微:还有中国式的魔幻。
杨传珍:你的感觉很对。这些年来,许多中国作家,今天学习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明天摹仿卡尔维诺和布尔加科夫,但谁也没有成功,只披了一张外国作家的皮,不伦不类,还自以为得了人家的真经。摩罗的小说,是从作家的生命深出喷射出来的另一个生命,你无法分开是写实还是魔幻,但那些场景、气氛、形象、精神是那么和谐统一,又是那么撼人。正如你所说,这不是从外国文本中摹仿来的魔幻,而是直接来自生命体验的、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式魔幻,是艺术家创造出来的“第二世界”,而不是用学来的技术组装的冒牌货。
杜紫微:血土,石头精,孬孬与老虎,虎阵,哭声,杀猪,葬礼,鄱湖长调,这些章节无不焕发着魔幻的神采;厚重的历史传说,传奇的傻子的预言,神秘的傩舞与悲凉的唱腔,在张家湾这块土地上织出了一幅五彩斑斓的生命锦缎。在这里,美统摄了一切,作家将具有普泛意义的内心苦痛转化为令人销魂的音乐,完成了划时代的精神涅磐。
杨传珍:我认为,《六道悲伤》中所呈现的痛苦,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创作主体内心痛苦的折射,作者所揭示的一切都源于自己那颗承载苦难的心灵。他通过这部作品,在耻辱中寻找尊严,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荒寒中寻找温暖,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化解苦难中寻找做人的幸福,为灵魂寻找信仰。他的信仰,不是人间天国,不是哪一种具体宗教的神,而是对生命的敬畏,是从自身做起的善待一切生灵。这样的作品,超然物外的文人写不出来,勇于建造“憎的丰碑”的文化斗士写不出来,它只能出自一个在精神上勇于承担人类全部罪恶的生命伦理主义者,一个为全人类祈祷的普世宗教的圣徒,一个用诗性思维洞悉整个人类本性的艺术思想家的生命深处。在这个意义上,《六道悲伤》是摩罗的,也是人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