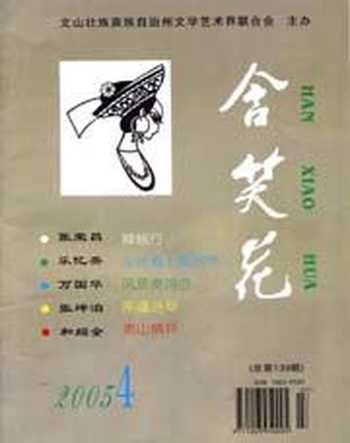屋 祭
杨启波
家是我们出发的地方
零的起点
死与生的模式变得更为复杂
——艾略特
前年春天,家里来电话说要拆掉老屋重建新居了。不知怎的心里顿时就涌起一股莫名的怅然。我连忙从千里之外赶回家,带着相机,我想把有关老屋的所有记忆,都定格在胶片上,让它们成为我日后痊愈乡思的一味良药。
然而当我风尘仆仆地赶回老家时,我却沮丧地发现,面对老屋,端着相机,我却不知到底该往哪儿人手,不知到底该把哪些东西留下来。我这才知道,即使能拍下一些相片,也仅仅是表面上的东西,有关老屋的所有记忆,都是刻在心头上的。无论从哪个角度,哪个层面,都无法找到能抵塞铭刻在心底的任何一个角落啊。
老屋是一间很平常的滇东南民居,座西向东,瓦房,三格,泥土春的墙,木板做隔墙。这样普通的老屋,记载的却是我成年以前的那一大段成长的欢笑和梦魇!记忆最为深刻的,应该是老屋中的这盘小磨,这座灶台,这个火塘,还有就是这个神龛了。
老家在乡政府所在地,每逢到星期四是赶集天,母亲就会蒸点卷粉,炒几个小菜,在老屋前摆个小摊,每星期一摆一次,做点小生意贴补家用。
这盘小磨可就派上大用场了。用来磨米浆、豆浆。每到星期三这天,我和二弟任务就重啦。中午放学回家,吃完饭就开始推磨,上学前把米浆磨好,母亲蒸着。等我和二弟下午放学回来继续推,二弟够不着磨把,用一条长凳子垫着,母亲背着三弟把泡好的米放进磨眼里。一圈又一圈,一星期又一星期,一年又一年,慢慢的二弟不用凳子垫了,再后来我一个人也推得动了。
我和二弟是很愿意推磨的,虽然很累,但在星期三这天晚上却可以吃炒卷粉。至今我仍然对炒卷粉情有独钟,怕就是那时养成的习惯啊。
更令我们哥俩兴奋的是,母亲许诺第二天每人发一角钱。对一个孩子来说,一角钱是多大的概念啊!可以买糖,一分钱两颗的那种;可以买小玩具,五分钱或是一角钱。有时也买冰棒等等,反正用途多着呢。有时候看见小伙伴吃糖而我没有钱,就非常地盼望星期三快点到来。推磨累了的时候,就老想着明天的糖,明天就有糖吃了,多有诱惑力多鼓励人的糖啊!后来长大了,现实的残酷,令我每每遇到迷惑和困顿,我总是对自己说,明天的糖是会有的,一定会有的。就是这样的“糖”,促使我不断向前奔走。
灶台在西南角,泥土舂的,一烧火就满屋子的浓烟,呛得人直流眼泪。我是老大,又无姐妹,所以很小就学会了做饭。个子小,够不着,我时时请邻居来帮我把甑子抱进锅里。父母干活有时回来很晚,特别是农忙时节,更是“两头黑”。遇上这种时候,我就把锅里的猪食铲出来,把锅洗干净,把甑子放在锅里蒸着,等母亲回来炒菜。我则领着弟弟们在灶门前,烧一小堆火,相倚着等父母回家。有一回,邻居没人在家,我抬条凳子垫着,试着把甑子抱进锅里,凳子一跷,连人带甑子摔倒在地,饭撒了一地,甑子也摔烂了。父母回家虽然没骂我,但我还是很内疚。所以我以后做事总是很小心,老怕自己的“甑子”被摔烂了。
难忘灶台的原因,其实还是因为吃的关系。那时总觉得随时都在想着吃,肚子老饿,所以一回家就往灶台那里跑,看看有什么可以吃的。哪怕锅里煮的是猪食,母亲也会把整个的芭蕉芋或是芍药煮在里面,掏出来用清水一冲,用刀把皮削了,可好吃啦。
还有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可别提有多令人兴奋呀!母亲在灶台上切肉,我们哥仨在灶台边流着口水,眼巴巴地盯着菜板上的肉。母亲便笑着骂了,小馋猫!骂完就开始分肉了:这是老大的,这是老二的,喏,这是老三的。哥仨来不及比谁的大小,拿着一溜烟小跑开了。其它和二弟偷吃的事就不提了,记忆深刻的还有端五节。端五节那天,因为要上学,所以老早就猴急急的站在锅边,吸着口水,眼睛盯着锅里的粽子,在母亲“还不熟不熟”的责骂声中抓两个提着就跑了。母亲包的粽子五颜六色,香甜可口。十四岁那年,我把母亲包的粽子写进我的作文里,题目叫做“粽子飘香”,竟然获得县作文竞赛一等奖。母亲用深深的母爱褒奖了我的喜悦,端五节再次来临的时候,我的大部分同学吃上了母亲包的粽子。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那种被夸奖的幸福之音包围的滋味。
火塘在老屋的西南角。在我的记忆里,火塘是老屋中最为温馨的地方了。有一段时间父亲经常在外做工,家里只有母子四人。夜晚来临时,母亲烧起火,我和二弟枕着母亲的腿,三弟在母亲背上甜甜的睡了。母亲边打毛线边给我们讲故事。我最记得的是母亲讲的“输三不抵信二”的故事,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大意是做人做事要讲“诚信”。但我们通常是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还有神龛,其实就是一张普通的柜子,我在那下面跪过两次!并不是祭奠祖先,而是因为我做错了事。一次是我和同学打架,被父亲拉来跪;另一次是我和二弟去摘人家的黄瓜,被母亲拉来跪。直到如今,我做事也是很小心,因为在我内心深处,总有一张“神龛”雄赳赳地横立着,时时提醒着我。
喔,还有,还有那盏马灯。我上小学四年级时,老师要求上晚自习。下自习我不敢独自回家,因为中间要经过一座坟地。我总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就大声叫唤母亲,等到看得见母亲开门提着那盏马灯出来的灯光,我才一溜烟小跑着回家。那时就觉得灯光是那么的温馨,而家,又是多么的安全呵!在老屋里,我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尽管后来我上了师范,个头已比母亲高了许多,母亲还会爱怜地拢拢我的头发,或是理理我的衣领。也许是母亲过多地宠我,直到今天,我偶然表现出来的孩子气,被别人惊愕地瞪大双眼注视着我时,我才蓦然醒悟:我面对的不是母亲呀!
还有那张我们哥仨睡过的床,那时觉得很大,现在竟那么小了。还有,还有——可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随着老屋的拆除而烟消云散了!而母亲,我可怜的母亲,已去世九年了,在她四十二岁生日即将到来的时候,她踏着夕阳的残血走进她那小小的房屋里。
有人说,死人是活在活人心中的。等到活人再死去后,那个世界发生的所有悲喜故事,再没有人知晓了。直到今天,我也没有拿母亲的相片去画遗像,甚至连母亲留下的惟一的一张相片,也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并不是我不怀念母亲,我以为,画张哪怕是极像的相片摆着又有什么用呢?我不想让我的孩子指着像框里的人问我那是谁,我不能将一个抽象意义的“奶奶”以及那个悲惨的故事强加给她,我的孩子是无辜的,她有权利享受健康的生活。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母亲的一举手一投足,还有她死后人殓时变形扭曲的脸庞。无论任何相片,都没有我心里的这张真实、逼真。母亲去世多年,我仍时时在梦中见到不同时期的母亲。在我心里,母亲永远是那样的年轻,而母亲也绝对没料到,她的儿子已沧桑得两鬓霜花了。八年前我填过一首怀念母亲的词,其中有“竟惊然、儿改妆”的句子,现在想起来,仍不免觞怀吁吁。
现在,老屋终于被拆除了。嵌入我多年情感的老屋的最后消失,我灵魂的栖息地已不复存在,联系的纽带断了,是否就意味着我将像浮萍一样浪迹天涯?
老屋,我沉重的老屋!你就像一个渡口,我乘着理想的船儿驶离你的码头,在一个又一个晨曦来临又离去的日子,我没有目的地,只有到达一个个码头又一一的离去。我——成了一个永远没有目的地的流浪儿!当我面对我的新居茫然失措,当我面对“新”的人群惊恐彷徨时,我总是想起你——我的老屋!
哦,老屋,我沉重的老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