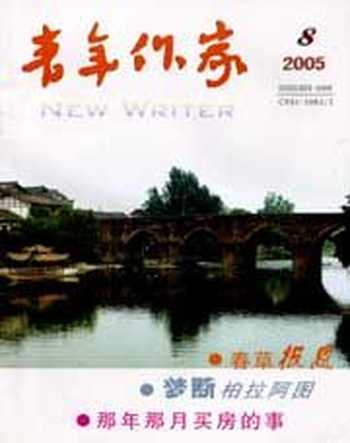临时舅舅
丁 援
我的儿子枫枫对邮票发生了兴趣。星期天,我把历年来收集的、亲朋好友馈赠的邮票,一起拿了出来,和他一同欣赏。其中一本邮集的封面呈暗蓝色,正面烫着一个金色的美国国徽,已经退色了,边角也有些磨损。翻开封面,扉页上印着:
Souvenir of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an Francisco: 1945
我对儿子说:“这是爸爸最珍爱的邮集,它是中国著名作家萧乾爷爷采访第一届联合国大会时所得的赠品。后来,萧爷爷把它转送给了爸爸。萧爷爷已经去世了。”抚摩着邮集,不由得想起我和萧伯伯相处的日子。于是,我给儿子讲起了我和我这个“临时舅舅”的一些往事。
我从部队复员后,被分配到北京光电技术研究所当钳工。拿着二级工的工资,干的却是学徒的工作。每当看见所里的工程师们坐在明亮的设计室,面对图板,驰骋在设计的方案中,我心里无比地羡慕。
我决心自学成才。数理化学起来比较容易,最让我头疼的是英语。我的母亲与萧乾先生和他的太太文沫若女士相识,于是介绍我拜萧伯伯为师,学习英语。
我每星期去萧伯伯家一次,把我在一星期学习中的疑难告诉萧伯伯,由他释疑。他每次给我留下作业,待到下次去时为我当面批改指正。萧伯伯特别重视英文造句,强调学以致用。有时候,萧伯伯会对我说,你的这句话从语法上讲没有错误,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不能这样说,太不客气了,显得粗鲁。跟着萧伯伯学习,使我受益良多。
记得有一次,我写的句子文法错误太多,改动之后仍然不通顺,我心里很焦躁,丧气的话冲口而出:“英文太难了,算了,不学了。”这时候,萧伯伯的表情严肃起来,他说,在学术上和事业上,不要轻言放弃。放弃是容易的,可是那样既辜负了亲友们的期望,也辜负了自己过去的努力。萧伯伯教我英语,也教我治学的精神。他的教诲使我终生难忘。
每次教授完英文,萧伯伯都会和我天南海北地聊会儿天。聊我插队、当兵时的趣事,聊萧伯伯在“五七干校”的往事,聊人生百态,也偶尔涉及政治时事。
萧伯伯告诉我,他愿意和青年人聊天,近距离观察他们,从中挖掘写作素材,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作品中的人物。后来,他告诉我的母亲,他的一部作品中的人物有我的影子,让我读读那本书。可惜那时,我正准备出国,忙忙碌碌的,没有拜读那部作品。
萧伯伯是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和记者,然而他总是谦称自己是一个老报人。在左倾横行、黑白混淆的年代里,萧伯伯被打成了右派,文革中又受到迫害。萧伯伯的生活和写作环境很恶劣。我去他家学习期间,他住的是两间平房。外墙呈灰色,已经是斑斑驳驳,而且,房子较一般平房要矮,确切地说,还不如一些大户人家的门房。房间不过十平方米左右,他平时写作的那间屋里,有一张已无法说出颜色的三屉桌,两把椅子,一张单人床,两个书架并排靠墙,架子上塞满了书籍,显然已负荷过重,书架周围的地上也堆满了书和文稿。当我和萧伯伯分别坐在椅子上时,几乎膝盖顶着膝盖。
每当我看着萧伯伯顶着一头已见稀疏的白发,在昏暗的台灯下奋笔疾书,总有一股悲凉的感觉。尽管环境如此,萧伯伯却不以为然,总是那么乐观诙谐。我想萧伯伯的世界一定是在他的写作中,那儿有他美丽的殿堂。
至于他怎么又成了我的“舅舅”,这可是由一段特殊境遇撮合的呵。
1975年的一天凌晨,我在熟睡中忽然被惊醒了,耳边响起轰轰隆隆的声音,就好像火车开进了家门。母亲惊慌地喊:“快起来,地震了!”我滚下床,准备穿上长裤。我一条腿独立,试图把另一条腿塞进裤管,可是,由于地板在动,单腿立地根本站不稳,用了两三分钟才穿好裤子。折腾了好一会儿,全家人才惊惊慌慌地下了楼。
这时,院子里已有稀疏的人群。在昏黑的夜色中,人越来越多,尽都瑟瑟缩缩地站着,小声谈论着。大概是由于人们经过的磨难太多,即使发生了地震,也没有大呼小叫的,大家都默默地承受着所发生的一切。
地震中,钢筋水泥楼房都会晃散架,不知萧伯伯住的破旧平房怎么样了。我心里想着无论如何要抽空儿去看看萧伯伯,也许他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天渐渐亮了,人们慢慢散去。听了广播才知道,唐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地震,北京只是受到波及。广播里说还会有余震,要大家做好应急准备。
我先去上班。研究所的领导组织了值班纠察队,我是其中的一员,领导要求我们吃住在所里。在我不当班的时候,我赶紧去看了萧伯伯。
萧伯伯那里还好,从外表看,房屋依旧,这大概得益于房子低矮,但内部结构上有无损坏就不得而知了。听萧伯伯说震感不如楼房强烈,当然还是受了惊吓。平时不和他一起居住的大儿子回来过了。在儿子的帮助下,把一个单人床叠到他的床上,床腿对床腿,用钉子钉住。“立木顶千斤”,萧伯伯说就是屋顶平平落下来,他在下面的床上照常睡觉。我想,这真是北京人说的“穷凑合”。
接下来,地震的风声又紧了,余震不断。一天,我当班的时候,又来余震,眼瞅着所里大礼堂屋脊上的小石狮子骨碌碌地滚了下来,所有的玻璃窗都在哗哗啦啦地响动,声势惊人。让人们再次见识了大自然的威力。唐山人的凄惨伤亡的消息又陆续传来,人们更加忧心忡忡。萧伯伯也不再提他的有安全系数的双层床了。
上级发下了木头,各家在空旷的广场、街沿、院子里搭起了地震棚。如雨后春笋,一夜之间到处都是地震棚。我家动手晚了一两天,就找不到地方了,只好去和朋友住在一起。朋友的地震棚位于长安街的人行横道上,离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不过百米,离天安门也在五百米以内。空地如此难找,萧伯伯就更找不到搭地震棚的地方了。远的地方没有,近处更不行。墙外的胡同里,别说是搭地震棚,就是摆上一张方桌,汽车也得会跳高运动才能过得去。怎么办呢?
天无绝人之路。在那天下午的全所职工大会上,所长宣布:为了帮助所里职工渡过难关,所里把还在建设中的职工食堂开放,供无法建地震棚的职工和他们的直系亲属居住。
这个研究所是新创立的激光技术研究所,基本建设还没有完成。食堂只有四面墙,没有内部装修。已有照明设备。房顶也刚刚铺好了油毡,还没上瓦,可以算做“轻型”建筑吧。更可贵的是,在它的周围没有任何高大的建筑。因此,它虽然不是十全十美的避震设施,也称得上出类拔萃的地震棚了。
当时所里有很多通过各种关系进来的职工,包括一些高干子弟。他们不需要使用这个避震设施,另外部分职工在住地附近抢到了地盘,建起了地震棚。所以,申请的人不算多。对于一个准备容纳两百人进餐的地方来说,足以敷用。
可是领导讲了,必须是职工和他们的直系亲属,怎么弄出一个直系亲属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走后门了。我所在研究室的党支部书记平时待人很好,对我们年轻人更是重在教育,耐心帮助,大家都尊称她佟老太太。她是著名中共地下党员王甦先生的妻子。王甦当年为了北京市和平解放做出了杰出贡献,如果你看过“平津战役”这个电影,就会知道他的大名。所以,佟老太太在所里讲话很有分量。我便想到去找她。
找到了佟老太太,我告诉她,我的“舅舅”住在小胡同里,找不到地方搭地震棚。他的房子在上次地震中可能受了内伤。我的“舅舅”已经六十多岁了,腿脚不灵活,一旦遇震,就可能发生危险。可不可以让老人暂时住在所里的食堂里,一旦找到了搭地震棚的地方,立刻搬出来。佟老太太不愧为老共产党员,同情心就是强,她毫不犹豫地说,既是这样就让你舅舅搬过来吧。你去登个记,就写职工亲属,是我同意暂住在食堂的。
真像接到了特赦令。我赶紧打电话给萧伯伯,让他尽快搬过来,这样可以占据一个比较靠近大门的位置,便于进出。萧伯伯当天就来了。我们用红砖搭了四个砖垛,放上萧伯伯请人运来的床板,就算是一张床了。萧伯伯带来了简单的洗漱用具、正在创作的文稿,也带来了心爱的鼻烟,那是萧伯伯提神的专用品。于是,萧伯伯就在食堂里暂时住了下来。
等安顿好了,我告诉萧伯伯,如有人问起你就说你是我的舅舅,是所领导批准住在这里的,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萧伯伯笑着说:“你放心,我会当好这个‘临时舅舅的,你去忙你的吧。”
第二天早晨,我去看望萧伯伯,只见食堂里到处是地铺。萧伯伯正坐在小板凳上,以床铺为桌子,笔耕不止。其实我每次见到萧伯伯,都是这情景,他的手中总是握着笔。他似乎一辈子都离不开那支笔,后来在他八十岁高龄时,还和文阿姨携手合作,用了整整五年时间,付出巨大心力翻译了英国著名意识流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尤利西斯》。那毕竟是后话。而这次在这样的特殊时刻特殊环境下见到此种情景,就自然会让人产生不同寻常的感觉了。写作何止是他的生命呵!我颇为感慨地叫了一声萧伯伯,他才不得不停下了手中的笔。
萧伯伯不改诙谐,告诉我,他有了新邻居,是个中年的工人师傅。他主动向那个师傅作介绍,说他是我的舅舅,当然没有加上“临时”两个字。那个师傅一听,便对萧伯伯非常照顾,帮他打开水,还带他熟悉周围的环境。后来,那个师傅告诉萧伯伯,说我是他的徒弟。
我一听,这回好了。我的师傅章之辉成了萧伯伯的邻居。章师傅是个待人热情豪爽的人,有了他的帮助,我就放心了。得到了章师傅的认同,萧伯伯就正式成了我的“舅舅”了。
在所里居住期间,萧伯伯每天骑车回家去吃午饭和晚饭。好在他家离研究所不远,十分钟的骑程,来去还方便。不过,提起萧伯伯的车技,还真替他捏把汗。毕竟萧伯伯那时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腿脚不再灵便,反应力也不够敏捷了。萧伯伯在一篇杂文里还提到自己的车技。他别了人家的自行车,那人说他:“你会骑车吗?”得,他的骑车资格就给“取消了”。我还读过他的这篇京味十足的散文。
萧伯伯是个乐观的人。他对这个大地震棚很满意,对邻居也满意。他幽默地说,这里真不错,比家里的小房子凉快多了。是啊,这里房高屋大,没门没窗,夏天还行,如果地震警报不解除,一直闹到冬天去可就糟了,那就太“凉快”了。
幸亏地震警报在秋天里就解除了。生活恢复了正常。我又去跟萧伯伯学英语,直到恢复高考。
我和萧伯伯的师生友谊一直保持着。我喜欢集邮,萧伯伯知道后,把他作为记者采访第一届联合国大会时获赠的一本邮票集送给了我。我一直珍藏在身边。
萧伯伯已经作古了,但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永远值得我怀念。萧伯伯的音容笑貌和对事业的执著,永远地刻在了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