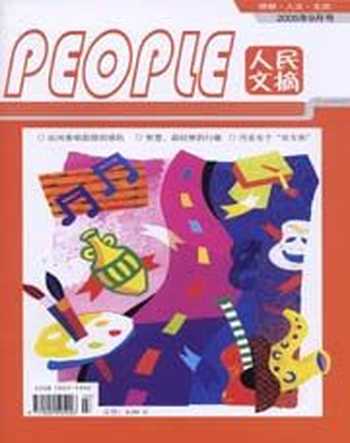后现代派钢琴家
罗露西

一个雨天的傍晚,我和爱丽丝正在住地附近的酒吧里聊天。一位男士拿着一杯威士忌走来。爱丽丝告诉我,这是钢琴家派克。第一眼见到派克,我就觉得他有些与众不同。
他50多岁,大大的脑袋,一头灰白色的长发齐耳微卷,身材不高,健壮如牛。爱丽丝向他介绍我,我站起来和他握手。当那双巨大的方型厚手,握住我的手的时候,我似乎感到有许多音符从那手里飘出来……
见到派克,爱麗丝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看得出她很喜欢派克,尽管派克小爱丽丝许多岁。爱丽丝告诉我,派克是一位后现代派钢琴家,在英国、法国、德国小有名气,广播电视都采访过他。他不但演奏,还演唱和作曲,也举办过个人音乐会。
派克坐下来和我们闲聊起来。
派克喝着威士忌。我从正面直视他,那英俊宽阔的脸上神情很严肃。它让我想起德国贝多芬博物馆前的贝多芬雕像,那是一座一看就永远也不会忘记的雕像,而且每当想起那尊雕像,都能与命运交响曲联系在一起。眼前的这位派克,蓝色的眸子里传递出的一种与音乐结缘才有的神秘感,迫使我去探究他。
“你为什么要作曲?”我主动发问。
“启发人们去思考。”他简洁地回答。
“我喜欢古典音乐,特别是那些不是太沉重的古典音乐,像肖邦、贝多芬、李斯特、勃拉姆斯、舒曼、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曲。”我一口气说了一大堆人名。
“你生活在一二百年前,我生活在现实,我的音乐表现的是现代。”派克说。
“和古典音乐相比,对现代音乐,我几乎一点不懂,有的现代音乐很难理解,很狂躁。你的音乐是后现代音乐,那么什么是后现代音乐呢?”我又问。
“你可以去看我的网页,那上面有介绍。”他拿出纸和笔写下了他的网址。
喝完了威士忌,派克站起身和我们道别。派克走后,爱丽丝告诉我,她认识派克很多年,他和一位法国女友,住在酒吧斜对面一幢昂贵的有几百年历史的老房子里。
晚上回来,我马上打开电脑,上网查看派克的网页。我仔细地浏览他的背景介绍。他毕业于伦敦大学,主修哲学。后来进入皇家音乐学院,学习钢琴和单簧管。毕业后一直从事音乐创作、演出和钢琴家教。网页上,转载了大量报纸杂志对他音乐的评论文章。关上电脑,我似乎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单相思状态中。
第二天,我一个人到了酒吧,不为别的,就为能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再见到派克。我坐在一个朝向窗外的位子,这里可以看到每一个进入酒吧的人。8点多钟,派克来了。我主动和他打招呼。他从吧台买了一杯威士忌后走过来,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位子上。我心里有些激动,又想尽量掩饰心中迅速增长的对他的爱慕,但还是按捺不住先开口了,“昨夜我查看了你的网页,真没想到你是一位前卫的音乐家。”派克边喝酒边讲述起他的生活,似乎并不想谈音乐。他讲起了自己的故事。他出生在伦敦,父亲、祖父都是律师,他没有兄弟姐妹,曾有过一位从事美术创作的女友,并有一个女儿。现在,女友和女儿都在美国,女儿已经结婚,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派克点起了一支烟抽起来,显得有些忧郁,像在思念女友和女儿。
“你应该到中国去举办音乐会,后现代派音乐对于中国听众来说,也许是很新的东西。”我对派克说。
“我需要钱,很多演出赚不了什么钱,销售音乐碟也不容易。做钢琴家教,有时赚钱不少,但要看人脸色。一次,我教一位贵妇的儿子弹琴,后来,她突然终止了合同,原因是她的婚姻出现问题,她甩给我1万镑。钱不少,可那一刻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我不愿受人摆布。”派克讲着,我仿佛看到那些伟大的音乐家们都曾经历的艰难的画面。

音乐家似乎都肩负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看着派克那双大大的方型厚手,就知道那就是为钢琴而生的。
一会儿,派克对我说,“你等一下,我去拿一盘碟给你。”然后走出酒吧,直奔街对面那老房子的家。十几分钟后他回来,递给我一张碟,“你回去听一下,里面是我的代表作品。”
晚上回来,打开音响,放入音碟,音乐响起……钢琴的演奏带来一片宁静,静得有些压抑。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一直认为现代音乐就是要给人以强烈刺激,而派克的音乐却恰恰相反。由他自己作曲、自己演唱、自己配器的音乐,每一个音符都是他心底之声。音乐结束后,我不想再听,它产生的死一般的静,正好让我很快进入了梦乡。
早上起来,我强迫自己再听一遍派克的音乐,以便晚上能与他谈听后的感受。这次我坐在音响旁,一动不动从头听到尾。突然我感到一种极度的来自音乐的失望情绪,这是昨晚听时没有感觉到的。许多不和谐音出现在过于缓慢低沉的旋律中,像一潭死水,没有波澜。也许他的音乐很棒,但我无法理解它。音乐结束,关掉音响,我好像是在受着压抑的煎熬,心情一下变得很不好。这种音乐我绝不想再去听它。
晚上又见到派克,我们坐在酒吧的一个角落里。他还是喝着威士忌,我喝着爱尔兰的黑啤。我把碟还给他,“感谢你让我知道什么是后现代音乐。”我说。
“你的感觉怎样?”他看着我,用浑厚纯正的男中音问我。
“钢琴的音质是一流的,音色极其优美,那一定是一架很好的琴。音乐太静,太悲了,像葬礼曲,或失败之歌,这样的音乐听多了会影响情绪,产生负面影响。”我直截了当地说。
“你说对了,那是架古钢琴,祖父留给我的。”他低声讲完,没有再说话。那一晚,我俩静静地喝着酒,没有情绪再谈音乐,我被他的音乐彻底打倒。三天里我对他产生的那种“单相思”骤然降温。音乐让我从他那强壮的身躯、英俊的脸庞和为钢琴而生的大手这些优越的外表中,探测到了一颗深藏的悲凉的心。
我要逃脱他,就像逃脱他的音乐一样。我不愿与阴郁为伍,我喜欢快乐和阳光的性格。
(罗有能摘自《下午茶》安徽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