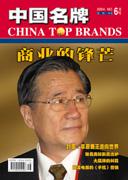百年传奇荣宝斋

1964年,一个男青年来到荣宝斋,索价1500元想卖掉手中的物品。在30余件字画里, 有苏轼题李公麟的《三马图》题跋、 北宋范仲淹的《师鲁二扎》的残缺部分等国宝,而稀世珍品宋代书法四大家之一的米芾《苕溪诗卷》竟然赫列其中,一时令荣宝斋的店员目瞪口呆,难以置信专家认为,这批文物如果拿到现在的市场拍卖,至少值几千万。
稀世珍品《苕溪诗卷》惊现荣宝斋
1964年的一个清晨,一个男青年拿着一个布包来到京城琉璃厂的荣宝斋,要求卖掉包中的物品。
店员打开包裹,只粗粗一瞥,便马上被包中的物品惊呆了:在这个破布包裹里,共有字画30余件,虽鱼龙混杂,却有一批国宝级的文物!其中有苏轼题李公麟的《三马图》题跋、北宋范仲淹《师鲁二扎》的残缺部分,宋代书法四大家之一米芾的《苕溪诗卷》,这可是米元章的两幅传世力作之一,只此一件就可称之为稀世珍品。《苕溪诗卷》共分两部分,前半部分在国民党撤退时被带到了台湾,而最精彩的一部分则早在溥仪离宫时就被带出了紫禁城,后流散于民间。建国后文物专家苦苦寻觅,一无所获,而这次,稀世国宝居然不请自到,真是喜从天降!
荣宝斋的老人侯恺、郑茂达、米景扬等回忆起当时来还印象深刻。那次具体接待的一个叫王大山,一个是营业科的副科长田宜生。都是荣宝斋干了多年的人,眼力还是有的。当时就问这个青年,这东西你打算卖多少钱。青年说你们看着给吧。田宜生说,东西是你的,要卖多少钱得你说呀。这个青年有点不好意思的说,给我1500元行吗?店员心里清楚,这可不是1500元的东西,可是也不好去挑明了说,最后只能说,你看这样好不好,现在快中午了你先吃饭,吃完饭咱们再商量好不好?
为了进一步确认这批文物的真伪,和判断它的实际价值,国宝出现的消息被迅速汇报给了国务院、文化部的一批领导、以及在京的文物鉴定专家。所有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激动不已 。
米景扬回忆说,那时候我在编辑室工作,我们上午有15分钟休息,我一般都到门市部去看画,那天一去,我就看出大家都非常紧张。我说怎么回事,买着宝贝了?这个时候,门口来了很多辆汽车。当时文物局的正局长是张葱玉,好像副局长是王冶秋,还有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这些都是对文化贡献非常大的,都是非常喜欢中国书画艺术的,这些领导就来了,我记得齐燕铭来的时候就兴奋得蹦蹦跳跳,那个门槛一跳就往里走。
经理侯恺回忆说,当时来了好多人,就在我那办公室,一大堆东西,那气氛很紧张的。许多东西领导和专家都很熟悉,连画作上有什么伤痕、残缺,大约什么时候流落到哪里,什么时候又转到哪里,张葱玉讲的很清楚,如数家珍,听上去真了不起。
郑茂达说,这批东西是国家的重要文化财富,是没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有专家说,如果一定要用金钱来衡量,那么估计再高也不为过。那个青年要价1500块钱,跟这批东西的实际价值相差很远。在当时,就是给他一万五千元、十五万元也不为过。如果拿到现在的拍卖市场去拍卖,至少得值几千万。但是经验告诉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给多了,给多了会使卖主产生很多想法,甚至把他吓跑,东西留不下来。所以当时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把这青年稳住,把东西留下来。他们觉得对方要价1500,还他1400比较合适,因为这样比较接近他的要价,比较自然。商量之后就这么定下来了。下午3点之后,那个青年按时来到荣宝斋,他没二话就接受了荣宝斋1400元的还价,办完手续点了钱就走了。
当时的荣宝斋经理侯恺觉得,这么多重要的文物能保存下来,是给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1400元和实际价值相差悬殊,所以报请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同志,希望能给予那个青年奖励。当时文化部为此还特批了一笔奖金,并由齐燕铭同志出面,请东北有关领导在报纸上对于那个青年保护文物的行为给予高度的表扬。但由于那青年留下的地址不详,以及紧接着的四清运动和十年浩劫,使这件事竟成了一桩悬案。

荣宝斋倾力收购中华流失国宝,众大师顶礼膜拜书画极品之作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处于政权更迭的时期,久藏于深宫大内、王孙贵胄府中的珍宝、名迹大量流散于民间。加之,民国的动荡社会局面,更导致了这些珍宝的频繁异主,这也就造就了中国古玩民间交易的一个黄金时期。
其实,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每到改朝换代,文物典籍必遭浩劫,同时也必然导致大批珍贵文物流散民间。以国宝《韩熙载夜宴图》为例,这幅创作于南唐时期的作品,在南唐灭亡后便进入了宋代皇宫。元初重又流散于民间,后转为皇室所有。明初重又为私人获得。从乾隆帝留下的“太上皇帝玺”中可以看出这件珍宝最后又进入了清廷大内。民国初年,《韩熙载夜宴图》再次流散于民间,被张大千买下,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从这串复杂的记录中,我们可以发现,文物除了乱世流散于民间这个定律以外,到了和平年代,随着社会稳定必向中央集中。
建国后,政治和经济的稳定为文物的回流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这时文物也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形成回流。然而,进入20世纪随着西方势力的入侵, 民间文物交易的活跃直接导致了大批珍贵的文物流向海外。建国初期,由于许多技术上的难度,仍无法有效避免文物的外流。侯恺说,那时没有明确详尽的规定,只是讲对文物有个限制,叫乾隆以上的不能出口。可是海关他也不懂的,比方写着乾隆,一看这不能出口肯定扣住了,它没有写乾隆,那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了,也就出去了。
与其封堵出口,不如掌握源头。对于这个问题,当时最为有效的解决方式,就是国家出面,请一批文物鉴定的行家里手,到民间收购这些珍贵的文物。这样不但可以使流散民间的文物得到更有效的保护,同时也最大可能的避免了文物的外流。公私合营后的荣宝斋不但具有国家资本的背景,而且在琉璃厂上百余年的经营,也使它具备了文物鉴定方面独到的能力,所有这些条件使得荣宝斋成了执行这一文物收购计划的最佳选择。
对于文物收购来说,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具备鉴别这些文物真伪的能力,所以收购之人至关重要。画家许麟庐,师从齐白石,精研师道,深得老人书画的精髓。五六十年代凭着自己在书画方面的造诣,他参与并见证了荣宝斋的文物收购活动。对于鉴别书画的真假,许麟庐说,鉴别真假,必须要看得多,见得广。因为我看得多:看过他早年的,中年的,晚年的,也看过他在纸本上画的,在绫本画的。怎么知道真假呢?只可会意不能言传。就是看得多了,自己知识丰富了,再加推理判断,就能辨别出它的真假。
在这一时期,荣宝斋收购的文物中明清书画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这不仅因为明清两代是中国画创作的一个高峰时期,而且这个时期的创作风格和技法对于我国现代书画家的影响极大。荣宝斋所藏的这批任伯年的作品对徐悲鸿的影响就极为深远。
许麟庐介绍说,徐悲鸿先生最喜欢任伯年,他说生我的那天,就是任伯年先生去世的那天,所以他对任伯年的画非常有感情。徐悲鸿画人物画的衣纹技法,都脱胎于任伯年。所以看看悲鸿画作里衣纹的转折,都是吸收了任伯年的画法。他有一个册页,专门刻了一方图章叫“悲鸿生命”,在任伯年的每张画上都打上悲鸿生命。
相较任伯年对徐悲鸿先生的影响,齐白石则更加推崇徐渭的画风。明代画家徐渭是中国大写意画的先驱之一,齐白石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白石老人曾说过:恨不得早先三百年,去为徐渭研墨、理纸。
荣宝斋收藏的一幅徐渭的“杂花卷”,宽30厘米,长4米有余, 每段缀以七言绝句一首,绘有八种花卉 。此卷被齐白石先生鉴定后认为是中国写意画中,可欲而不可求的极品。
正当荣宝斋在一步步打开收购局面的时候,形势的变化却让它不得不加快自己在各地的收购步伐。六十年代,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许多珍贵的书画作品被化入“四旧”,认为是历史的糟粕。在这种环境下,文物在民间的保护变成了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当时文化界的一批有识之士认识到保护这些文物的迫切性,同时也加紧了文物的民间收购行动。当时文化部规定,不能跨地区收购文物,而对荣宝斋却实行“特殊的文物政策”,不仅允许他们到全国名地收购,而且为其给各地文物部门出具了大量的介绍信,甚至为此拨出了大笔专款。
许麟庐回忆说,那个时候的价钱简直没谱,要跟现在比起来没法比。现在一张画上百万、几十万。那时候上几千了不得了,别说上万了。任伯年吴昌硕这两大家都在上海,当时过去近百年的画以及古代的画,因归为四旧了,就不值钱了。有些收藏家认为这些画都不值什么,所以在上海那个时候,20来块钱一张,买吴昌硕的画,买任伯年的画,成箱地向北京运。
仇英是明代四大家之一,工临摹,擅画山水、人物,作品工细严整,设色华丽。他的《松溪高士图》则以墨笔小写意的手法绘成,一反其作品风格,是他作品中极少见到的。近年同等价值的作品,拍卖多在数百万以上。而当时的收购价却只有区区几百元而已。

绝迹契丹版大藏经山西惊现,耗时九百天枯朽残片修复完好如初
随着收购文物的日渐增多,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荣宝斋的面前。
收回的这些文物经过数百年的流传,很多已经变的残破不堪。然而,对于荣宝斋这样的一个收藏机构而言,收藏的目的更多的在于研究和保护。特别是对于许多古旧书画来说,只有经过修复和装裱后,才能最大限度地恢复文物原有的面目。公私合营后,琉璃厂上一批有名的装裱和修复技师被吸收进入了荣宝斋,一度使荣宝斋的装裱和修复力量,堪舆故宫博物院相媲美。在荣宝斋的众多修复工作中,最受瞩目的、也是最能体现其修复能力的,是对一批辽代大藏经的修缮。
大藏经是佛教的一部大百科全书,它不仅收录了大量的佛经和历代高僧的重要著述,还记录了佛教发源地印度的部分历史和民俗。这部经书在它的发源地印度已经失传,只有汉文大藏经还流传于世 。有史料记载其中犹以辽代所刊印的契丹藏版本最为上乘。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这批经书在辽代以后,竟然绝迹人间。历经数朝,有无数收藏家和僧侣对它们苦苦寻觅,但始终未果。
1974年,在对山西省境内的应县木塔的一次维修过程中,文物工作者意外的在第四层释迦佛的肚子中发现了绝迹已久的契丹版大藏经,但它们因长期受潮,已粘连如棒,无法展观。几经辗转这批经卷被送到了北京的荣宝斋。
对于契丹版大藏经的修复可以说集中了荣宝斋最强的修复力量,其中就包括了北派装裱高手张贵桐和王家瑞先生。他们因修复了唐代《女娲图》和明代钟钦礼的《山水》等大量古旧书画,而在业内享有盛誉。明代钟钦礼的山水在文革中被当作四旧,撕成了上百张大大小小的碎片。1979年,荣宝斋以25块钱收购了这幅作品,修复国手张贵桐师傅采用北派整托的办法,恢复了这幅画的本来面貌,使它又重新获得了原有的艺术和研究价值。
在车间主任冯鹏生的安排下,张贵桐、王家瑞和李振东先后加入到契丹大藏经的修复工作之中。这次修复工作虽然集中了荣宝斋最强的修复力量,但因经卷破损严重,修复它们的难度,仍是始料不及的。当时存放经卷的佛像腹中,不巧被一窝黄鼠狼占为巢穴,结果可想而知,这批珍贵的佛经让黄鼠狼弄的一片狼迹,许多珍品都无法展观。是否能将她们重新组合,成了人们心中一个极大的悬念。张贵桐和王家瑞先生凭着多年修复的经验,使荣宝斋得以配置出特制的药水。在药水的作用下,那些粘连在一起的经卷终于得以展开,湮没了数百年的契丹版大藏经得以再一次展示在世人的面前。
在四位师傅的细心拼接下,这些经卷一件件得以修正和复原。然而,其中一幅辽代的佛像却给他们留下了极大的遗憾。这幅佛像在修复完成之后,却发现找不到眼睛、鼻子等重要部位的残缺部分,等于这幅珍贵的佛像虽然修复完成,但却留下了严重的缺陷。当时王家瑞和冯鹏生两位师傅,经过分析后大胆推断,如果这些碎片还有留存的可能,那只能在一个地方——仍在佛像腹中。此时距最初发现这批经卷已过了一年的时间。人们都认为,这个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然而在两位先生的坚持下,又重新打开了佛像,竟然真的从尘土中筛出了几张碎片。重新装裱后,这几张碎片,恰恰和丢失的部分完全吻合。
修复这批珍贵的文物前后共耗时九百多天,荣宝斋将契丹版大藏经从一堆枯朽的残片,还原到现在的样子,是复原书画上的奇迹。

荣宝斋藏品田黄石——令玉称臣的“石中之帝”
以南纸店起家的荣宝斋不但对历代名家字画情有独钟,而且对文房四宝也关爱有加。单就印章和珍贵的石材来说,就在荣宝斋的藏品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其中的田黄石、白寿山石、鸡血石,无论数量和质量都为国内众多收藏单位所罕见,特别是有“石中之帝”之称的田黄石更是倍受瞩目。
印章雕刻专家郑槐忠介绍说,天黄石被誉为石中之帝。自从田黄石出现,有了这么一句话叫做“令玉称臣”。玉石的历史非常悠久。战国时候,一块和氏璧要换十五座城,这个大家都知道。一直到清代,乾隆也非常喜欢玉。历代帝王都喜欢玉石,玉是帝王玩的石头。田黄石出来了,就令玉俯首称臣,可见天黄石它的价值。从清代以来,就有“一寸田黄一寸金”的说法。随着开采的加剧,田黄的矿源基本已经枯竭。从乾隆以后就很难再有大型的田黄出现。到了今天一寸见方、质地上乘的田黄,拍卖多在百万以上。
上个世纪的80年代,福建省寿山乡有人带话给荣宝斋,说在他们那里发现了一块重达4.5公斤的田黄石,令荣宝斋将信将疑。经过几百年的开采,如此级别的田黄石,几乎不可能再有了。但同时他们为这不确定的信息极度的兴奋:真的会有这样的石中之帝么!
当时参与收购的米景扬回忆说,1986年,福州搞寿山石的一个人姓陈,到我们这儿来了,说寿山乡发现一个4.5公斤重的大田黄。这让我们大吃一惊。荣宝斋的收购人员袁良说,这么大的在天黄里面属于王了。古往今来,这么大的天黄十分罕见。一般就是有个斤八两的就算大的了。这个八九斤重那就是相当大了! 后经过荣宝斋上下的协商认为,无论这个消息是真是假,都必须到福州的寿山乡一探究竟。因为这可能是荣宝斋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袁良回忆说,当时是五个农民拥有这块石头,一般人他不让见。陈耀华跟他们关系不错,把我领去以后,能够我让见见石头,这就很不简单了。米景扬回忆说,看这个石头并没在村里头。当时,我看从对面山梁上很远,有个人夹着一件雨衣走过来了,敢情这块石头就夹在雨衣里。确实是一块无价之宝。经过几次三番地谈,后来他跟踪到我们住的旅馆,查了登记簿,知道我们确实是北京荣宝斋的,才肯相信我们。价钱谈妥以后,他们表示不要汇款,就要现金。
经过协商,双方以13.5万元的价格成交。由于当时还未发行50元和100元面额的人民币,这笔巨款便是一个庞大的体积——现金整整装满了一个旅行袋和两个大纸箱。把这笔巨款从北京带到福州也颇费了一番周折,甚至连最后上山的消息也严格加以保密。
现在收藏于荣宝斋的这块田黄石,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田黄石石材之一,而其价值已无法再用金钱来衡量了。
稀世珍品《苕溪诗卷》收购背后的真实故事
当荣宝斋的文物收购行动已经过去多年后,萦绕在他们心中最大的悬念,还是那次对于米芾《苕溪诗卷》的收购。
当年的那个青年到底是谁?他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国宝级的文物?在他的背后还会有别的神秘人物吗?其实,早在文物收购的当日,在场的我国著名文物鉴定专家杨仁恺先生就曾说过:捐献的这批文物,虽然大多都为残片,但每一件都是国宝级文物。由此可以看出,若无相当的文物鉴赏能力,是绝然作不出这种选择的,在这个青年背后一定还有更加神秘的人物。
时隔30多年,一份地方报纸上刊登的文章,却让人们重新看到了解开这个谜团的希望。1996年3月30日,哈尔滨的《新晚报》登载该报记者圆小铃寻访那个青年及其母亲的文章。为解开重重谜团,《探索·发现》栏目的摄制人员来到哈尔滨,找到了七年前写下这篇报道的记者圆小铃。96年圆小铃采访时,当年的那个青年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时隔七年圆小铃对他的真名已经记不清楚,这次是否还能找到他是个疑问。另外,在那次捐献的文物中,大多为清廷大内所藏,如此众多的国宝级文物,又是如何流散于东北的呢?原来,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00多年的清王朝,但仍在紫禁城内保留了一个“小朝廷”。根据当时的《清室优待条例》,中国历代王朝深藏于大内的名迹、珍宝仍由溥仪支配。在溥仪所著的《我的前半生》中有多处这样的记载:“我们行动的第一步是筹备经费,方法是把宫内最值钱的字画、名迹,以我赏溥杰为名,由他带出宫外,溥杰每次下学回家必带走一大包,这样的活动几乎一天不断的干了半年多”。当时的溥仪受他的老师庄士敦的影响,一心想到欧洲留学,他原想把这些珍宝变卖后作为留学的费用,也备离宫后的生活所需。但随着溥仪重建大清国的梦想,这批国宝又同他一起来到了东北。
圆小铃回忆说,大约是我去的第五次还是第六次,我说我还想听听你谈过去的事。那天孙曼霞(化名)声音特别小,说话的那种语调特别慢,经常是说几句话然后就沉默好长好长时间,沉默的时候我就发现她手有点发抖。
以下是她讲的往事。青年人丁心刚(化名)的父亲丁征龙(化名),早年毕业于东北大学政治系,曾留学德国和法国,后受张学良的资助,进了日内瓦大学。卢沟桥事变后回国,在张学良北京办公处工作。1945年8月调往营口大桥煤矿。9月8日,他告别妻子,与朋友骆大昭、王学武一起去长春看望同学和老师。时值日本投降不久,长春街上许多小摊贩手里都有从伪满故宫流散出来的文物。丁征龙懂得这些古物的价值,花钱买下了一批字画和字画碎片。
9月20日,孙曼霞在营口听到了不幸的消息:有人在营口附近的铁路边发现了自己丈夫的尸体。同时,与丈夫同去的骆大昭也来到家中告之自己的丈夫是被流窜的俄兵所杀。就在当晚,矿上的一名矿工悄悄来到家中,说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事情经过。他说我认识你丈夫,几天前我也去长春了,去长春回来的时候,由于没钱买票是扒火车回来的,当时躲拉苹果筐的货车里面。离开长春不久,他就听见车里面有人打架争吵,然后就是互相厮打的声音,后来就听见有人喊救命,再过一会儿车箱里就没有动静了,他吓得躲在筐里也不敢声张。回到矿上的第二天,他听说有人在离营口很近的一个小站的郊外,发现了她丈夫的尸体,因为当时车上特别黑,所以并没看清人的容貌,但从声音上判断,喊救命的那个人极有可能就是她的丈夫丁征龙。孙曼霞得到这个消息后,冷静下来回想,发现骆大昭所说有许多疑点。经过一番查访,孙曼霞认定杀害自己丈夫的就是同行的骆大昭。原来事发当晚,同行的骆大昭红了眼,暗起贼心,于9月20日,在搭乘货运列车回营口的路上将丁争龙杀害,夺走了字画。孙曼霞当即告发骆大昭的罪行。骆大昭在铁的事实面前供认不讳。孙曼霞终于为丈夫昭了雪,并在枪毙骆大昭那天,拿回了那批字画和丈夫的遗物。
转眼到了六十年代。孙曼霞日渐感到这些字画长期放在家里不是回事。在她看来,纸这东西说完就完,把它保存下来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万一有个闪失,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死去的丈夫。最终她下定决心,为它们寻找一个更为妥善的去处。这就发生了六十年代哈尔滨青年向荣宝斋捐献文物的一幕。而荣宝斋则把这批国宝无偿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为它们寻得了最终归宿。
荣宝斋的藏品,虽故事各异,但今天它们都静静地躺在库房之中,无言承载着中华瑰丽文化的异彩,也必将烛照后来。
数百年后,相信人们依然会记得,有这样一个地方,曾是众多中华文物宝贝的栖身乐园,那就是,琉璃厂上的百年老店——荣宝斋。
——从任伯年到徐悲鸿”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