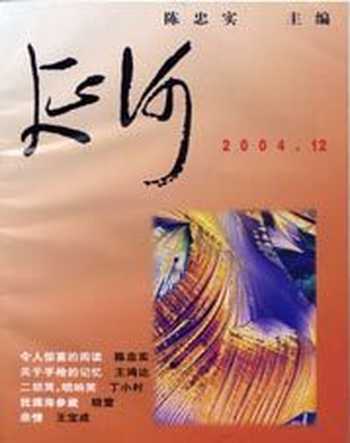亲情
繁华世界,漫漫人生,金钱、财富和权力耗费了多少人的视线和精力,又由此衍释出多少生活的悲喜剧?然而认真盘点,仔细思量,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恐怕还不是这些,而是感情。而在感情世界里,占核心位置的大概就要算亲情了。
一
九岁以前,母亲留给我的印象比父亲要多,然而九岁以后,就只有父亲了。记得是一个秋日的黄昏,父亲把我从正在上学的建庄小学叫出去,一条腿半跪在地上,拉着我的小手说:“你妈把心瞎了,撇下咱们父子俩跟旁人走了。”话未落音,眼泪就刷刷地流了下来。从这以后,我们父子俩就相依为命地度过了近五十年的岁月,父亲成了我心目中最亲近的人。
父亲是一个记忆力很强的人,他能把三国、水浒和很多民间故事大段大段地讲给周围的人听,但遇到大事却往往拿不定主意。和母亲离婚以后,他找到结拜的大哥顺儿说:“大哥,兄弟遭了家难,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你给我指一条明路。”顺儿抽着旱烟,思谋了半天说:“宝成妈离婚后,就住在佛爷砭,离咱芦峪村不到二里路,看样子是丢心不下娃。你如今就这一根独苗,万一让引走了,你这一辈子如何下场?你有蒲城先人留下的老底子,何必死守在这山旮旯里?叫我说你不如脚一跺,咳一声,一口顽痰唾利,领上全家回蒲城老家去,重起炉灶过自己的日子!”父亲听了这位大哥的话,刚过罢年,先以回老家拜年为名将我从当时的宜君县建庄乡引回到三百里路外的蒲城县花王村,寄养在伯父家里。第二年春天,就举家搬回了花王村。对于我们这个家来说,这是一次战略性的转移。从此,我就失去了母亲的音信,在父亲和祖父祖母的照管下,开始了艰难而又漫长的求学生涯。
本来就没有什么家底,又有五口人吃饭,全靠父亲一个人挣工分,养家糊口成了问题,还要供我上学,父亲所受的难场可想而知。父亲多次用试探的口气和我商量还能不能上学,看到我态度非常坚决时,总是满脸的愁苦,又不愿挡我上学的兴头,就只好硬着头皮往下供。但每到新学期来临时,父亲又总是忍不住要提出退学的事。初中三年级那一年,发展到了最严重的时候,那时已经进入可怕的饥荒年代,父亲就像一头精疲力竭的老黄牛,实在没有力气再拖着这个破败的家庭漏船向前走了,就再一次正式向我提出了退学的问题,我一口拒绝了。父亲生气了,说我不懂事,难道要吃他的肉不成?我被父亲这话刺痛了,就自己动手挖药,捉蝎子,烧草木灰,期盼给自己挣够学费。然而一个暑假下来,只攒了不足三元钱,不到学费的三分之一。这时,父亲开始心平气和地和我讨论重新返回北山芦峪村的问题,说川道这地方,日子实在不好熬,不比从前在山里,只要地里种下。囤里就能打下;冬里上山伐木解板,钱也来得方便;地头堰边,随便刨几撅,撒把菜种,白菜、萝卜全有了,秋里腌上两缸,一冬一春碗里不淡。父亲说得不错,但我心里明白,返回北山就意味着停学,这是我无论如何都不愿接受的。直到开学的前一天,父亲从炕席底下取出一张早就借好的拾元人民币交给我说:“下了一场雨,秋粮也许有指望。既老天爷促红你,就去上你的学吧。”
当我考上高中以后,父亲彻底打消了让我停学的念头,和已经有点力气的妹妹拼命在生产队劳动,全心全意地供我上学。心想上到这一步,挡也挡不住了,念到高中毕业,兴许能找到一个挣钱的饭碗。然而这时中国农村已经进入最困难的年代,关中农村的背馍生都在搞“瓜菜代”,而我已经降到了走读生的苦境,即每天傍晚跑十里路回家吃饭,顺便给第二天中午带点什么可吃的东西。即使如此,家里也不能保证我每天从学校回来都有饭吃,更不要说带了。万般无奈之下,父亲只好选择了给生产队打胡基的办法,因为每打五百页胡基,除了可以挣二十分工外,生产队还给补助斤半口粮。图的就是这点粮食。然而以饥饿之躯去干这种农村最重的活,无异于挖肉补疮。但父亲别无选择。他在东场里选定地方,然而就拉土,渗水,打胡基,每一页胡基都需要付出巨大的能量,能量不足,就只有一遍又一遍地勒腰带,腰带勒得不能再勒了,只好用喊声来为自己提神,每打一杵就从胸腔里发出“嗨”的一声呐喊,把整个村头都震动了。村人们说:“王战为了供儿子念书,把老命都搭上了!”这样干了一大晌,回家吃饭时,祖母只能调一碗掠熟的萝卜丝为他充饥。父亲端起碗就往嘴里扒,吃得上气不接下气。吃到剩下少半碗时,他的筷子慢下来,停住,忽然连碗带萝卜丝摔在了地上,泪水顺着蜡黄的瘦脸流了下来。这一幕永远地钳印在了我的记忆里。在这人生的大痛之际,我曾把心一横,企图放弃学业,回家来代替父亲劳作,但最终我还是背着祖母为我准备的掺了一些面麸的菜疙瘩,走回了学校。因为我明白,也许改变我和父亲以及这个家的贫苦命运的惟一出路,就在我的学业的高低上。
经过我和父亲的努力,我终于完成了高中的学业。接到兰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我高兴地跑到大队菜园去告诉父亲。我本来想先向父亲叙说接到通知书的经过的,父亲停住手里的活,说:“不说那些了,你现在只说报名得多少钱?”我说大概六十元左右。父亲就东跑西借地给我凑足了六十五元学费。在那样的年月,一块钱对我们这个家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六十五元钱造成的经济压力便可想而知。然而更糟糕的是入学后由于我的一时谦让,被评了个乙等助学金,刚好够伙食费,而这次评定由于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开始,竟然六年一贯到底,从未更动。结果使我这个本来应该第一个享受甲等助学金的人被打入了窘困的地狱,经常为八分钱的邮票发愁,更别说学习用具和生活用品了。万不得已时,只好向父亲张口,而父亲总是千方百计地给我寄点钱来,有时五元,有时八元,最多的一次是十五元,而且每学期最多只能有两次。每次接到父亲的汇款,我总是回想起父亲打胡基的那段悲怆的往事,而父亲和乡亲们代替牲口在磨道里推磨,在田野上拉犁拉耙的图景更是经常不断地呈现在我的眼前,我早就感到愧疚了,随着上学时间的推移,这种愧疚已经演变成一种负罪的感觉,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祖父、祖母相继去世了,妹妹出嫁了,父亲一个人开始了独居的生活。我知道父亲的能力已经达到了极限,所以当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华阴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的时候,我便迫不及待地写信将父亲接到我所在的学生连去,让父亲开始接受儿子对他的回报,因为我已经有每月四十八元的工资了。我们当时还住在当地群众的空房里,睡着地铺,塑料单子一揭下面全是水珠子,父亲就睡在我的铺位上,享了三天儿子的“福”。此后的很多年,我的生活的首要内容就是孝敬父亲。一九八一年的冬天,当我领到《收获》杂志寄来的《喜鹊泪》的三百六十元稿费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圆梦。我领着父亲上街,给他买了一件二毛皮袄,一副石头眼镜,一顶栽绒棉帽和一双新棉鞋,又让妻子给父亲做了一身里外三新的棉裤棉袄,这是那个年代农村老人渴望过上殷实生活的几项标志。为此,妻子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来款待父亲。当我将全身焕然一新的父亲扶着坐在桌前的时候,我的眼鼻阵阵发酸,我真想跪倒在父亲面前,对他老人家说:“父亲,儿对不起你老人家,让你受了那么多年的苦……”
二
在我参加工作以后的很多年里,父亲都是一个人住在乡下,只是在农闲或者年节的时候来西安住一段时间,但住不了十天半月,就说心慌得不行,催着送他回乡下去。随着时日的消逝,我越来越意识到父亲年事的高迈,不宜再一个人在乡下独居下去,多次催他搬到西安来住,但总是遭到他的拒绝。他说:一个人在乡下住惯了,心里朗然,粗茶淡饭吃着也中过。再说,他还想为我守着家里这个烂摊子,说公家的饭碗总不能端一辈子,万一哪一天我落了马,或者将来国家精简机构,把我下放了,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有乡下这么个家,怎么都过得下去。有一年春节,父亲因故不能来西安过年,我办好年货后已是大年三十的中午,因此就急忙往汽车站赶。当我赶回花王村时,整个村子都已笼罩在浓烈的过年气氛中了,而父亲却一个人在院子的柴禾堆旁撕扯棉花杆,准备做饭,脸上一副凄然的神情。我心里十分难受,心想这次一定要将父亲接走。父亲看见我回来了,很高兴,布满皱纹的脸上立即绽开灿烂的笑容,说年货都已办好,见只有他一个人,心里确实有些难过,这下好了,咱们父子俩可以一起过年了。我提出这次他一定要跟我搬到西安去住,态度十分坚决。但父亲仍不肯,说他身板还硬朗,用不着我操心,要我过罢初一就回去,说西安还有云侠和两个娃哩,不要耽搁了他们过年。
父亲是个农民,对劳作生性存有一种喜好甚至沉迷。不管做什么活儿,他的舌尖总喜欢从嘴角不时地伸出来,像在泯舔一块看不见的糖果。倘是在热天,他的脖子上总是搭着一条乌兮兮的毛巾,汗流得睁不开眼了,才拉下毛巾擦一擦,然后再干。他有二亩八分地的责任田,除了挂牵着西安的儿孙们外,他把心思和精力全部投在了这块土地上。在接种这块责任田的时候,父亲已经过了古稀之年,但他一点也不服老,也不服别的农户,他要在自己经营的这块土地上创造出全村亩产的最高记录。当我帮父亲往地里拉农家肥的时候,当我和父亲并肩拉耙拉耱的时候,我都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尤其是当我和父亲一起收割成熟了的小麦的时候,当我帮他把收割的麦往场里拉运的时候,当我和父亲迎着拂晓的晨风把前一天碾好的麦子往出扬的时候,我都十分强烈地感受到了父亲那火热的劳动精神和急于知道单产和总产的迫切心情。我知道,他很想听到村里人这样的夸奖:别看老汉上年纪了,地里打的粮食可并不比别人少。我曾多次劝他把地让人代耕,他都不答应。这让我十分担心。一直到他七十九岁那一年,一场麦收熬尽了他的最后一点体力,他终于病倒了。这是一九九零年的夏天,我正忙着为陕西电视台创作电视连续剧《庄稼汉》,接到父亲病重的电报后,我立即放下笔,赶回老家。我一路上心里都在为父亲祈祷,尤其是快进村的时候,我的脚步都不敢往前再迈了。我停住脚步,望着村子上空那一片浓密的树荫,简直不敢想象父亲到底病成了什么样子。我平生头一次这样近距离地感受到了死亡对父亲的威胁;毕竟已经是快八十高龄的老人了,风地里的灯,说灭就会灭的。好在父亲的病还没有发展到那样的地步,当经过治疗,病情稍微稳定一些以后,我便不由分说,把父亲接回了西安。记得那是一场狂风暴雨后的早晨,我们父子俩乘着长途汽车往西安赶,父亲倒在我怀里睡着了,我望着父亲那劳累一生变得十分疲惫的苍老的面容,禁不住热泪盈眶。我在心里发誓,从现在起,我宁可将功名利禄全部放弃,也绝不让我的苦命一辈子的父亲再受什么可怜。
当时我的住房只有两室,父亲和两个孩子住在一起,每天晚上,儿子晓舟都要拉开钢架床睡觉,第二天再叠起来。吃饭时,妻子总是将肉菜和可口的菜放在靠近父亲的地方。我外出回家,也总是不忘给父亲带上一些他喜欢吃的糖果、油糕和甑糕一类小食品,并且随时给他一些零花钱,让他随便给自己买一些想吃的东西。而父亲也总是舍不得全部花掉,不时地给家里购置一些日用的东西。为了满足父亲一定要将他埋在故土的要求,也为了让父亲避开西安每年十分难熬的苦夏,我每年夏天都要将父亲送回老家,托给堂弟锁成两口照应,入秋以后再接回西安。早就给父亲准备好的全套老衣总是被装在一个大包袱里,来回随父亲而行。搬进新居以后,我就在书房里支了一张床,供父亲专用。我伏案写作时,父亲不时地站在旁边瞧望一会儿,时间太长了,他就会劝我说:“歇一歇,不要太劳。”写到农村的事,父亲就是我的活字典,问什么,父亲就能给我答出什么。我们父子间的这种亲情式的珠连璧合,极大地安慰了我的苦难的灵魂,使我感到莫大的欣慰。我盼望父亲长寿,盼望我们父子间这种和谐的关系能够永久地保持下去。但这可能吗?
二十世纪最后一年的初春,我患了胃病,来势很凶,折腾了二十多天才渐次缓和过来。为了缓解被疾病消磨得疲惫不堪的心情,我骑着自行车,冒着大风,到一个朋友的书店去闲聊了很长时间。回来时就听到家属院人说父亲走路被风吹倒,摔断了腿,已经被送到红十字医院去了。我急忙赶到医院时,父亲已经躺在急救室临时安排的病床上,打着吊针,妻子和大儿子晓江在旁边照看着。父亲见我来了,就招手把我叫到身边,语气平静而又果断地对我说:“到时候了,不要花冤枉钱了,赶快往老家送吧!”我当然不会照他说的做,而是按部就班地安排他住院治疗,因为我身体十分虚弱,还雇请了一位保姆日夜守候在他身旁,我每天至少两次往医院给父亲送饭。等到把父亲从医院接回家时,外面已经是万紫千红的春天了,而我却浑然不觉。
父亲的身体素质是很好的,如果不是这次意外的劫难,活过九十五岁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看着眼前这情景,我就不能不从内心里感到难过。我意识到,父亲和我一起相处的日子可能已经不多了。虽然如此,我仍然心存希望,因为父亲除了膀胱结石以外,再无其他毛病,即使将来走不成路,有我这个儿子在就行。我会全心全意把老父亲侍奉到寿终正寝那一天的。因为我要的就是我们父子间几十年来这种亲情的延续。只要我在家,侍候父亲的事全由我包下,送水送饭,端屎端尿,是我份内的事,我一点也不觉得麻烦。怕父亲一个人躺在床上心慌,我就尽可能多地抽出时间陪他说话;怕我出外办事时父亲感到寂寞,我就在旧书摊买了不少连环画放在父亲枕边,让他翻看。我总想让父亲多吃点肉菜,但父亲一见荤腥就拉肚子,白天就不说了,晚上动辄四五次,甚至五六次,弄得我整夜睡不好觉;即使处于半朦胧状态,只要父亲在书房里轻轻唤一声,我都听得见,马上爬起来跑过去侍候。这期间,我的胃病犯过几次,在妻的催促下,我上附近一家大医院做了检查,钡餐透视的结果是胃窦炎。我一边服药,一边为父亲尽着孝心。到了零一年春天,我的病情加重,吃什么胃药都不大管用了,胃疼得没法吃饭,脸色越来越难看,体重也开始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仍然不大在意,仍然以为我会永久地侍奉着父亲。只要父亲那边一叫,我就会一只手捂住胸口,一只手为父亲冲洗便盆。我的原则是:只要我在家,侍候父亲的一切事情全由我一个人承担,一般不让妻子和孩子插手。眼下自己也病成这个样子,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了。一天晚上,我给一个懂点医术的大学同学打电话咨询,他的回答是:把一切事情全放下,明天一早就去医院检查,主要做胃镜检查。第二天早晨,侍候父亲吃过早饭以后,我就在妻的陪伴下去了省医院。当我们坐在胃镜诊室门外等候的时候,妻子忽然反常地将我的手抓得紧紧的,她已经预感到了某种不祥。检查是十分痛苦的,完毕后,妻子被大夫单独叫了进去,我就知道不好,回到家里躺在床上休息时,我已经觉察出妻子在卫生间里抽泣。我笑着对妻子说:“说吧,是不是得了不好的病?”妻子再也控制不住了,泪如雨下:“让你看病,你老拖……”医院要求下午就去办住院手续。当我将父亲侍候好,准备离开家时,我忽然走不动了。我回过头来,仔细审视着这个家里的一切,头脑里一片茫然。我心存着许多遗憾,但反射出的头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不行了,扔下老父亲该怎么办?妻子趴在我肩头上嚎啕大哭起来,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妻子。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我来不及思考自己面临的这一切。
因为赶上“五·一”长假,医院不上班,手术被安排在五月十日进行,这样我还可以在自己心爱的家里多待几天。第二天我给父亲端饭时,父亲非常严肃地问我:“昨天云侠咋啦?”我说:“没怎么。”父亲说:“那为啥哭得那么厉害?”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父亲。父亲说:“过日子,夫妻要和睦,你可不要欺负云侠。”我向父亲点了点头。父亲这才开始吃饭,吃得很香。我在父亲身旁站了很长时间。我意识到,这个家已经到了最危机的关头,如何最大限度地保全这个家,已经成了摆在我面前的最严重的课题,即使不幸的命运要同时降临到我们父子头上,也必须在我亲手把老父亲送下土以后,我再走。否则,我将自绝于天地,再也不会相信还有什么天理!
和云侠商量后,我们先将父亲送回老家,先后由堂弟和妹妹照看,然后将我推进了手术室。接着就是定期的痛苦的化疗。我们父子俩在同一时间和不同的地点面对着死亡,经受着生命的巨大的劫难。这年十月的中下旬,我和妻子到黄河岸边的妹妹家去看望了一次父亲。虽然我被化疗折磨得面目全非,父亲还是一眼认出了我,他躺在土炕上,满眼含泪拉住我的手,久久不肯放开。岁末,我刚接受完第四次化疗不几天,就接到了妹妹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吃不下饭了,一个劲儿喊着赶快把他往回送。于是父亲被从百里以外的赵渡镇送回了花王村。我和妻子也从西安赶回了故里。第四天,父亲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我知道,二十多年来我最害怕的时刻就要到来。我抱住父亲,脸贴住他的脸,用手不停地抚摸着他那响着浓痰的脖子,流着泪说:“大,你咋咽得下这一口气呀……”之后,父亲的喘息声渐渐地消失下去,就像安详地入睡了一样。我意识到,我们父子间生离死别的时刻已经到来。当亲戚和村人给父亲穿老衣的时候,妹妹在一旁流着泪说:“大,你一路走好,一路走好……”当我在大门外烧倒头纸的时候,我放声痛哭起来,这哭声惊天动地,是我一生从来没有过的。
二零零一年,是我个人生命史上最黑暗的一年。
三
一位几十年和自己相依为命的亲人突然之间从我面前消失了,这在心里上和感情上造成了巨大的真空,这种真空是世界上任何东西都难以填充和弥补的。尽管我知道父亲迟早会离我而去,我在心理上很早就开始做这种准备,但当父亲真正离开我的时候,还是很难一下子接受这种现实。为了很好地缅怀父亲,也为了让心灵上的创伤逐渐地得到弥合,我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和妻子回故园去居住一段时间。回到故园,就会产生一种仍然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感觉,这种感觉就像幼时躺在父亲怀抱里那样温馨,并且容易引发对过去生活清晰而又绵长的回忆。
其实故园并非我家的祖居。我家的祖居在花王村原来的东城门里路南。听父亲说,那里原来有我们家一座很大的宅院,祖上好几辈人曾经活得很风光。到了清朝中期不知什么时候,一场大饥馑,就使那里变成了一片瓦砾。老先人将那一大片院房换了几斤锅盔馍,带领着全家逃向了桥山深处的关门镇附近的一个叫杨洞儿的荒山沟。从此,我家几辈人就开始了上下辗转的流离生活;蒲城闹饥荒了就逃进北山去,山里闹土匪了又逃回蒲城老家。现在的故园原是村里王户的祠堂,五五年我们全家从芦峪村搬回花王时,父亲花三百六十五元从王户手里买来的。那时祠堂的厢房和门房都没有了,就剩下后面三间破旧的大房。我青少年时期很多关于祖父、祖母和父亲的记忆都是和这座房子联系在一起的。一九六五年,即我上大学的第二年的冬天,为了给祖母割棺板,也为了给我结婚准备新房,父亲将那座大房拆了,另在前院盖起了四小间对檐厦房,同时用腾出的木料给祖母割了一副棺板。父亲一生的最大心愿就是亲手盖起几间新房,我看出这次变更令父亲非常伤心,因为这只是迫于无奈的翻拆,而不是盖新房。所以二十年后,当我拿到自己第一本书的两千元稿费时,我就打定主意满足父亲的心愿,让他亲手给家里盖了一次新房。这是一九八六年初的事,当时父亲已是七十四岁的老人,为了买几十根新椽,他多次上县城跑木料市场;而为了买到理想的大扒钉,他竟不惜跑四五十里路,将几十斤重的铁货步行从兴镇背回家。盖房时,父亲除了帮我照料匠人,还要满村里跑着借匠人需要的东西,情绪空前的高涨,一场房盖下来,我已经精疲力竭,而父亲却健康如旧,这使我心里十分高兴。我一生除了为父亲养老送终外,还为父亲办了两件大事:这次盖房是一件;另一件就是盖房后的第二年,我在父亲的许可下,找见了已经三十多年没有见面的母亲,并且将从新疆赶回来看我的母亲带回花王,和父亲见了面。虽然只是一次见面,但在我的家史上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为我不但为孩子找见了祖母,为妻子找见了婆婆,而且为我大半生没有享受过母爱的心灵找回了慰藉。更重要的是,当父亲和母亲在全村人的热烈的目光下含泪握手的时候,我看到了人性的伟大的光芒,我为父亲母亲能够在这一瞬间填平几十年感情上的沟壑,完成他们心灵上的和解而感到骄傲。
当然,父亲生前也留下了一些遗憾。老人有两个心愿未能实现:一个是他从我给他的零花钱里节约出三百元钱,本来要给两个孙媳妇作见面礼的,但他临终前也未能看见孙子媳妇;一个是他一直想回芦峪村去看一看,尤其是想拜谢一下曾经给他指了明路的那位大哥,也未能如愿。这实际上也成了我的终生遗憾。
父亲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庄稼人,但在我的心目中,他比很多有地位有名望的人要高尚得多。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来没有拍打过我一巴掌,这是我这个自诩为文化人的人也没有做到的;为了不让我受后母的虐待,父亲自四十一岁和母亲离婚以后,再没有后娶过,连提都没提过这层话。
如今,我已经度过了生命的危险期,平稳地进入了康复期。感谢上苍的不弃,也感谢父亲在天国的护佑。我和妻子住在故园里,看见父亲栽养的菊花在秋天灿烂开放,冬青已经长得高过了西墙,又能怡然自得地在田野里徜徉,和乡亲们拉家常,还能静静地坐在小窗前读我喜欢的书,写我想写的文章,我感到非常自足。但愿天地长在,日月常明,生活之树长青。也但愿父亲能经常回到我的梦里来。
王宝成,1944年出生,兰州大学毕业,出版长篇小说《梦幻与现实》三部曲《饥荒》《红尘》《心境》。创作有电视剧《庄稼汉》《神禾源》等多部及中短篇小说等,中国作协会员,现居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