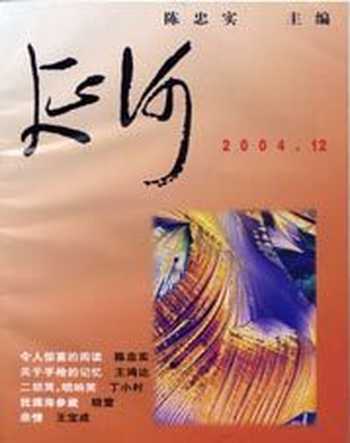拾麦琐忆
夏日里一个周末,我带女儿去公园游罢归来时,已近黄昏。掀开竹帘,一眼望见住在乡下小镇的母亲来了,正坐在窗前同妻子说话。我忙迎上去问候老人家,女儿欢天喜地,像小燕子直扑进奶奶怀里。刹时,屋子里笑语喧哗。
妻子冲我诡秘地一笑:“妈给咱们送好吃的来啦。”见我茫然不解的样子,母亲微笑着站起身来说:“新麦下来了,我抽空拾了几把,蒸了点馍馍,给岚岚尝个鲜。”我这才发现书架旁边的地上放着一个竹篮子,掀开蒙在篮子上的笼布,呈现在眼前的是满满一篮雪白的馒头,那光洁的表皮在灯下显得纯净、诱人。见此情景,女儿乐得直拍小手,“奶奶,你真逗,老远的路,提这么多馒头干啥?是不是怕我饿着?”“是呀!”母亲笑着拉过岚岚细瘦的小手,轻轻抚着,责备道:“瞧,还这么瘦,豆芽似的,都是那不养人的饼干吃的!”女儿朝我做个鬼脸,抓起馒头吃了起来。“好吃么?”母亲问。“好吃得很,比面包还好吃哩!”女儿脆脆地回答。“那就多吃点,你爸小时候要吃点白馍可不容易哩!”母亲说着,从篮子里取出一个馒头递给我。
凝望着母亲那周遭布满皱纹的眼睛,我似乎看见有两点星光在轻轻跳动。眼前,陡然涌现出一幅熟悉的画面:如火的骄阳高悬天际,收罢麦的田野上空荡荡的,母亲弯着腰正一穗一穗地拾麦,灼热的山风把她脸上的汗珠吹洒在金黄的麦穗上……
童年生活的帷幕是伴随着十年浩劫的开始而拉开的。对于我们这些懵懂的孩子来说,除了不能进学校正常念书外,更要命的是,肚子经常吃不饱。作为吃商品粮的城镇居民,每月定量非但不够吃,更令人头痛的是以高粱面为主的粗粮要占百分之六十。这样,家里蒸馍用的几乎全是高粱面。为了使我们能咽下粗硬的高粱面馍,母亲想了许多法子。譬如,发面时放点糖精,把馍尽量蒸得虚软些。偶尔,也用节省下的麦面掺进去,做一种名曰“金裹银”花卷馍。那是由一层紫黑的高粱面夹一层细白的麦面卷起来的。听得出,动人的名字本身就反映了时人对粮食的渴念珍视。有趣的是,实际上不好下咽的高粱面因其色泽赤乌而获得金子的美喻。而麦面只能被称喻为银子,名与实恰好打了个颠倒。物以稀为贵,我们这些成日价吃不到麦面馍的孩子对它的渴望是不难想象的。偶尔,乡下的亲戚来小镇赶集带几块麦面馍,兄妹四个总免不了争吵一场,你吃得多了,我吃得少了,闹个不休。母亲责骂一阵,往往暗自垂泪。
不过,一年中却有那么个把月,不但能够吃到白馍,而且简直可以说一饱口福呢。这就是麦收季节,镇上许多居民能通过去乡下拾麦来弥补一年来积攒的对麦面的渴望。
往往是麦梢刚刚泛黄,大家就开始计划今年先去哪里拾,哪天开始行动,而心头里也已微微荡漾起新麦的香气了。日子一天天迫近,“算黄虫”愈叫愈响,小镇周围的麦田泛起了黄金色。终于,甘肃来的赶场麦客(家乡人称之为“炒面客”)出现在小镇了。他们往往举家而动,晚上就睡在街道的房檐下,一边吼唱秦腔小曲,一边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填炒面,彼此用磨得雪亮的镰刀剃头,一个个光葫芦在路灯下明晃晃地耀眼。“开镰了!”随着麦客们兴奋的叫喊,我们的好时光也来临了。
完全是自觉的行动,每天下午一放学,撒腿就往附近的麦田跑。到了地里,书包一扔,就你追我赶,比赛一般拾起麦来。真得感谢那时的生产队“大锅饭”,割麦者多不太细心,麦穗拉拉杂杂,撒了一地,不大功夫,就能拾好几把。夕阳西下,夜幕垂落,这时,尽管穿着旧凉鞋的脚丫子被麦茬扎得流血,腰弯得又困又痛,肚子也饿得咕咕叫,但是当我们腋下夹着一大把麦穗跨进门槛,领受到母亲疼爱欣慰的目光时,心里却有一种自豪欢悦之情滋生涌动。当然,这份豪迈而自感庄严的情怀,今天的孩子是难以领略的。
在拾麦季节,家里最辛苦的是母亲。当时,在外地一个公社当书记的父亲已作为走资派被造反派打倒,“靠边站”了,要随时接受批斗,没有造反派的恩准,不得回家,我们很少见到他。母亲整日价提心吊胆,惟恐他熬不下去走了绝路。巨大的心理压力使才三十多岁的她,看上去十分憔悴。但每天下班后,她都要去小镇周围的地里拾麦,哪怕只拾几把,然后又匆匆赶回家为我们兄妹几个准备晚饭。往往,当我们在灯下围桌吃饭时,母亲却疲惫不堪地伏在炕沿睡着了。我们便急切地呼喊:“妈,你吃饭呀。”拉着她的胳膊,她会猛地坐起来,手臂弯着在腰背捶几下说:“你们吃吧,妈一点都不饿。”然后,取来簸箕、麦把,蹲在门口揉搓起来。搓一会,再簸一会。最后便是晶莹的麦粒,有两碗多吧。静静地看着母亲做这一切,我们心中有一股无法言说的感动,大家暗暗下定决心,明日一定要多拾一些。
除了每天利用课余时间去近处拾麦外,到麦子全黄,我们可以有几个整天去远处山村拾麦。那时,镇上有20多年历史的公立小学已被解散,老师全被下放到附近生产大队新办的几个小学了。据说,这样做才能保证贫下中农社员的子女真正享有受教育权,不能允许城里的“少爷小姐”们在家门口那么舒服地念书,这是缩小城乡差别的重要措施。我们兄妹几个便只好来到小镇旁边一个生产大队办的小学里念书。毕竟农家孩子多,麦收紧张季节,学校便会放上一星期的假,让学生回家帮助大人收麦。这样我们吃商品粮的学生就有几天放闲。这正是大伙巴望不得的好时机,可以自由自在做拾麦的远足。一大早,小伙伴十来个结成伴,在母亲们要注意安全的千叮咛、万嘱咐中跨出了家门。由于要去远处的山乡拾整整一天麦,各人都带着水壶、干粮、口袋等家什,精神抖擞,看上去真像一支小小的远征军。不过水壶可不是那种锡铁皮做的军用水壶,而是医院里用过的空葡萄糖瓶子,软橡皮盖子捂着满满一瓶子掺有糖精末的白开水。可别小看这粗陋的瓶子,它不仅给我们解渴的满足,在当时,确实还是很招人羡慕的时髦品哩!
我们去的较多的地方是离小镇有十来里的千阳岭。那儿地广人稀,麦子割倒后,队里社员根本顾不上去拾散落的麦穗。况且,还可以“免费”坐一段汽车哩。说起来,当时那些冒险至今想起都有点后怕。千阳岭上盘绕着宝平线(宝鸡至平凉公路),汽车从山下往上开,多像蜗牛一般缓慢。我们便分成几股站在坡度较大的路边,等待搭“免费车”的时机。多半选那些满载货物而带有拖挂的大卡车作为搭乘对象。它爬大坡时,还没人步行走得快,加上拖车后箱板很低,我们攀着不费多少力气就爬了上去,而司机一点也不会发觉。坐在拖车里,大伙猫着腰,不敢大声说话,彼此打手势,做怪相,表达着冒险成功后内心的喜悦得意。当然,也不免很紧张,眼睛盯着驾驶室,耳朵专心致志于汽车发动机的响声,时时做好一旦被司机发现,及时跳车逃跑的准备。除非被发现,我们可以一直坐到千阳岭顶端。跳车地点早已选定,在上山的路将结束处的一个大坡处。这事不敢有丝毫马虎,一但错过那个地点,车开始下山,速度转快,再跳车就有摔个半死的危险;若不跳,则会一直被拉到千阳县城去,那儿离家居的小镇足有50里路,而且还可能受司机不客气的惩罚。我们所玩的这些冒险游戏,大人们恐怕做梦也想不到。要是知道,真不知会吓成什么哩!幸运的是,在我爬车的多次经历中,除了有一次被司机发现,紧急跳下,膝盖撞肿了外,基本上是安然无事,爬得上去,也跳得下来。而我斜背在军挎包里的自制玻璃瓶水壶也真叫争气,硬是没摔破过。后来,这个装葡萄糖液的玻璃瓶又被当作暖壶,伴我渡过了知青生涯的三个寒冬。在冷气潇潇的乡下小土屋里,它所散发的温热驱走的不仅仅是体表的寒冷,更是心头的凄楚孤寂。多少个雪花飘飞的冬夜,靠着这份温暖,我读着《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等等那个年代费心觅到的精品,完全忘记了冰冷的时空。再后来,我离开山村时,队上一位农家的孩子怀着感激接受了它。现在,那位当年学知青样,不睡热炕睡冷床的孩子该娶妻生子了吧?!在电热褥已十分普及的情况下,我不知道那“土暖壶”是否还受到主人的青睐,也许已经打碎了吧。然而,那份心头的温暖已镌在我心头,那是无法抹去的!
逢到工休日,母亲也和我们一起去远处的乡间拾麦。头天晚上,她大概只能睡四、五个钟头,鸡叫头遍,便起来为我们烙饼子,准备远行的吃、喝等用品。凌晨四点来钟,兄妹四个跟在母亲身后,揉着惺松睡眼出发了。那时,小镇尚在梦中,街道房沿台阶上横七竖八地躺着甘肃来的麦客,他们发出的沉重的鼾声在静寂的空气中听来格外清楚。我们不忍惊扰这些劳累了昨日又将劳累今日的远方人儿的好梦,脚步尽量放轻。那一刻,一种新奇激动而神秘的情愫悄然涌上心头,似乎感到了成人的自豪,似乎为那些正在床上做梦的人感到惋惜,他们可曾知道小镇凌晨这种凄苦中的壮美么?!
出了小镇,跨过小石桥,我们沿着曲曲折折的山路向千阳岭攀登。约摸一个小时便来到山顶。这时放眼东眺,远处正泛起鱼肚白,不大功夫,像是有一只神奇的笔于看不见处在东天涂抹。白色渐变成橙黄、桔黄,终于在浅浅的红潮中涌出了一个黄中透亮的朦胧的圆球。它看上去柔和温婉,悄然无声,含着几分羞涩,几分清丽,很像一位对镜晨妆的少女。稍近处,沐浴在晨曦中的山梁沟壑、村落人家、树木公路红艳艳地,又显得那样雄浑博大,安详凝重。身边,噙在草尖上的露珠颤微微的,交相辉映,又像无数双儿童眼睛正一眨一眨,调皮地望着人嘻笑。这晨光中的美景令人陶醉,令人激奋。兄妹四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对着远处山顶那一轮红日忘形地大声吼叫起来,“嗨噢……太阳出来了!”这喊叫伴随着对面山梁上的“崖娃娃”的呼应发出连绵的回声,此起彼落,余音袅袅。瞧着我们大呼小叫的欢快样,母亲也露出了很少看到的笑容。但她的笑是浅浅的,也不说什么,只是怜爱地用手抚着才七岁的小弟,替他抚一下乱蓬蓬的头发和因喊叫而憋得通红的小脸,然后便弯腰在麦地里检索起来,而我们就像一群小鸡雏,跟在她身后,一边叽叽喳喳,互相打闹着,一边开始了各自的劳作。渐渐地,田野上安静了下来,只听见大家不时移动的脚步声。
时至正午,骄阳似火,母亲直起腰,挥一把汗,大声呼唤分散在田野四处的儿女们,该吃午饭了。我们来到田边一棵大树遮荫下,围坐在母亲身边。母亲拿出一块塑料布,铺在地上,然后把放有咸菜、凉拌黄瓜的铁饭盒打开,置于正中,每人一块“金裹银”馍,两个西红柿。所谓午餐,也就是这些。然而,我们吃得津津有味,这大概只能归因于一个上午劳作后的饥渴疲困吧。此时,也正是山后炸石场点炮时节,轰隆隆的放炮声从远处传来,一声又一声,闷雷一般,神秘悠远。朝坡下望去,零星分布的山野人家场院里,可以看到牛拉着碌碡碾场的情景,盘山道上偶尔走过一辆破旧的拖拉机,上面是堆得如小山般的青石头,对面山梁上放牛的老人和已吃得饱饱的牛儿静静地栖息在沟边的一片小树林里。
我们都不说话,疲劳使大家就那么静静地躺在麦地边,一会儿就睡着了,而母亲正拿出剪刀把堆在脚边的麦穗头儿一把一把往下剪,然后再装进带来的布袋里……
多少年过去了,这情景竟是那样生动清晰地浮在眼前。我知道,它已永远定格在我十四岁的年轮上了,那是无法抹去的历史痕印。当我后来离开小镇,来到都市里,坐在大学校园的假山喷池边,当我徜徉于书的海洋里而惬意忘情时,我常常会突然忆起千阳岭麦地边围在母亲身边午餐的情景,我不知道弟妹们是否还记得这一切!
回忆是酸楚的,回忆又是迷人的。当我追述这一切时,我看到年迈的母亲眼里噙满泪花,“孩子,小时候的事,都过去多少年了,你还记得这么清楚。”母亲像是问我,又像是自语,“是不能忘记那些事的。”我回答。
女儿一直在静静地听我诉说,我发现这时她稚气的小脸上竟头一回现出一种像是深思的神态,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正在把这一切同她熟悉的许多童话联系在一起,也许她会因为童话竟同自己的父亲、奶奶有关而感到好奇。沉思片刻,女儿忽然抬起头对我说:“爸爸,明天你带我去拾麦穗吧!”我使劲点了点头,“明天我们和奶奶一起去拾麦穗!
常黎峰,笔名黎峰,就职于陕西省委党校《理论导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