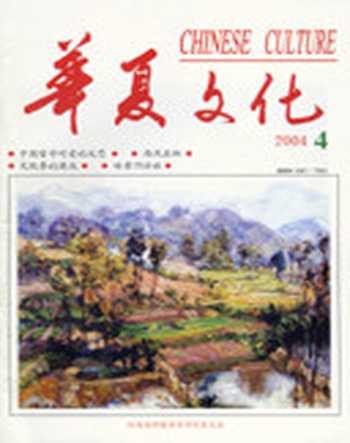西风东渐
张 旗
鸦片战争前的清代旅游已颇具规模,经济相对发达的江南地区,尤其是长三角沿江中心城镇,如苏州、无锡、镇江、南京、扬州,市民多殷实,旅游活动几乎一直处于活跃状态。其旅游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观光游、采风游和时令游几种。官宦文士是观光游和采风游的主体,社会大众则是时令游的主体,具体包括传统节庆游和宗教节令游。有人把这一时期的旅游特点概括为群众性、规模大、地域广、日常化,足见当时当地旅游括动之盛。“游踪成市”,这是对当时旅游业对社会发展所起作用的概括。实际上,兴旺而频繁的旅游活动,刺激了与旅游相关行业的发展。苏州、南京、扬州有许多因游客而生的酒楼茶肆。旅游购物则刺激了各地特色手工业的发展与繁荣。苏州丝织、南京云锦、扬州玉器都是旅游产品的一时之选。一些风景区还自发出现了服务游客的门面和卖艺杂耍等娱乐表演,吸纳了众多的社会闲散劳动力。
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间,中国社会经历千古未有之变局,经济现象异常复杂多彩,最主要的特征是西风东渐。晚清旅游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一方面保持了历史发展的惯性,同时也偏离既定的发展轨迹,带有一些异域风情。在一些强烈受到西方文化辐射的开埠区,旅游则有超前发展。具体的表现在以下方面。旅游交通更加便利,更具有现代性。清代传统的交通系统分为水陆两系。北方多车骑,南方多江舟,具有地区特点。但从整体上看,舟行是主流交通方式。英使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之后,在南下途中,对便利的水运交通留下深刻印象。西方文明进入中国后,在交通方面最大的改变是某些城市出现了洋轮和火车以及新的交通线。1845年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轮船公司如旗昌、怡和、太古在中国先后开辟若干航线,国内也出现了轮船招商局,专事水运。铁路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由西洋人开先河,随后在京津地区、台湾等处先后兴建了铁路干线。
无论是水路运输还是铁路运输,都由货运入手,其后逐渐增加了客运服务。以水运为例,外资旗昌轮船公司首先以上海为中心,开辟南北两条航线,接着将业务拓展到长江航运,最初承接中国商人的沿海转口贸易,以货运为主。由于西洋火轮在交通运输上占有优势,航速快,不受季风影响,能避免沿途盗匪的劫掠,并给乘客配有保险,所以,相对高效的且服务配套的新式交通工具逐渐改变了部分中国旅游者的出行方式。从1870年开始,客运业务逐渐占有越来越大份额,特别是在天津与宁波的航线上。由于上海毗邻宁波,商人采购物资,往往亲自出马,搭乘轮船。天津航线客运量增加是因为有中国官员和北上参加科举的秀才们的光顾。这些旅客对新式交通工具的便捷安全感受是如此之深,以致于除了乘坐火轮,不会考虑其他交通方式。
1871年起无论沿海航线还是长江航线,中国乘客都成为主体。西方人将中国人对西方交通工具态度的转变,看成是中国人文明进步的表征之一。但是,国人刚刚接触到这些新鲜事物的时候,还是费了些周折。根据 1866年的旗昌轮船商务报告记载,有一个显要官员曾携家带口离开南方,乘了一艘包租的外国轮船。可是船还没有开出虎门,他就已经吓得半死了,恳求船长让他在香港上岸。船长当然没有同意。后来,这位官员在上海上了岸,然后无论如何也不再乘坐海船北上了。
旅游范围日渐扩大,部分旅游者开始具有全球观念。出境游是这一时期的新生现象。随着中国逐步纳人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出于与国际社会接触和接轨的需要,以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考虑,一大批外交人员和留学生奔赴海外,足迹遍及欧美非等大洲。他们的海外见闻和国内西式学堂教育内容的相互印证,改变了人们的旅游时空观念。出行海外归国的人回想起出国前对世界天圆地方之臆想,不啻于坐井之蛙。
国内旅游资源进一步系统化、品牌化,并且在旅游资源开发中国家开始参与其中。手工艺品、菜系和茶叶在清末都已经形成体系。尤其是中国莱,随着中西近代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菜在西方赢得了好评。而西餐则以租界为中心,辐射到一些较为发达的中心城市,成为维新官场的时尚之一,甚至有没吃过法国大莱就算不得维新的说法。在旅游资源的开发上,至晚清,历朝历代帝王、官僚和士绅发掘出的旅游资源,在历史文化的积淀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品牌和特色,供游人比较赏玩。近年现身于鞍山的《情境迹锦》即是应需之作。该书成书于光绪十三年(即公元 1887年),作者王叶桂,所载内容为“直隶、盛京、江西、湖广……共十八省山川古迹”。值得注意的是,在特定条件下,国家开始参与旅游度假区的开发。有学者认为,北戴河是中国滨海度假旅游的发源地,在近代旅游上开了很多先河。19世纪下半叶,欧美人士(多为传教士)来北戴河传教兼避暑人数增多。伴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在维新思想的冲击下,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3月16日,清政府正式批准秦皇岛“自开商埠”。嗣后不久;又宣布与之毗邻的北戴河海滨(西起戴河口东芝金山嘴沿海向内3华里、)为各国人士避暑地,允许中外人士杂居(《北戴河,中国现代旅游业的摇篮》)。
国内旅游群体分化明显。中西交往的频繁,商业活动的频繁,造就了—个特殊的中间阶层,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旅游者的阶层结构。商业地位的提升,直接冲击了原先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排序。首先,在过去行商的基础上,发展出近代的买办群体,以及与之相关的中间商(购买与批发商)、城镇商人。(包括洋货号店主、地主富农、高利贷者)。他们主要从事商务旅游,西式旅游往往由他们引介、扩散到其他阶层。知识分子群体分化为新旧两派。新派知识分子往往具有西洋教育的背景;受到洋务和维新思想的熏陶,经常接触洋务;相对开明,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他们社会地位较高,影响较大,是西式旅游的主要推动者。由于商业雇佣劳动的兴起,人口流动速度和规模大大加快。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农民受到近代中心城市产业格局(商业和金融业发达)和自身素质的制约,绝大多数从业于和旅游密切相关的服务性行业。而原来从事娱乐业的社会群体,则因为城市地位的变化而有所转移。近代上海一跃而为商业中心,商贾穈氟中外杂处。苏扬各地之烟花,亦都图上海富商大贾之多,一时翩迁而来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旅游娱乐中西相杂。开埠较早的中心城市,如上海,西方人首先建设了一些用于社交、娱乐的俱乐部。相比之下,中国原有的旧式剧场场地狭小,不对号入座,演出次数不足,不能满足新兴近代城市市、民的需要。于是一些专门的娱乐设施应运而生,既赶时髦,又吸收其中合理的成份。比如百乐门,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室内有冷暖气装置,具有复合武功能,既有剧场、舞厅,也提供住宿。游乐,场如上海大世界,内部装有哈哈境、电梯,还可露天眺望全上海风光。还有各种地方戏、滑稽戏、魔术、点心小吃,一张票一天。经济稍逊的区域中心城市,虽然西式的娱乐设施还没有大规模出现,地方戏剧仍然是娱乐的主流时尚,但是西风的痕迹已依稀可见。此如街头摆设的西洋景,游客游览时手中的望远镜等(《老残游记》)。
旅游消费两极分化。一般的社会大众,旅游活动主要是时令和节庆游,属于近郊旅游,自带餐饮,不在外住宿,所以旅游消费极低。一些旅游名胜区常年均有戏曲杂技表演。如南京夫子庙,每逢清明日“百戏具陈”,游客围如堵墙,人声鼎沸,但当收看费时,则互相退缩,默不作声,有的给极少的钱,有的直接逃走等到开场再演,重又蹑足而来,从中午到晚上,往复如织(《画舫余谈》)。而官僚士绅阶层则不同,他们讲求排场,互相攀比,根据张仲礼的研究,t887年中国的士绅阶层占当时中国人口的2%,收入却占全部国民。收入的21%(《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他们是高消费群体,也是远游的主体。1871年旗昌轮船公司的船票价格,上海至烟台十三两五钱;上海到天津十八两;烟台到天津十两。按当时的银价折合成人民币,上海到天津的客运票价至少在4500元以上。这可以直观地反映社会上层的消费能力和水平;也”可反映各个社会阶层旅游消费的差距。
总之,晚清旅游风尚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而表现出与以往旅游不同的特色,但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力有限,绝大多数旅游风尚仍然是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