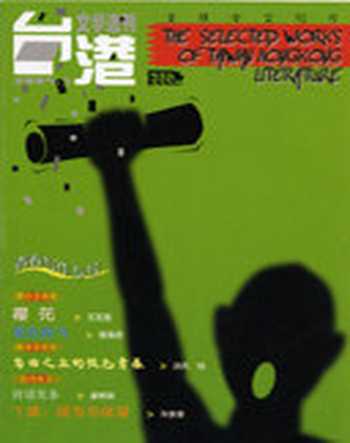英雄本“无名”!
王寿来
大陆导演张艺谋的武侠历史电影《英雄》在台湾上演后,立即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热烈讨论的话题,各方褒贬不一,甚至有两极化的评价,让万千影迷莫衷一是。
在国人根深柢固的文化根源中,英雄崇拜及神格化,可说是一种无可逆转的族群“印记”。因此,所谓英雄一词,自有其约定俗成、不言而喻的含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长阪坡救主的赵予龙、大破金兵拐子马的岳飞、景阳岗打虎的武松等等人物,无不是里巷口耳相传、妇孺公认的英雄。
然而,观毕张艺谋这部投资三千万荚金的电影巨作,人们不禁要思索,影片故事里究竟谁才是真正的英雄?是功亏一篑,被秦王劝服的刺客无名?是甘愿自我牺牲,好让无名能“上殿十步,与王对饮”的残剑、飞雪、长空?抑或是甘冒千古暴君恶名,统一战国时代分裂局面的秦王政?
其实,秦始皇的功过是非,历史早有定位与定评,任何企图翻案的文章,都有其无法超越的难度。或许,更重要的是,这样一部以历史为背景的电影创作,提供了更宽广的思考面向与角度,使我们在面对许多历史议题时,可以有更深入、更全面的观照。
记得多年前,我在旧金山曾亲自向著名的历史学者黎东方教授请教有关史料可信度的问题,他不假思索地答道:“依我看来,百分之八十的历史,都是不可靠的,但问题是,你若不读历史,就连那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也不知道了!”大师一言的“加持”,助我一跃跳脱读史无谓的心灵挣扎,令我感念至今。
摆脱电影中谁为英雄的纠缠,另一个较现实的问题是:活在当今的社会里,什么是英雄的行径?人们究竟应否努力做一名英雄?对此,想必也人云各殊,而我打年轻时,内心中隐隐约约已有若干先入为主的定见。
影响我最深的,说来是两部美国新闻总署制作的纪录影片。那时,美国与台湾还有正式邦交,老荚设在南海路的新闻处工作态度认真积极,特别配合“建中”放学的时间,放映一些介绍美国各个层面的影片。
其中一部是探讨当年荑国开拓西部,白人与原住民印地安人争夺土地的情形,提到名将卡斯达(GeorSe Ann-strong Custer)在一八七六年六月二十五日率领二百一十多名骑兵,与三五千名苏族与夏安族印地安人遭遇,以寡击众,激战一小时,全军阵亡。大部分官兵死后都受到剥衣及剥头皮之辱,卡斯达本人身中两枪,一枪在左太阳穴,一枪在胸口,但衣着与身体皆算完整,未受任何侵犯。战场上惟一幸存的,是一匹奄奄一息、身受重伤的军马。
印地安人敬重英雄,未以处置敌人的传统方式,来对待卡斯达,固然教人印象深刻,但片末述及今日印地安人原居地划有保留区,族人与美国境内其他族裔享受完全平等之待遇,又让人有不胜枚般之感,进而体认到法国当代哲学家莫兰(Edgar Morin)所言:“历史仿佛创造了一些境遇,使某些人能经历极端的体验”,论点精辟,提示了所谓英雄,往往只是特殊时间与空间座标下的产物。
另一部美国新闻处所放映的影片,主题涉及有关森林守望员(forest guard)的日常生活。所刻划的,是一群坚守岗位的男女,甘于平凡与寂寞,经年孤守在渺无人迹的山林里,整日只能与乌兽为伴,每天数度上下高达数十米的嘹望台,手持望远镜极目八方眺望,发现有冒烟的起火点,就须立刻通报森林救火队。他们的生活补给,不少是通过直升机投送,有些据点特殊偏僻,要隔好几个月才能看到同伴过来接班或回到平地休假。
该片结尾强调,森林守望员的工作,看似单纯卑微,其实重要性万不能等闲视之,因为,他们是在守护着大自然的“无尽藏”,守护着人类的根,尽管默默无闻,永难升官发财,实是做无名英雄的伟大事业。
片中看不出任何刻意的说教,只是以写实的手法白描森林守望员的工作点滴,以及他们长期忍受孤寂的不凡毅力。说实在话,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认知到,原来世间还有一种了不起的人物,活得那样低姿,那样与世无争。
古往今来,许多名人都论述或歌颂过“英雄”,或为“英雄”一词下过掷地有声的注脚,而其中我最喜欢的一段话,倒不是出自任何一位教人闻之如雷贯耳的大人物,而是出自于匈牙利女诗人、犹太人复国英雄漠娜·赛妮西(Han-nah Senesh,1921—1944)。这段话是这样说的:
“有些星星虽然早已消失,其亮光在地球上依然可见。有些人虽已不在人间,其光辉继续照亮世界。在夜晚漆黑一片时,这些光源格外明亮。”(Tlhere are stars Whoseradianee iS visible On earththough they have lOng beenextinct.There are people Whosebrillianee continues tO liRhttheWOrldthoughtheyarenOlongeramongtheUving.These1ights are Particularly briShtwhen the night 1s dark.)
赛妮西只活了二十三岁,可谓红颜薄命,却有着非常传奇的一生。她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一个犹太裔的中产家庭,父亲身兼剧作家与记者二职,在她六岁时,即英年辞世,家道因而中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朝野反犹大人的风潮逐渐形成,一九三八年欧战之初,匈牙利政府宣布支持德国,境内犹太人的处境益形艰难。热爱写诗的赛妮西,决定放弃上大学的梦想,回到犹太人的原乡巴勒斯坦,进入农业学校就读,以便将来投身开垦及建国工作。然而,她并未忘记故乡苦难的犹太父老,毅然加入地下反抗组织,计划潜回家乡救援同胞。
一九四四年六月,在英军的协助下,赛妮西跟其他三十一位队员跑到开罗接受跳伞、渗透、爆破、谍报等严格的训练,吃尽千辛万苦,终于被安排空降于南斯拉夫靠近匈牙利的边界,与其他地下组织会合。
潜入敌后不久,赛妮西不幸被捕,受尽种种威逼利诱及惨无人道的折磨,始终不肯屈服。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她遭德军行刑队枪决殉难,战后遗体被运回以色列西北部港都海法,以军礼荣典隆重安葬。
无独有偶的,我国近代也有一位革命女诗人的遭遇,堪与赛妮西的英烈事迹相互辉映,那就是国父孙中山先生曾以“巾帼英雄”四宇,题写其墓的鉴湖女侠秋瑾。她被清廷逮捕就义时,也不过只有三十二岁。
人们吟诵秋瑾的诗,读到:“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死去犹能化碧涛”,受其豪情壮志的感染,胸中舍我其谁的熊熊烈火,能不被点燃吗?
不求大名者,却得以青史留名,这或许是古今中外所有英雄人物始料未及的。想来,今生今世,我们很难效法张艺谋镜头下那种万夫莫敌的勇士行径,然而,我们应该相信,此去红尘路上,不论你我如何随缘放旷,一定仍有机会,做一个尽其在我的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