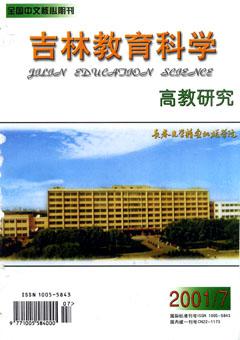论学术自由的“度”
郭荣祥
大学学术自由的重要性已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学术自由能激发学者追求真理的灵感和勇气,促进大学学术的繁荣,推动社会科学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创新人才的健康成长。可以说,“学术自由是大学生机与活力的象征”,“如果没有学术自由,大学的生命就会枯萎”。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学术自由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关于学术自由的“度”的确立原则、“度”的标准,一直是有争议的话题,笔者就此谈谈看法。
一、学术自由度的曲折史
学术自由的“度”,是指在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中,随学者或学术团体的意志自由活动的范围和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学术自由的度起伏跌笛。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学术自由的时代,私人有讲学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因而“百家争鸣”,出现了众多的新思想、新学说,对推动社会进步、科学文化繁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以春秋战国为代表的封建社会早期,有着充分的学术自由,无所谓度。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那时的学术研究活动处于一种混沌无序的状态,统治者还没有意识到这种极度的学术自由对其政治统治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那时正值封建制度刚刚形成,统治者急需新的理论为巩固其封建制度服务。学术自由在统治者这种“疏漏”和“需要”的夹缝中,到了一种极限,从而形成了各学派竞相争辩的风气和“百家争鸣”的局面,推动了学术和政治理论的发展。随着封建社会的巩固和发展,统治者逐渐意识到学术自由对政治的某些反作用,因而或多或少予以限制。两汉时期,学术自由受到一定抑制,自由度较小。如察始皇压制学术自由、焚书坑儒、取缔百家之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那一时期学术思想贫乏,歌功颂德盛行。唐、宋、六朝等时代,学术自由的度较大,因而文学艺术繁荣,科学技术鼎盛。明清时代,学术自由度很低,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压制学术思想,学者们或不问国事,沉迷于考据;或热衷八股,缺乏创新。中华民国时期,学术自由的度随着民国政权的转变和时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更。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积极着手教育改革,学术自由的度很大。袁世凯篡权后,阴谋复辟帝制,压制学术自由。接踵而至的军阀混战期间,民国政府的统治者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夺政治和军事的胜利上,无暇顾及学术领域,学术自由的度较大。蒋介石为首的民国政府成立后,其表面上仍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旗帜,实际上压制学术自由,压制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倡学术自由,表现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中。文革期间,左倾思想对学术自由横加压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自由又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学术自由在国外也有着曲折的历史。如在公元前5~6世纪的古希腊,奴隶主和自由民拥有广泛的权利保障和言论自由。那时,古希腊的科学、文化取得了丰富灿烂的伟大成就。当基督教的圣经被确定为最高和最后的真理后,一切不符合教义的学术思想都遭到禁止,学术自由受到严重的压制,因而希腊和罗马的兴盛跌到了中世纪的黑暗深渊。文艺复兴运动后,资产阶级以刚刚萌发的民主意识,实现了欧洲文化历史的重大转折,提倡学术自由。资产阶级在取得统治地位后,压制学术自由的现象不断发生。如本世纪30年代,德国法西斯曾解散了科研机构,焚烧了柏林图书馆,大批学者、教师遭放逐,德国的科学研究从此衰退。由于社会、历史等原因,美国相对来说学术自由的度较大,但也是有限度的,即便到了现代,美国仍以敌视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的激进者和社会主义国家。
纵观学术自由的发展史、学术自由度的历史演变,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在何种社会制度下,学术自由的度主要是随着统治者对学术自由作用的认识而变迁的。当统治者认识到学术自由对学术繁荣和社会科学文化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时,对学术自由的限制越小,学术自由的度值愈大;而当统治者认为学术自由对政治影响巨大,可能会动摇其统治地位时,对学术自由的限制越大,其度值愈小。
大学作为社会的一部分,自然受制于整个社会学术自由的大气候。社会学术自由的氛围越浓,大学学术自由的度越大,大学越活跃;反之亦然。大学又常常站在社会的最前沿,是社会学术自由度的“晴雨表”,早于社会其他部分感受到学术自由的“气温”。同时,大学并不是消极地领受整个社会学术自由度的制约的,而是积极争取着学术自由的权利,并总是担当着领导社会进行争取更大学术自由度斗争的重任。由于大学是学术活动、学术研究的中心,肩负着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科学研究等重任,作为较为独立的机构,大学相对于社会往往有着更大的学术自由度。当然,这还取决于大学的校长。如德国柏林大学创始人洪堡,他认为“自由”是大学“第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因而,积极争取大学的学术自由权,使学术自由在柏林大学得以真正实施。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因而当时的北大拥有较大的学术自由度,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发祥地。
二、学术自由度的确立原则
在讨论学术自由的度的确立原则之前,必须首先讨论一个与学术自由度相关的问题,即学术的价值问题。价值是客体之于主体目的的积极意义,是客体的属性满足主体某种需要的关系范畴。学术价值是以学术作为客体,以社会、人类作为主体所构成的价值关系。也就是说,学术价值是学术活动、学术结果的客观属性和它所反映的规律能满足社会、人类需要的某种性能。它包括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指学术本身渗透着价值和价值判断因素;二是指从事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的学者在学术研究活动中的价值判断,主要表现在从事学术研究活动的动机上。
学术自由的度,主要是依据学术的社会价值确立的。学术的社会价值,是指学术与社会相互的作用和影响,表现为学术所具有的积极的、正面的社会功能。一般说来,学术的社会价值包括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两类。物质价值,主要指客体同主体的社会、人的生存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物质需要的关系。当学术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人类物质生活的改善、促进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时,便被认为是具有物质价值的。精神价值是相对于物质价值而育的。它是指客体同社会、人的精神文化需要的关系,大体上包括知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等方面。在这三种精神价值中,知识价值就是所谓的“真”,道德价值就是所谓的“善”,审美价值就是所谓的“美”。三种价值的统一,就是通常所说的真善美的统一。“所谓真乃是知识上的善,美乃是知觉上的善;而善则为道德价值的真,美则为表象与知觉上的真,真可以说是知性的美,而善可以说是行为的美。”当学术通过推动哲学观念的变革和思维方式的进步、推动道德观念更新、推动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时,便被认
为是具有精神价值的。
学术的价值、学术的社会价值具有主观性。一方面,表现为从事学术研究活动的学者所带有的主观价值判断上;另一方面,表现在社会高层管理者对学术价值和学术社会价值的主观判断上,反映在对不同类型的学术研究的区别对待中。当一种或一类学术研究被认为具有社会价值时,往往所给予的自由度很大;反之,则受到抑制。由于对学术的社会价值的判断还带有社会高层管理者的主观认识色彩,因而可能会影响到对学术社会价值的正确判断。这是导致一些社会、一些时期学术自由度很小的主要原因。社会高层管理者应对此有足够的认识,尽可能将这种主观认识上的偏差降到最低状态,以使得真正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有充分的自由度。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学术价值,特别是学术的社会价值,由于所站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又有所区别。比如,一些战争武器(如核弹、生化武器等)的研制。这些对于纯学术来说是无价值,甚至是负价值的,因为它们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但对于国家来说,又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们能保卫国家的安全,防止外敌入侵,给国家带来战争的主动权和开战后的胜利。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学术自由度的确立,不应以包括社会高层管理者在内的个人对学术价值、学术社会价值的好恶为依据,而应以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要有利于弘扬真善美,抑制假恶丑;要有利于国家、社会、人类的发展,不得损害国家、社会、他人的利益为原则。弘扬真善美,促进国家、社会、人类的发展是学术自由的目标,是理想状态;抑制假恶丑,不得损害国家、社会、他人的利益是起码要求,是学术自由的最低限度。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知识、价值判断水准的提高,对学术价值、学术社会价值的判断会更趋合理、更趋客观。因而学术自由的度应该呈上升趋势,政府应让学术逐步走向“市场”。当学术价值、学术的社会价值高时,自然有很高的自由度;若相反,学术就会失去其“市场”,伪学术会受到社会、他人的抵制,难以生存。政府只充当“宏观调控”的角色。
三、大学学术自由度的标准
大学应该有更大的学术自由度。首先,这是由大学的人员结构决定的。大学是高素质人才的汇集地,他们对学术价值、学术社会价值的判断能力强,有能力辨别真善美与假恶丑,能感受到各种学术活动之于国家、社会、人类的利与害,应该充分相信并尊重他们进行各种学术活动的觉悟和水平。其次,是由大学的本质决定的。大学研究和传播的是高深学问,这些学问或者还处于已知与未知之间的交界处,或者虽然已知,但由于它们过于深奥神秘,常人的才智难以把握。大学这一本质特征,使其教育和研究过程应该有更大的自由性和探索性。再次,是由大学生的学习特点决定的。大学生的学习是研究性学习,是对高深学问的探讨,需要自由宽松的学习和研究氛围。大学生的身心发展已趋成熟,其思维能力、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能力已相当发展,具有自由的意愿和能力。如果没有一定的自由,大学生的自主性、独特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就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独特个性和高度责任感的创新人才也无法造就出来。
那么,大学的学术自由度是不是应该大到一种毫无束缚的地步呢?当然不是。学术自由如同科学技术一样,是一柄双刃剑,用好它利己利人、利社会利国家,否则相反。因而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有规范的自由。我们认为,大学学术自由的度,应该视学术活动的不同方面区别对待。
第一,学术思想的极度自由。大学的学术自由,包括教学的自由、研究的自由和学习的自由等内容。思想的自由是贯穿以上诸方面的核心。在教学中,从教学内容的组织到教学方法的设计,都包含着教师的思想,教师可以也应该将自己的学术思想融会贯通于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如果在教学中教师没有思想的自由,教师都千第一律地讲授,那将是一种教学的悲哀,师生从事学术研究时,更需要思想的自由。否则,就不会有新思想,更不会有创新。同样,大学生学习中也需要思想的自由。表现在他们可以对知识有自己的理解,可以怀疑、辩驳甚至反叛原有的知识,并形成自己的思想。创新人才的培养,首先必须培养其良好的思维习惯,培养其独立、自由、有创建的思考意识,从而经常进发出创新的思想火花。其实,思想是很难禁锢的,它的实质是一种活跃于内的东西,当受到外界干扰时,可能不表露于外。但人的思想一旦形成,就难以用外力改变。我们提倡学术思想的自由,就是要营造一种思想不受外界约束的氛围,使人们形成良好的多思考的习惯,井将其新思想充分表露出来。一方面可将这种新的思想转化成学术成果,另一方面通过思想的广泛交流,激发他人的创新与创造。应该允许多元的思想存在,提倡各种学术思想的交流与讨论,这样既可以丰富学术思想,又能在交流和讨论中使合理的、真善美的思想光大。粉碎“四人帮”后,我国曾有过一段迷惘期,通过有关“真理标准”思想的大讨论,很快便走出迷途。所以,17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曾指出,思想的自由“对于科学和艺术是绝对必须的,因为若是一个人判断事物不能完全自由,没有拘束,则从事科学和艺术,就不会有什么收获。
第二,学术过程的高度自由。大学的教学、研究、学习的过程,应该有充分的自由。学术思想的自由不需要外界给予多少物质作为条件,学术过程却需要它们。因而,与学术思想的自由相比,学术过程的自由度要小些,它是受一定物质条件限制的。对一些真善美的学术思想,应创造条件让其继续下去,转化为学术成果。反之,则不一定提供这种便利。当然,不提供条件的便利,并不等于强加干预或予以扼杀。因为,有些新的学术思想在当初可能会被看作是荒诞的。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在其诞生初期便被认为是“歪理邪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刚“出生”时,能理解的不过几人。
第三,学术成果推广与应用的适度自由。学校自由的度,应表现在学术成果的推广应用中。对具有学术价值和学术社会价值,即那些符合真善美标准,有利于国家、社会、人类发展的学术成果,应给以很大的便利、很大的自由度。学术成果推广应用的适度自由,还因为,新的学术成果,一般说来还停留在学术理论研究、理论分析和实验之中,若要推广应用,必须有一个经过实践逐步检验的过程。如果轻易推广,将可能是灾难性的。比如,克隆技术,作为学术性的研究,许多国家都给予很大的自由,它为人类探索生命的奥秘、培育动植物良种及部分病痛的治疗等,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至于是否允许“克隆人”,包括我国在内的众多国家都明确表示反对。因为这不仅是一个伦理的问题,还涉及到对克隆出的生命性能的未彻知的问题。再如,原用于治疗感冒的部分药物,由于当初推广它们时对其负面作用还处于未知或未全知状态,使得它们危害人类许多年。虽然现在许多国家将这些药物“禁封”,但已造成的伤害可能是无法挽回的。因而,学术成果的推广应用应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
总之,大学学术自由的度,不应表现在对学术活动过程的约束中,更不应表现在对学术思想的约束中,而主要表现在对学术成果推广应用的约束之中。
作者系南通工学院咸教中心助理研究员主任助理
(江苏南通226007)
责任编辑:黎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