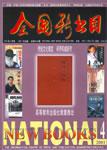贾平凹:追寻永远的“香格里拉”
文/周思明
“香格里拉”这个洋味十足的名词儿,可能会引起人们对现代都市中那一幢幢刺破青天且金碧辉煌的高级酒店的联想。其实,在西方,它不过是一个自然原始的精神家园罢了。与湘西作家沈从文一样,陕西作家贾平凹在完成了从一个货真价实的农民到蜚声海内外的著名作家的历史进程之后,仍念念不忘自己是个农民。贾平凹那深沉的“农民情结”,他那“与其广阔而浮面,倒不如狭小而深入”的典型的农民式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诚朴和易感的秉性,他的对人的“性格”和乡土语言、风土人情的高度敏感及特殊才情,给他带来了文学创作上的巨大成功。面对贾平凹这部传记文学作品《我是农民》(陕西旅游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以下简称《农民》)不由令我产生一个认知:传记是历史的造山运动之记录,自传必是以往的“我”与今日的“我”,彼此间进行的一场关于“我”的历史性对话,这就需要读者诸君努力寻觅到那一扇门,那扇可能通向作家心灵深处的深藏不露却处处显现的“香格里拉”之门。
贾平凹曾孕育生产了一大批与陕西黄土地上农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文艺作品。贾平凹总归是农民出身,无论其身居何方,位居何职,出笼何物,总是把他对陕西农村故土,对在这块土地上生衍繁息的父老乡亲的血肉之情,还有他本人的农民习气,有意无意地袒露出来。有人说,贾平凹就是为了陕西黄土地才来到人间的,陕西乡村那雄浑壮阔、苍凉凄美的自然风光,也仿佛是为贾平凹的画笔而独存的。印度人曾赞谓泰戈尔是印度歌鸟巢中诞生的孩子,这不仅是因为泰戈尔同鸟一样善歌,更重要的是,这位老翁永远为印度古老而静谧的土地而歌,为嬉戏在长流不息的恒河两岸天真无邪的孩子们而歌。泰戈尔永远是属于印度的。贾平凹呢,把他比作一只啄食飞翔于黄土地上空的鸟儿,当是贴切的。为了这块西部农村部落的芸芸众生,苍茫万木,以及亟待冲破地壳的生命涌泉,他以一个农民作家的别具特色的劳作,发出独特而别致的啼唤。
在贾平凹身上,农民和作家是合二而一、水乳交融的。他的小说《商州初录》、《鸡窝洼的人家》、《天狗》等等,是一篇篇淳朴民风的赞美诗。在《农民》中,作家以其柔热的笔触,写道:“丹凤境内十之有七都是山寨,平川地就是丹江两岸,而两岸好地方只有龙驹寨、商镇和棣花。龙驹寨是县城,称城里,棣花称街,商镇就是镇。两年前第一次到镇上,是父亲用自行车带我去的。镇上的街道那么长,正逢着集市,人多得像要把两边木板门石房挤塌了似的……(《初中生活》)”。寥寥几笔,家乡风情画跃然纸上。贾平凹怀着对农民、农村的一片挚爱,以一个亲见、亲知、亲历的土著人身份,用漫叙的笔调,从容落墨,娓娓道来。其间融入了作家童年生活的情思与经验,这使得他笔下的民俗描写神奇又丰厚,优美且和谐,震响着艺术的强音——对中国,是一种独特的乡野之音;对世界,则是绝无仅有的民族之音。
贾平凹个人的生活实践,铸就成了一个痴心不改的“农民”,形成了他创作生涯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文化选择。没有“农民”,就没有贾平凹这样一位作家。“农民”把贾平凹推上文学道路,并规定了他文学创作的生活观、文艺观和审美观。其实自称“农民”正是作家在文化选择上“发现自己”的智慧表现。何谓“发现自己”?且听高尔基是怎么说的:“人的使命是: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对生活、对人生、对特定事实的主观态度,并把这种态度用自己的形式和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贾平凹一再强调“我是农民”,这不应被认作是作家一般意义上的自谦、自嘲或调侃之词,恰恰相反,贾平凹是从个人具体实际现实生活的独特感受,以及独特的表现式样和语言。一句话,作家只有发现自己,才能成就自己,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个性和创作个性,才能找到通向自然美丽的“香格里拉”的那扇门扉。在作家贾平凹向世人宣称“我是农民”时,实际上他是在向我们传达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
我就是我,你不可改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