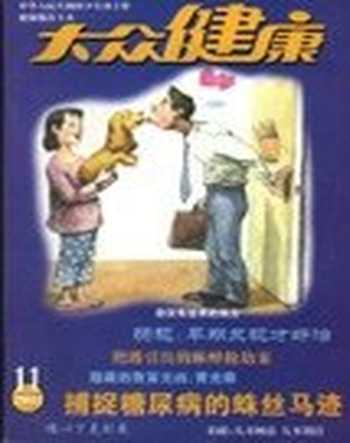一号患者
晨 星

一天早晨,我无意间发现脖子上有个淋巴结很显眼,心想:乖乖,它怎么这么大!一周以后,我发现锁骨上方也出现了一个硬块。我把这事告诉了妻子帕蒂。她立即催我去医院检查。可是,我们公司研制的CEPRATE系统正处于关键时刻,我怎么能离开呢?尽管帕蒂每晚催我与大夫预约时我都满口答应,可是第二天一到公司就忘了。
最后,我总算抽空去了一趟医院。大夫给我做了全面检查,并先后做了两次淋巴结组织活检。在我49岁生日那天,奥利大夫给我发了个电子邮件说:我患了上皮细胞淋巴癌。我一下子楞了,上皮细胞淋巴癌目前尚属公认的顽症,这种癌细胞特别活跃,对传统的化疗药物具有罕见的抗药性。害怕、恐惧攫住了我,我心烦意乱,第一次意识到死之将至。
奥利大夫建议我不妨试试干细胞移植,即先从我体内取出干细胞,将混杂其中的癌细胞杀死之后,再将干细胞移回我体内,重建我的造血和免疫系统。我们公司研制的CEPRATE系统正是用于从血液里提取干细胞的。真没想到,现在世上惟一能救我的竟是我们自己公司正在研究的新技术。
我叫来了公司的生物科学家乔·塔尔诺斯基,向他叙述了我的病情,并告诉他:我已决定采用干细胞移植疗法,而且准备用我们自己研制的CEPRATE系统提取干细胞。这意味着,我将是用这一医疗仪器的第一位患者。但是CEPRATE系统尚不能保证从任何被癌细胞污染的血液里提取纯粹的干细胞,乔他们正在研究解决这一问题。现在由于我的病情,他们必须在8周内解决这一难题。显然,我有点儿强人所难。
乔立即成立了一个攻关小组,成员都是精兵强将,例如血液净化专家尼科勒·普罗沃斯特、曾在斯坦福大学专门从事免疫学研究的沙伦·亚当斯等。开始几周,进展缓慢,不是淋巴癌细胞过多,就是提出的干细胞过少。俗语说“穷则变,变则通”,一次次的失败使攻关小组改变了提取方法:不再直接提取,而是先将已经净化过的血液中绝大部分淋巴癌细胞杀死,然后再提取干细胞。这一次,他们成功了。
5月下旬的一天,奥利等陪我在医院预约进行干细胞移植的时间,最后订为6月17日进行。为做准备,我提前住进医院接受化疗以刺激骨髓生成大量的干细胞。每次化疗过后,我都恶心得要命,头发纷纷脱落,血中的白细胞急剧下降,连续3天,我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6天之后,我的骨髓终于开始生成干细胞,白细胞也开始回升。与此同时,攻关小组也在做最后的准备。
6月17日早晨,我住进了哈奇森癌症研究中心,开始接受干细胞移植。一般人每一微升血里的干细胞不足50个,而这时我每微升血里的干细胞至少有300个。医务人员首先从我体内抽了一杯鲜红的血液,然后研究人员将淋巴癌细胞抗体注入其中。30分钟之后,装着我的鲜红色血液的袋子吊在了净化仪器的顶端。遗憾的是,经化验清洁过的血液里仍然混有淋巴癌细胞。为此,尼科勒等人在清洁过的血里又加入了两种特殊化学反应物,期望在第二次净化时,能将剩余的癌细胞全部清除掉。这次净化过程大约用了3个半小时。我焦急地等待着。结果是,血里99.9%的癌细胞已经被清除,然而毕竟不是100%,如果将这样的血注入我的体内,那剩下的0.1%的癌细胞仍可致我于死地。
经过分析,尼科勒他们最后决定增加两种特殊化学反应物的量,再拚一次。人常说,科研成功是灵感、奉献精神与辛勤汗水的结晶。可要我说,科研成功有时是在绝望中到来的。第二个星期二的早晨,沙伦再次赶往癌症研究中心,随身带了几套备用的净化装置、几瓶淋巴癌细胞抗体和新合成的特殊化学反应物。成败在此一举,所有的人都捏着一把汗。但是,在进行最后一道净化时,血袋里的血逐渐凝固,致使净化程序无法继续进行。天啊!难道我最后的希望就要因为这简单的血液凝固而葬送吗?就在这穷途末路时,沙伦急中生智,决定把血袋一分为二,另外再增加一套净化装置,两套净化装置同时进行,以缩短时间减少凝固,终于使整个净化过程按时完成。化验结果令人振奋,提取的干细胞100%纯净,没有一个癌细胞。
7月26日,我住进了华盛顿医院6318房间。这是一个专为放射性治疗预备的特殊房间,墙壁里有6英寸厚的铅板。在进行干细胞移植前,奥利大夫还要通过放疗、化疗杀死我血液里的淋巴癌细胞,进行最后一次清理。放射性物质刚一进入我的体内,立即展开了一场异乎寻常的战斗。数十亿个淋巴癌细胞抗体在我的血管里追捕癌细胞并把它们杀死。恶心接连不断地向我袭来……
我已经4天没吃东西了。4天中,我只能闭目躺在床上。更糟的是,精神上的痛苦比肉体上的痛苦还难令人忍受。我渴望身边有人,哪怕只是碰一碰也好。帕蒂与孩子们每天都来看我。尽管他们呆在铅板后面,大夫还是劝他们不要久留,以免遭受辐射。随后的几天越发难熬,不时令人想到地狱。12天以后,奥利大夫终于允许我回家过一个晚上。我儿子杰米和本接我回家。这时的我浑身软弱无力,但那天晚饭,我竟然吃了两块比萨饼,而且没感到恶心。
随后进入移植的最后阶段。8月12日,我的经过提纯的干细胞重新注入我体内。整个过程只用了10分钟。如果成功了,提纯的干细胞在我的骨髓里安家、分裂、繁殖,帮助我重新建立起造血和免疫系统。在此期间,我必须千方百计地避免感染、发烧或流血。因为这些看似寻常的疾病,对我都潜伏着致命的危险。
不幸的是,干细胞注射的第二天,我突然发烧。大夫一天3次给我量体温,给我注射了不同配方的抗生素。但是,我的体温仍是有增无减。帕蒂急得发疯,白天黑夜守在我的病床边。我体内的白细胞仍是零,同时红细胞和血小板的数目也开始下降。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大夫不得不开始每天为我输血。
还有更痛苦的是浑身疼痛。吗啡及其他止痛药使我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从早到晚昏昏沉沉。清醒时,我甚至想:如果每一个患者都像我一样遭受如此折磨,我和我公司的人至今所付出的努力值得吗?
干细胞移植后的第10天,高烧终于开始下降了,我也逐渐恢复了神志,慢慢地我能吃东西了。几个星期以后,我坐上轮椅,回家了。9月下旬,奥利又给我做了一次检查,我的淋巴系统已经没有癌细胞了,由于化疗脱得光秃秃的头顶也逐渐长出了头发。几个月之后,我完全康复了。我又可以拉上帕蒂驾驶游艇出海了。
痊愈后,我又回到公司。这次在死亡线上徘徊的经历让我重新理解了生命的价值,也重新了解了我们工作的意义。一年来,我和公司的科研人员殚精竭虑,攻下了一个个科学难题。今后我们还会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