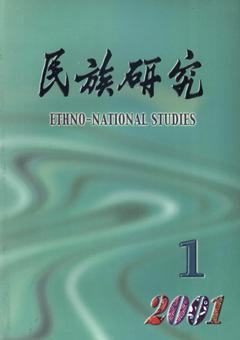《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评析
广东地处五岭南海之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先秦时期,这里居住着土著越人,他们独特的文化创造,是后世岭南文化的底本。秦汉以降,北方汉族不断南迁至广东不同地区,他们带来的中原文化,一方面与当地越人文化相融合,一方面适应不同的生态环境进行文化的重整再造。至明清时期,广东汉族三民系的文化形貌已与现代基本相同。与之共生的是壮、瑶、畲、回、满等族群的文化。这些少数民族,处在汉民族包围之中,却在文化交融与互动的背景下不同程度地保持着自己的传统。这种天然的区域格局、独特的人文景观,是广东进行族群和区域文化研究的先天优势。由黄淑娉先生主编的《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简称《研究》),便是这样一部足以体现人类学区域性研究特色的力作。
第一,秉承南方人类学之学术传统,强调四个分支学科的综合研究。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的体质形态和社会文化现象的学科,包括体质人类学、民族学(狭义的文化人类学)、史前考古学和语言人类学。解放前,我国南方人类学家杨成志、林惠祥和江应棵等教授便力主四学科的结合。80年代初,梁钊韬教授在中山大学复办人类学系,同样主张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建构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就此而言,《研究》是一部承其统绪之作。
文化是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充分发挥各学科的专长,不仅有助于抓住一个族群的文化特点,也可以整体把握一个区域的文化形貌。史前考古学的研究,证明了自马坝人到南方古越人的体质形态南方特征渐趋突出,也再现了古代南越人的文化特征及其与周边文化的相互影响,这是岭南文化特色的历史渊源。对广东汉族的体质测量过去虽有零星资料,但对广东汉族三民系体质特征的研究,对910人、33项指标的准确测量,在中国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方面该书还属于首次。测量的数据表明,三民系均具有华南人的体质特征,并且通过聚类分析,对各民系与百越民族的融合程度以及南迁前的所居地作出了判断。从而在体质形态的研究上为广东汉人来自北方的事实提供了新的论证。语言是族群重要的文化特征,也是其心理认同的重要标志。对复杂的广东语言进行人类学的研究,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其存在的诸多特性,不仅跨越了纯语言学的探讨,而且为广东语言的分布格局寻找到了内在的依据。其中,对诸如粤方言的扩张之势、深圳和珠海普通话语言社区的形成,以及多元背景下的香港语言、语文的格局等状况,均进行了颇具见地的文化分析。
第二,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着重以个案研究揭示文化的本质。田野调查是我们正确观察和认识社会的研究方法,也是我们理解被研究者如何用自己的语言和思维来表达历史和文化的重要途径。然而,只有这种共时的研究,不能追溯社会文化现象的历史发展,无法评估资料提供人对过去的阐述。因此,只有将历史研究和实地调查相结合,才能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这是人类学诠释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基础。《研究》一书鲜明地体现了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特色。
广东的历史文献不仅有《广东新语》一类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通志、府志、州志和县志更是卷帙浩繁,这为区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材料。此外,海外人类学家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广东。从1918、1919年库尔伯(D.H.Kulp)对广东潮州凤凰村的民族志调查,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人类学家因未能进入内地而在香港新界地区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到8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波特夫妇(S.H.Potter和J.M.Potter)对东莞茶山镇的研究著作《中国的农民:革命的人类学》一书出版,学者们翔实的调查内容、独特的研究方法,为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诸多可供参考的范式,《研究》一书在许多方面也给予了回应。每一个族群的文化特点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随着历史的前行,也都在不断地摒弃和创新中发生着或急或缓的变迁。记录文化的现状、描绘出变化的轨迹、分析其内在的动力、预测未来的走势,这是《研究》一书结合文献资料和对17个市县的一些社区(村落或管理区)进行实地调查后,完成的巨大工程。宗法家族制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影响可谓深刻持久。新中国成立前夕,这种制度在内地已被基本摧毁,但在广东的一些地方其残余却依然发挥作用。研究者借助历史文献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家族制的起源与发展及其在广东的变化和特点做了清晰的梳理。同时又结合三民系9个个案的实地调查,分析了80年代后家族制再度复苏的背景和在现实生活中的功能,从而精当地阐释了其存在的弊端和一度被抹煞了的积极作用。
第三,汉族和少数民族研究并举,但突出了汉族不同民系和群体的文化研究。广东是历史上少数民族广布的地区,如今聚居在粤北的壮族和瑶族,主要分布于罗浮山区、莲花山区和凤凰山区的畲族,以及散居于城市中的回族和满族,族源不同,文化特点各异。他们是广东区域文化的组成部分,对这些民族与汉族相互交融的研究,也为我们在比较性和整体性上把握这一区域的文化特色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与少数民族相比,这里的汉族文化同样具有特色。广东背靠内陆,北部多山地丘陵,中部为河网密布的冲积平原和三角洲,南濒南海,特定的生态环境使这里的地方文化色彩十分鲜明。汉族三民系的格局是不同时代、不同境遇下的南迁汉人,用不同方言和文化建立自己汉人身份的结果。民系观念,滥觞于客家人的身份认同,也是潮汕人和广府人身份认同的依据。民族以不同的文化特点相区别,民族的自我意识是在共同的文化中产生的。同理,文化也是民系认同的标志。同一民系的人群说同一种方言,有共同的生活方式和信仰观念,并因此形成了共同的族群意识。只是与不同的民族相比,不同民系同源于一个母体文化,彼此间的差异要小一些。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认识,《研究》重点探讨了汉族三民系的文化特点,描述了与粤文化同根共生的香港文化、澳门文化,以及深受三民系涵化的水上居民(疍家)的生活景况。
对文化人格的研究是人类学的专长。文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其稳定性使之在世代之间进行传递和互动中,塑造出了相应的文化人格。《研究》通过对三民系族群心理的测试调查,加之对其文化源流的梳理,分析了各民系社会心理的成因,并概括出了他们各自的族群精神。
第四,大、小传统文化兼顾,但更钟情于对民间社会生活探讨。人类学以对人类社会、人类行为及人类本性的分析为宗旨,这决定了她的研究必将把大传统文化和小传统文化、人类行为及人类本性的分析为宗旨。广东的民间文化,则上续越人古俗,中通汉地文化,近有外来风习之洗礼。广东人借助珠江三角洲地利之便创造的多元经济,决定了他们经济生活的基本形貌。汉族传统社会的宗法家族制,至近代已趋于衰微崩溃,而广东发达的家族制度却一直保留到现代,依附于家族制度的家族世仆制,在解放以后才被彻底摧毁。不落夫家与自梳女的习俗,虽已拉下了帷幕,但在民间生活中却依旧余音未绝。广为流行的捡骨重葬,寄予了岭南人对死后生活的理解,从中亦可追溯其百越文化的渊源。饮食文化融会南北、中西,民居建筑极具南国地方特色。繁多的节日结合着民间信仰,祖先崇拜是其信仰生活的基底和内核。民间工艺有
广府的广绣、牙雕、端砚,潮汕的金漆木雕、潮绣、潮瓷;艺术有粤剧、粤曲、潮剧、潮州锣鼓、汉剧、客家山歌等。正是这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方式,构成了民间社会的生活图景。应该强调的是,大、小传统文化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因为前者中渗透着乡土社会的印记,后者中始终熔铸着上层文化的影响。社会文化的本来面目是二者联系和互动的结果。
人类学之传统,是从民间社会的角度来审视社会和文化变迁的轨迹。《研究》正是基于细致而深入的调查,通过或全面或专题的个案研究,记录了这可能会转瞬即逝的生活景象。可以说,学者们源于乡土的本色研究,为我们从一个小社区透视一个大区域的发展,乃至中国社会适应时代要求的变迁,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文本资料。这些调查报告,均收在《研究》的姊妹篇《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调查报告集》之中。
第五,立足乡土社会,关注现实问题,显示了人类学独特的应用价值。人类学从产生之初,到研究视野不断扩展的今天,始终是一门极具应用价值的学科。她以文化的视角,关注民众生活,关注社会发展,着重对现实问题做出文化的解释。《研究》对各民系物质生产、生活俗制、民间信仰,乃至族群心理的描述分析,对协调区域内族群关系、扩大对外交流、引导社会变迁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也在文化的根基上为经济的发展寻找到了解释和依据。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多元经济的发展,使较强的商品意识早已成为其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能率先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经济快速发展,除了凭借其天时、地利的因素之外,外来工群体异质文化的介入、潜在的重商传统、开放务实的心态亦是绝对不能忽视的文化因素。
与城市化同步的是农民物质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以及各种生活俗制的相应变迁。然而,无可否认的是,精神文化的转型却步履维艰。人们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的滞后现象甚为严重。文化变迁之迅猛,使原有的文化传统与新的生活方式在人们的精神层面上发生了强烈的冲撞。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尽享现代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又把已逝的民间陋习重新视为圭臬,这是现代化进程的巨大阻力。如何逐步化解二者的冲突,实现文化的整合,又该以何种方式完成两种文化的内部转换,是《研究》没有解决的问题。但研究者毕竟在繁杂的文化事项背后,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人类学、民族学自20年代下半叶引入国门,始终处于中国化的进程之中。期间融入了几代学者的学术实践。本土化需要对国外的人类学理论和实践进行客观的分析,需要研究方法的借鉴,更需要基于大量田野工作之上的创新。其基点在于实践。这是分析、借鉴乃至创新的根本前提。《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在广东这一汉族区域文化特点突出的环境中,以人类学家独创性的求索,关注民生之情怀,撰写出了这部具有特色的研究著作。这不仅是推进人类学本土化务实的研究成果,更是对中华文化研究的贡献。
(作者孙庆忠,1969年生,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生。地址:广州市,邮编510275)
[责任编辑刘世哲]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