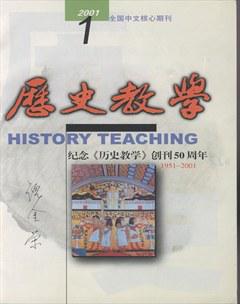《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序
戴 逸
一部世界文化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各民族文化相互传播、碰撞、融合和不断创新的历史。学术界比较公认的人类“原生文化”发祥地的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也有人称作尼罗河文明、两河(底格拉斯河、幼发拉底河)文明、印度河文明和黄河文明,就是在文化的交流中不断创新和发展,并影响了世界文化的进程。发源于尼罗河北部的埃及文化,由于和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化相距不远,约在一千公里左右,又没有难以逾越的地理屏障,相互交流相对比较频繁。大量的考古成果已经证明,埃及和两河流域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技术乃至天文、历法、语言文字、算术、服饰等方面有许多相同或相近的地方。埃及最早的象形文字,就曾受到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图画文字的影响。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地区)的苏美尔人所创造的楔形文字,在公元前两千年中期逐步变成了西亚各族人民的通用文字。由于埃及文化和巴比伦文化的大量交流和融合,学术界也有不少学者将其合称为东地中海文明或西亚文明。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文化,虽然受伊朗高原的阻隔,和西亚文化交流非常困难,但目前的出土文物和一些文献记载充分说明,两个地区也时常有人员和货物的往来,美索不达米亚的图画文字曾传入印度,西亚地区还出土了印度河流域生产的哈拉巴文化的印章。而作为欧洲文化发源地的希腊文化,很早就和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有着较为广泛的交流。在埃及曾发现了一个很古老的仓库,里面藏有希腊克里特岛生产的各种金银器皿;在克里特岛上出土的许多文物,则明显地可以寻到埃及文化的因子,克里特的文字、壁画、印章、石器以及各种装饰品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埃及文化的影响。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产生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加里特字母,很早就传到了希腊,希腊字母和阿拉伯字母都是在乌加里特字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来的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直至今天的英文、法文、俄文、德文、梵文、阿拉伯文等,就字母来讲,都是乌加里特字母的进一步发展。文化的传播已经超越了种族和国界。至于公元前6世纪希腊和波斯之间的战争,特别是公元前4世纪北起希腊,南到埃及,东抵南亚次大陆印度的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欧洲文明、阿拉伯文明和印度文明更互相冲突、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讲,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和欧洲文化,从原生期至后来的再生期,并没有绝对严格的疆域限制。
中国文化在原生期由于受地理因素和生产力的限制,无法冲破喜马拉雅山脉的阻隔,与西亚文明和南亚文明交汇。但是,仍然遵循着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努力向外传播,与他民族文化交流,出现了包括朝鲜、日本、越南以及东南亚广大地区的中华文化圈,同时在汉代以后与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乃至欧洲文化有较多的交流和融合,显示了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受容性。张骞通西域、丝绸之路的出现,中国和阿拉伯及地中海地区的文化交流达到了一定的水平,造纸、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的西传,改变了西亚、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风貌。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高僧克服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促成了在汉代以后逐步扩展的中印佛教文化交流,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而明清以来,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欧洲西方文化的呼啸东来,更迫使中国文化在困境中艰难而有力地向现代化迈进。学术界的一些学者将秦以前称之为中国文化原生时的独立发展时期,将汉至宋概括为中印文化的融合时期,将近五百多年以来归之为中西文化的深刻交汇时期。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则形象地把中国历史的演进说成是“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三个相互递进的时期。这些概说不能讲百分之百的科学,但道出了文化交流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毫无疑问,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等曾对中国文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文化也直接或间接推进了欧洲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印度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进步。文化交流促进了人类文明,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随着对文化交流重要性认识的逐步深化和近代学术体系在我国的逐渐建立,中国学者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即开始了具有近代学术意义的文化和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尤其是在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直接推动下,五四前后出现了研究文化的热潮。从推进中国全面现代化的目的出发,一大批学者以西方文化为重要的参照系,致力于解决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关系问题,也就是老生常谈的古今中西问题。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虽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学术流派,也引发了影响深远的东西文化大论战,但问题远没有解决。这说明中国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的艰巨性。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五四之后特别是二三十年代,产生了一批相当有水平的文化研究成果。就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来讲,已经写出了几部很有价值的学术专著,为这个新兴学术门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向达的《中西交通史》、张星火良的《欧化东渐史》和《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此后,历史在推进了半个多世纪之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80年代以来学术界和知识界又出现了文化研究的热潮。除了继续讨论古今中西文化关系之外,对世界流行的各式各样的文化理论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将文化的研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上,也取得了骄人的学术成果。比较有水平的专著就有二十多部,周一良先生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季羡林先生所著的《中印文化交流史》是其中的佼佼者。不过,从总体上来考察,这些著作大都是从国别、地区或某方面的问题出发,分专题去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这当然是非常必要和有价值的;如果进一步从推进文化交流史的深入研究出发,还应该编写一部大型的,按照整个历史发展顺序,比较全面系统地来论述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沿革的专著。为弥补这一缺憾,李喜所同志主编了这部5卷本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按时间先后,深入评述了从古代到1999年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并列入了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九五”重点项目。这实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该书贯彻厚今薄古的原则,依据中外文化交流的客观实际,上古至明中叶1卷,明末清初至鸦片战争1卷,而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半世纪有3卷,特别是首次将新中国以来的中外文化交流单列1卷加以详尽的叙述,略古评今,重点突出,将历史和现状有机的结合起来,给人一种历史的整体感。如果详细阅读该书,还可以发现较为明显的3个特点:1北冉舷低场⑷面,但重点突出。该书将中国传统史学的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写作方法较好地结合起来,交叉运用,以编年体为历史发展的基本顺序,把五千年的中外文化交流分阶段加以前后编排,历史顺序十分清晰;具体到每一个阶段,也可以讲每一卷,则在照顾到前后顺序的前提下采取纪事本末体的方法,分专题进行较完整的评述,这就使具体的文化交流事件或人物相对独立和深入,增加了历史的厚重感。每一卷后所附的大事年表,不仅便于查阅,而且补充了纪事本末体写作中年代会打乱的不足。可以讲在整体编排上,该书是独具匠心的。在内容的选择上,该书也颇有特色,做到了面和点的合理而有机地结合。全书在对五千年的中外文化交流进行系统描述的基础上,对影响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文化交流现象都作了重点考察,尤其是加强了交流的背景和结果的剖析。像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张骞通西域、佛教与中国文化、四大发明与世界、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西学东渐、留学生与中外文化、港澳与中西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改革开放与文化交流、当代西方思潮与中国等几十个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问题,书中都进行了全面而有一定哲理的探讨。有了这些重点画面,自然会加深读者的印象并有所启迪,由历史联想到现在乃至未来。
2苯隙嗟亟行了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比较是交流的前提,任何文化交流都是在相互比较下进行的,所以只有准确地了解了不同文化的不同特点,才能较好地去论述中外文化的交流。一部好的文化交流史必须突出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应该说,该书在这方面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对于欧洲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异同,书中都用了一定的篇幅加以论述;即使是同一文化圈内的文化,如日本文化、越南文化、朝鲜半岛文化等,书中也力所能及地作了评论。可喜的是,在一般剖析这些文化的不同特质的基础上,该书还运用文化生态的理论试图从不同文化生成的客观环境上去加以比较研究。由于地理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人文环境的差异,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文化就必然有不同的特质。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是这个道理。该书能够从文化的生成环境和生存状态来进行比较研究,就使文化的研究大大深入了一步。随着文化比较研究的加深,自然就为文化的融合性和变异性,以及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可能性等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样是中外宗教文化的交流,佛教就会在中国生根开花,基督教就较难发展;而同样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就出现了不少新的流派,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化的印记。这都是文化的差异性使然。对这些不同的文化现象进行比较研究,不仅能够提出一些新的观点,而且会给人以哲理性的思考。总之,以文化的比较为基础,去叙述文化交流的背景、过程、手段和影响,既避免了以往的一些论著平铺直叙的罗列现象的缺陷,又增强了该书的学术深度。
3备挥薪锨康睦砺厶剿骶神。对于文化交流中的许多理论问题,该书不仅有所涉及,而且大胆地提出了作者的看法。尽管个别观点还有可商榷的地方,但这种勇敢的探索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例如,各民族文化的高低优劣问题,很难界定和评判,而这个问题讲不明白,所谓文化交流就不大好叙述。书中提出了一个高势能文化向低势能文化传播的观点,认为一般情况下总是高势能的文化向低势能的文化传播,低势能的文化只有在融合高势能的文化中才可以生存和发展。这种观点虽然有待进一步完善,但解决了研究文化交流史的一些难点,有开拓意义。再如文化的传播机制和接收机制,书中从理论解析和实际史实论述的结合上重点作了评说。提出良好的传播机制与优良的接收机制的完美结合,才会出现高层次的文化交流,二者缺一不可。而且还对文化的传播和接收机制作了理论上的探讨,发人深思。还有,文化交流中的民族性和时代性问题,非常难以把握。往往强调了民族性,就可能关闭开放的大门,拒绝文化的交流;提倡了时代性,又难免会引发不顾民族尊严,崇洋媚外,将文化的交流引入了歧途。该书在总结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后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国人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文化交流的方向和面貌。一个高素质的民族就会较好地处理保持民族传统和跟上时代潮流的关系,去创造高水平的新文化。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来讲,现代化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石,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应统一到现代化上来。这些理论探索,无疑增加了全书的亮点。
(戴逸,1926年生,江苏常熟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史学会会长、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社科联副主席。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代史稿》、《简明清史》、《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乾隆帝及其时代》、《履霜集》、《繁露集》等。)责任编辑:蔡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