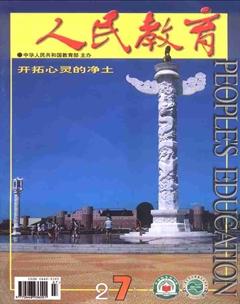天望先生
雷久相
初识天望先生,已是大学二年级了。当时,先生教我们“古代汉语》,并兼任班主任。
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上午,先生虽已满头白发,却龙行虎步地走进了教室忽然,他劈头就朗诵起毛泽东主席的《清平乐·六盘山》,又从“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二句中掐头,用极规范、极道劲的楷体,写下“天望”二字待学生们大声或小声地念起来后,他又淡淡一笑,点点头。然后,他在“天望”前添了个“张”字……倾刻间,教室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先生连同窗外的秋阳,就这样无遮无挡却又无限怡人地定格在我们的心里。
先生的嗓音粗而沙,所操普通话中饱含着永州的特色,常惹得三五同学掩口嗤笑.先生见了却并不气恼,反而淡然作笑曰:“我是‘乡音无改鬓毛衰了,为使同学们日后出言不至于如我般‘呕哑嘲哳难为听,老朽不耻献丑,权当抛砖引玉吧,望谅!望谅!”大家立刻哑了笑,个个正襟危坐,全神贯注于先生讲课:
先生讲课极投入,每入佳境,往往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明亮的目光共睿智的火花飞扬。他那花白的稀发,随着连珠似的妙语而灵动,使我们在萧瑟的深秋里变得生动,让长长的酷夏变得短暂
一日,先生的课正讲得来劲,忽然飞入一只蝴蝶围着讲台翩翩起舞,有心痒者就啧啧不已,先生却似无睹,仍是滔滔不绝于苏东坡的《蝶恋花·密州上元》。此时,好像九百多年前密州山城元宵节的寂寞冷清尽写在先生脸上,我们也恍惚置身于“火冷灯稀”的“昏昏雪意”之中了:后来,那小蝶竟擦先生的鼻尖而戏了。于是,先生便挥手驱蝶,并蹙眉道:“好像我没招惹你嘛。“全班哄堂大笑,而先生不笑,仍只顾讲课。不一会儿,那小蝶又落到了窗边正埋头做笔记的一女生头上,先生就憨笑:然后,他点点头说:“得其所哉!到底是‘蝶恋花啊。”笑得大家前仰后合,直唤肚痛。
先生讲课从不翻讲义,但每次又都腋下夹着绿皮本子进课堂:一些好奇心强的同学,疑心先生有些装样子,于是趁下课时间去偷翻,却见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规矩得似印刷一样,先生阅卷,也使用毛笔,那些点、横、竖、撇。绝不苟且:学生一份简单的作业,他有时竟写上数十字的评语,令敷衍者瞠目结舌。
记得有次期末考试,我们班里有一位同学得了59分,他非常担心补考,便壮着胆子,晚上去先生家中请求通融。谁知先生立即戴上老花眼镜,鄭重其事地找出试卷,认真地复查一遍后,正色道:“你只得这个分,不能再加了。”同学气急,欲拂袖而去。先生将他唤住,而且当晚为他补课,直到深夜。
天望先生是属于那种一生坎坷,晚年辉煌的人。这位当年武汉大学的高材生,因为“大跃进”时说了些不合时宜的话,被打成右派回乡改造长达20年。这期间,先生拖过板车,当过农民,后又到小学代过课。直到四十几岁时,他才与一位地道的农村妇女结了婚。在先生身边求学的那些岁月里,我们时常看见先生携苍老羸弱的妻子,和两个刚上小学的儿子在校内外散步,走出一路恩爱,带来一路温馨。我们有时不禁为之心酸,更为之敬仰。
面对天望先生,眼前总如矗立着一株苍劲而灵动的古树,长满了富有稚气的桠,丛生着天真的叶。先生的为人,是地道的真人挚性。他呼学生总是称“同志”,从没有寻常的“师道尊严”。先生讲授的《古代汉语》,本是艰涩难学得让人闻其名而做恶梦,可因为先生的知识博大精深,灵慧丰厚,使得他的课随意宛转,行云流水,深入浅出,又“死去活来”,而且每每上出了一种韵味、一种境界、一种气氛。听先生讲课,我们常常觉得可以闻到一股香气,犹如兰馨,又似檀香。能有幸听他讲课,至今想来,仍觉得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我们毕业后的第二年,先生便调回武汉大学任教去了。我们虽然从此断了音讯,但先生的音容笑貌和师表风范,却一直跃然我的心中,激励我时时奋进,以不愧为先生的弟子……
祝福您张天望先生,我们崇敬的老师,愿您晚年幸福,永远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