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 道
●牧 铃 吴 柱/文 ●大 伟/图
日球向地平线坠落时,那辆美式GMC军用十轮卡车总算翻过了大沙丘,回到了那一小片行将枯槁的胡杨林子边。
他提醒过她。还在4个小时前他就提醒她岔错路了。她非要跟他拧着。她宁可多绕几公里路也不愿在他面前认输开倒车,却没料到这一绕便是130公里,她驾着车子如同闯入了迷宫,在大漠里白白兜了半天风。
隔着驾驶室中间那道专为她特地设置的铁栅子,她朝那边的他瞥了一眼。
那人干瘪得像一堆剩下的脏衣,灰扑扑的,扔在驾驶室一角。如果不是那双铐在扶手上的爪子,几乎难以发现他的存在。
他的眼珠凸露着,漠然地凝视着窗口变换的单调景色。
绕过胡杨林,大卡车喷一路烟尘,追向那轮血色的落日。霞光给塔克拉玛干千里沙原镀上一层眩目的金辉。枯树桩,灰绿的骆驼蒿,偶尔还可以看到一两只狼,在晚风中翘首观望,似青铜雕塑,点缀着这一方死寂。
她指望在天黑之后看到营地的灯火。
然而,那期待中的亮光迟迟没有出现。车灯前方的车辙却不知在什么时候消逝了,再往前,松软的浮沙侵吞了路面。
又是一条废弃的古道牽
“这一次你白跑了90公里。”他宣告,声音安详得有些麻木。
“干嘛不早说?”
“说了也白说,不如省着唾沫。”他说。
咬咬牙,她猛推操纵杆,大卡车倒过了头,疯也似的冲散了一小群狼,向来路开去。
那些狼撒开又瘦又长的脚杆子,以优雅的姿势轻快地弹跃着,紧追在卡车两旁。她憋着口气,把油门加大到极限。车速却反而开始减慢——油箱空了。
狼群赶过了车头,乱糟糟地,在车灯的光柱里躲避着。大卡车不甘心地滑下一截斜坡,终于无可奈何地停下来。
她皱了皱眉。
她的空车箱里放着满满一桶油,200公升,足够她在沙漠里兜风的。可恼的是那些龇牙咧嘴的饿狼。车一停,驾驶室两侧便有数不清的狼爪子在抓挠车门。她不知该怎样去汲油。
从座椅后拿出一支七九步枪,她拉开枪栓,把窗玻璃旋开一条线,砰地一声枪响,狼群四散开了。
“给我开铐!”男人突然喊,“趁这刻,我去加油!”
她不客气地用枪管在他的肩胛上杵了一下。全部加油过程只需两三分钟,她不必急在这一刻。
“别那么凶,小妞!”他一反平素那要死不活的声调,“这会儿,狼还怕枪响,等它们熟悉了,你就再也没机会加油了!”
她不再理睬他。把整副玻璃窗打开,她将步枪伸出去,静候着。
“如果你还想活着回去,就赶紧下车加油。”他透着齿缝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回答他的,是第二声枪响。
他于是不再开口,却不安分地将手铐拽得咯嘎作响。
5分钟,或许更久一点,逃散的狼群才重又聚集,分两路向卡车包抄过来。她端枪瞄准。三记点射过后,沙地上躺倒的黑影已经增加到4条。
她冷冷一笑,从容不迫地往枪膛里压进一梭子弹,才拎着一卷胶皮油管推开车门。但她马上又火烫着似的缩回了驾驶室。
——她被狼牙撕裂了半截裤管,而且看清了货厢中油桶上到处趴满了狼。
刮咯刮咯。狼爪子更起劲地抓挠车门,一个尖削的狼脑袋几乎蹿进了窗口。她连忙打了一枪,再旋上了窗玻璃。
又让他说中了,她恼怒地想。虽然不可能像他说的那样严重,但她知道,自己至少要跟狼周旋到天明。食肉猛兽在光天化日之下是不敢如此猖獗的。她只需要两分钟。汲上油,主动权又是她的了。
她清点了一下子弹便更加有恃无恐。34发,只要沉着应战,这群狼简直不够她打的。听老乡说过,狼的自然群,很少有达到20头的。
“报告,”男人又恢复了懒洋洋的语调,“我要撒尿。”
她恼火地给他摘去了把手铐和横档扶手缠在一起的锁链,用一件风衣搭上铁栅子。
驾驶室被隔成两个“单间”。人下不去,吃喝拉撒睡都得在这里面了,非此不行。
男人磨磨蹭蹭坐回了原位,她又撤开栅子,替他套上锁链。他一任她摆布,没有像白天那样耍贫嘴。
然后她熄了驾驶室的灯,有意把压缩饼干啃得山响,夸张地喝水,还哼起一段塔吉克舞曲。在做着这一切时她偷眼瞄了瞄她的俘虏。
他不吃不喝,凸露的眼珠映着窗外沙地上的冷月,发出死鱼眼的白光。
他吓坏啦,她想。于是她更响亮地啃那些带咸味的硬饼干。
她睡得安然没有做噩梦。
天明时分,她醒了。狼群停止了骚扰,三三五五或躺或坐地四散着,如同一群极有教养的顾客,在耐心地等待点心店开门。
她数了数,左右各11头,前方4头,再加上打死的和车厢里的——假设那里面依然是8头的话——包围车子的狼头总数远远超过了20,还没有估计那些藏在视线之外的。这就是说,不止一群的狼对她采取了联合行动。
她没有找到昨夜的战利品。那些死狼躺过的地方,只剩下了一片棕黑色的血迹。
狼也为同类举行葬礼吗牽
太阳出来了。阳光下的狼群懒散而疲惫,却丝毫没有要离开的征兆。
她焦躁地捶了捶车门,门外的狼冲动起来。她开一线车窗,把枪稍伸出去,马上被一头狼张嘴叼住了。
她不失时机地抠了一下扳机。
那狼在空中翻了一个跟头,重重地摔在地上。几十头狼冲上去,片刻,各各舔嘴咂舌地散开,沙地上只剩下零乱的骨架。
这便是狼为同伴举行的葬礼。
这时,她才知道那些胜利品的去向。
强忍住恶心,她又射杀了一条饱餐后伸着懒腰的大狼。然后趁那帮凶恶的饕餮者争食之际,她一连两次推弹上膛。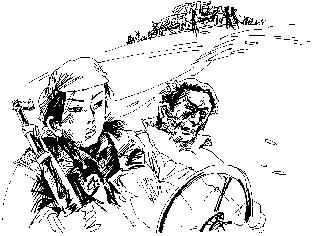
三条狼的尸体被撂在那儿。
其余的狼不敢那样张狂,但它们并不曾跑散,而是乖巧地藏到车边车底那些子弹无法击到的死角。
干嘛不趁狼惊魂未定时突围呢牽她装上新的一枚子弹,把油管放到伸手可及的地方。可是车门刚开了一线,立即有一只狼爪子伸进来。
她险些没能关上车门!
幸好那爪子在遭到车门撞击后知趣地缩回去。
她不再心存侥幸,不把这些狼杀绝,她是不可能得到给油箱汲油的两分钟的!
但这边的视野里已看不到一头狼。她打开栅子,小心地从他上面探过身去,旋开了另一片玻璃。
这5颗子弹又收拾了两条狼命,还把一个毛疏骨露的老家伙修理得只剩三条腿。老狼嗥叫着向远方逃窜,一群狼追上去,干净利索地扫除了它。
她发觉自己的胸脯紧贴在俘虏背脊上,忙向上抬了抬身子。男人忽然打起了呼噜,她知道他是装的。
吃堑长智的狼群更加隐蔽地贴近了车厢。她几乎失去了射击的机会。整个漫长的白天里,她仅仅打出了13发子弹。
至此,狼群已被消灭了三分之一。
但三分之二的狼同样足以将她困死车中。她只得寄希望于那几头死狼。
看来,这些永远饥饿的野兽是不会放弃同类的肉体的。也许,它们要待夜幕掩护才敢过去赴宴——这些世界上最有耐性的强盗!
她只有跟它们一泡到底了。
她还有足够两天的干粮和水,她就不相信,48小时内得不到那个两分钟的机会……
抱着枪,盯住朦胧天光下那石块般的狼尸,她整夜没敢合眼。她又尝试着开了几回车门。但狼比最警觉的猎狗还要机警,每一次尝试,都以她的仓惶败退而告终。
她疲劳得要命。拂晓前终于歪在一边睡着了——一只手抱着枪,另一只手捏半块饼干。
从左侧射进的阳光把她烤醒过来。
地上的死狼都不见了踪影。
“它们刚刚进完你给它们准备的早餐。”俘虏郑重其事地报告。
“干嘛不叫醒我牽”她愠怒地压下一道柳眉。
“是该为它们准备下一顿了。”他答非所问,“多准备一点,妞。我发现,它们的数量又增加了……”
她也听出外面的骚乱声异于昨日。狼群与狼群在争斗。她把门弄响,争斗立即停止,无数爪牙一齐扑向车门。
这帮畜生在对付人类时总是齐心协力的。
“你该振作些,男子汉!”她忍不住朝铁栅子那边喊。“没用啦……”他长叹一声,“前天,你放弃打响第一枪后的5分钟宁静的同时,也就放弃了最后一线生机……妞,咱们,谁也别想活着走出这片大漠啦!”
“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吗牽”
“有。当第二辆迷路的汽车也正巧来到这儿——可惜,只有千分之一的概率!”
她便不打算徒费唾沫。从工具箱中摸出一柄电工刀,她试了试刀锋,旋下三寸窗门。
一双狼爪子探了进来。
她抓住那只伸得长些的爪子,飞快地用刀锋贴上去用力旋了半圈,狼惨嚎着在同类的欢呼声中跌下去。她把切下的狼爪子扔向铁栅子的那一边。
那边没有动静。她相信男子汉被她的凶猛吓住了。
自信重又回到她的身上。当一张狼脸凑上来试图用牙齿咬碎玻璃时,她对准狼眼扎了一刀。
又是一阵狂叫和乱糟糟的撕掳,这一头受伤的狼也被它的伙伴们就地解决了。
狼便不再轻易蹿上门窗。
她关紧了窗门,把生血浓烈的腥味挡在外边。
嘎格嘎格的啃嚼声从他那边传来。她掀开一角风衣,看到他满嘴是毛和血,在咀嚼着她扔过去的狼爪子。
她又感到一阵恶心。
狼群终究没有留给她两分钟的空当。而且无论她怎样节省,也没能把最后一块干粮留到第7天早上。
饮水断得更早。
更要命的是,她只剩下5发子弹,而卡车四周的狼,粗粗算去,已不下百头。她估计至少有10群狼参与了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围猎。
也许他是对的。一开始她就不该开枪。倘不是她不断地供给死狼,那些狼什么也吃不上,说不定早就散了。
——它们简直不是在等着吃人,而是在借人类的手为它们向不幸的同类实施第一次打击,以便它们在吞食伙伴尸骨时更加名正言顺更加坦然,这些狼……
懊悔令人烦躁,但她已经躁不起来,饥渴早把她折磨得虚弱不堪。肠胃用疼痛和痉挛在向她报警,当一再警告无济于事,这些忠实的器官便进入自卫的麻木状态。
唯一的好处便是省略了在这小小空间里拉撒的麻烦和尴尬。
男人似乎比她更虚弱。嘎格声时不时响起,仿佛狼爪里有啃不尽吮不完的养分。他已经连毛带骨地啃掉了她扔过去的三只狼爪,现在又开始啃第4只。
而她只是昏睡,尽量避免体力的空耗。
当嘎格声停歇下来,车厢里便只剩下两个人粗浊的喘息。
她还不曾绝望。她知道,车队正在寻找她和她的“反帝—7343”。还有那千分之一的概率——一辆迷路的车正巧也来到这儿……
但这一丝丝希望也被第7天午间一股骤起的风沙掐断——前后车辙,连同这段废弃的、曾被狂风从沙底清扫出来的旧车道,都被尘沙覆盖,成为大漠起伏无定的波浪型雕塑天衣无缝的组成部分了。
车轮的一小半陷在沙里。现在,狼可以毫不费劲地蹿上车窗来窥视里面的猎物……
狼群的最后一支生力军是在第9天赶到的。在重新争夺地盘并竞争了盟主之后,乱糟糟的狼阵忽然变得井然有序,它们开始轮班发起冲锋,用身子撞向门窗。一个显然是狼王身份的大家伙赶走了车头上的几条母狼,坐到了正面的挡风玻璃前。挑衅地拉下一堆白如牙膏的粪便后它便肆无忌惮地打量车中猎物。那老狼烂红眼睛,口咧得可怕。它大张着嘴打了个呵欠,涎水顺下巴滴落到车窗上。卡车在撞击中震撼。跳得高些的那些狼瘦骨嶙峋的身子撞在玻璃上,窗玻璃便发出不堪重负的颤响,看上去随时有可能被撞破。
赖以保护的门窗一破,他们的生命就可以打上句号了……
她跟他互相依偎着。最后一次给他套上锁链后就没有力气再回自己的“单间”。他们就这样瘫软在一起,无可奈何地对着老狼的挑衅,相互倾听着每一下剧烈冲撞在对方心室中激发的余悸。
嘎格嘎格。他又开始啃骨头……咔地一声。她感觉到他被狼爪骨崩断了一颗牙。“妞!”他贴着她的额前乱纷纷的“刘海儿”喊。
她懒懒地扭了一下脖子让额头贴上他胡髭拉碴的左腮。
“你……起来。”他用胳膊肘顶住她的腰眼帮她坐正了。她看到他满嘴的血,还有那对黑眼仁中反映的自己的漫画造型。
“你拿着。”他用脚把一只袋拨过来——里面是半瓶水和一包干粮——最后那次分给他的一份。
“吃下去。”他命令,“咱们该作一次最后的努力了!”
她狐疑地看看他血污的嘴,没有动挪。
“吃吧。再拖延,恐怕来不及了——你必须恢复能拿动枪的力量……你还有4颗子弹。”
“5颗!”她纠正。她完全忘记在俘虏面前军火必须保密的原则。
“——还有一颗得留给我。押送一名犯人,不留一颗子弹是不行的……”
她便不再客气。下意识地挪开一段距离,她抓过干粮和水,狼吞虎咽起来。
“现在你把油管准备好,我设法将它插进油桶,你就猛汲……油开始流了,你注意我把火种扔向哪儿,就让油射到哪儿——狼群会退却的!你就抓紧那一瞬间把油引进油箱,再趁烟火掩护,发动车子……”
“你冲不出去……”
“我能!我已经把一壶机油淋在你的风衣上了,点燃它,人就随火往外蹿!”
“你以为我会替一名现行反革命打开手铐吗牽”她突然硬朗起来。
“我也知道……知道你很难改变主意,”俘虏叹息着说,“所以说……一直犹豫着。现在是最后一个时机了……”
“死了这条心吧!告诉你,我宁可跟狼决一死战——”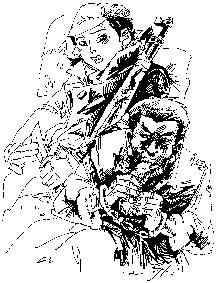
她跳起身,一膀子砸碎了那块已经出现了裂痕的门窗玻璃,用枪管把一条狼撞了个跟头;然后,她连续推弹上膛,击发——
血溅狼嗥,狼群阵脚乱了。
砰!右边车门大开,男人拥着一团火焰冲出去,“快——准备吸油!”他回身拽起一段油管。
原来,他早用牙咬着啥东西打开了手铐!
她嚯地转过身,朝火光衬托下那灰扑扑的身子打出了枪膛里最后一颗子弹。
男人惨叫一声从车门口仰面倒下;
群狼如蚁,霎时塞满了驾驶室……
风又开始狂啸。
沙尘窜天而起。日轮朦胧成一团惨白,漠然地瞠视着这远离人世的沙海中的奇景。
选自《芳草》总第17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