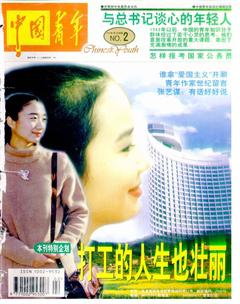与总书记谈心的年轻人
阳宗海
一本题为《与总书记谈心》的书,于不事声张之间,引起了读书界和理论界的关注。
引起人们关注的首先是这本书的作者,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一群平均年龄不超过40岁的青年知识分子,会聚了社科院各研究领域里的青年才俊,他们中的不少人近年来颇以观点的敏捷新锐而为媒介关注。正是这样一批跨世纪的青年理论工作者,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直面改革开放的重大课题,以一种集体的形式,把他们对党的政策的学习理解,对当代中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同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谈心、交心。值得关注的是,这批青年知识分子自信而又坦诚地宣告,他们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思想,信仰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们以一种积极进取的姿态,围绕着江泽民总书记《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一文,就江总书记提出的“十二大关系”,就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热点、难点和敏感问题畅所欲言。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这样的一本纯粹理论研究性的著作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正式印刷了10万册,而且至今畅销不衰,甚至出现了几个盗版的版本。这种间接体现出来的社会反应也引起了人们深深的思考。
我们这一批青年理论工作者,基本上都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走上社会的,目睹并参与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是改革开放为我们创造了成长的机会,也是改革开放使我们看到曾经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迅速腾飞的前景。我们由衷地希望为这一腾飞的早日实现贡献出自己的知识与智慧,探索出前进过程中兴利除弊的良方……
——引自《与总书记谈心》
人们注意到,会聚这批作者的,是一个叫做“中国社科院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集体。有人说这个研究中心是社科院下面一个理论特区;也有人称,这是中国理论建设最神秘的一块土地。不过在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看来,所谓“神秘”,一方面说明社会对于“中心”的功能、作用和活动不太了解;另一方面,说明近年来青年理论工作者,包括整个知识分子群与社会的联系比较少。“当实际生活提出了大量令人困惑的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当这些问题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所提供的解释有着比较明显的距离,当许多理论研究往往回避自然也就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这些年轻人说——“终于发现,我们也有一份责任”!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和青年知识分子的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始终是一致的。在采访中,参与本书写作的一位32岁的法学硕士对记者说:“中国的改革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事件,就像凤凰浴火一样,如果通过这场改革中国真的新生,那是非常壮美的。当然,如果她不能完成也是一种悲壮。在这样的一个时期,我们的责任感或者建设性需要一种从上到下的共同智慧。”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认识下,1993年,“中国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在社会科学院静悄悄的院落里出现了。
“中心”成立的当年,成功地组织了第一届“全国优秀青年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奖”。1995年7月,他们以“青年社会科学论坛”的形式,先后组织了对于“中国社会的稳定问题”、对于“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建设问题”、对于“民族和宗教问题”的几次理论研讨。读者从这些研讨的题目中完全可以看到,这些问题正是当代中国面对的十分重大但又十分敏感的问题。作为在各自学科里多有创见的一批青年理论工作者,他们聚集一堂,情笃中华,论及天下。可以说,在《与总书记谈心》一书中的许多观点,已经在这些讨论中渐趋雏形。
1995年10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若干重大关系》正式发表了,一时间,中外舆论纷纷将江总书记提出的“十二大关系”作为报道的热点,许多关心中国改革前途与命运的人们也对此作出各种各样的评说。“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学者们也敏锐地感觉到,“十二大关系”实际上是把当代中国最重大的,关系到国计民生和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都破了题。它凝聚着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于当前和今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全面而深入的思考。而这些问题正是他们近期来一直思考议论,有些往往又不得其解。现在,总书记把题目提出来了,作了令人信服的回答;同时又给理论工作者留下了广阔的研究天地。
1996年春,“青年社会科学论坛”在京郊专门就江总书记的讲话进行了整整3天的研究和讨论。大家越谈越觉得这些题目是一个尚待开发的“富矿”,在这些题目里有许多可以进行发散性思考的理论方向,深入钻研和阐发“十二大关系”,是今天青年理论工作者肩上一份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他们认为:仅仅等着领袖们去开创新理论,理论工作者只去诠释领袖思想的时代已经过去。领袖们的理论来自千百万群众的实践以及理论工作者创造性的理论思考,让更多的人来选择,让更多的人来讨论,正是这个包容性强的时代的特点,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的特点。领袖人物的著作更多的是行动的指南,至于社会各个领域千头万绪、复杂多变的诸多具体理论与实践问题,越来越需要各学科理论工作者在领袖思想的指导下,独立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
于是,青年学者们结合自己研究的学科领域,围绕江总书记提出的“十二大关系”进行了使人感到“耳目为之一新”的热烈的研究和讨论。在这场饱含报国之心的讨论中,一种渴望油然而升——与总书记谈谈心。
既然是与江泽民总书记谈心里话,我们就一定要采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把我们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在如何促使中国腾飞的具体思路上。
——引自《与总书记谈心》
这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理论研究著作,是一批青年学者智慧的结晶。参与写作的青年学者们说,这不是一部个人观点的“集合”,而是各学科思想和理论碰撞之后的“化合物”,我们是独立思考的,我们写的是自己心里的东西。
一位参与写作的经济学博士告诉记者:“我的思想转变是从90年代以后开始的。以前我对现实也总是持批评态度,对改革的进程迟缓不满,也对其他事情的处理失当不满。现在想来,就青年知识分子的主体而言,那可能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一个有着各种各样想法的阶段。”“我们的国家已经走过了最艰难的阶段,再坏也坏不到1978年刚开始改革的时候,也不会像1988年那样,那时供求关系非常复杂,人们思想也不安定。以后,到90年代,对于出现的经济过热控制得非常好,我们对国家的前景充满了信心。”“但是”——他说——“知识分子是尊重科学的,从尊重科学的意义上,我们不是为了依附于什么,而是看到,理论上‘十二大关系的提出,是有着科学依据,是符合时代和人民心愿的。”
另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博士说:“我在1989年曾经一度深感迷茫和痛苦,当时是怀着一种激情,觉得中国不改不行。这些年过去了,现在我参与写这本书,这也是一种表达。我知道,中国的改革不能走回头路,也决不能出现大的社会动荡。中国只要继续稳定,发展就会很快。所以在这本书里,我放弃了个人一些比较激进的观点。”
“1989年以后,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经过了若干灵魂的拷问”——一位研究比较政治的法学硕士说,“这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责任感还要伴随着一种建设性。”
“包括我们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如果提出批评性意见,很容易引起轰动。要说‘自由‘民主‘市场好像也很‘前卫,学术地位也高。许多西方人就是这样看的。”“但现在我觉得‘轰动的并不一定是好的,关键是看对中国是否有用。比如国企改革,公有制的路子是对的,尽管现在仍有困难,但任何一个厂长都在为能否打开市场而发愁,这比过去亏损也照发工资进步得多”刚刚接受过一位外国记者采访的博士说,“他老是问:中国经济会不会发生崩溃?会不会发生政治上的动乱?我告诉他:我们国家已经走过了最艰难的时候,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盼望走向繁荣,充满信心地去打厚实基础的时代。中国不会出现你们想像或盼望的事。”
在《与总书记谈心》这本书中,青年学者们的“心里话”溢于纸上,在与他们交谈的过程中,这种真诚也溢于言表。
他们说,一切关注中国前途的人们,不管其真实愿望如何,都看准了未来15——20年是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兴衰成败最为关键的历史时刻。我们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对改革是充满信心的。作为青年理论工作者,我们所做的,是循着领袖提出的思路,为读者乃至为民族建立信心寻找一个理论上的链条,同时在写作的形式上直指人心,所以书中表现出来的文字是明亮的。我们就是要让读者也让青年们认识到,中国现在就是要强大,中国人就是要抱成团,让我们国家发展上去!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在实践马克思主义,更应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只坚持马克思主义字句的人,不一定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守成者,完全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断送者。只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从胜利走向胜利,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引自《与总书记谈心》
对国家民族发展的责任和信心,对党的领袖和对读者的真诚,是《与总书记谈心》这本书中自始至终充溢着的一种激情。这种信心与真诚从根本上,来自一种理论上的坚定。或许正是当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公开宣扬的这种理念,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特殊关注。
他们在书中说:“我们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希望早日看到,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领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取得彻底的胜利,使我们可爱的祖国在21世纪成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青年学者们告诉记者,宣称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是我们经过思考,经过对世界历史和现实的对比和研究得出的。我们认为社会主义运动会以一种新的形式在世界上重新走向高潮。但这个高潮不一定是以过去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取得短期的轰动。“中国的社会主义红旗和阵地还能坚持多久?中国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吗?社会主义道路到底怎么走?”“一切有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的人们都应严肃自问和思考:我们怎么办?”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二大关系”的报告中提出:“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一条根本原则,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在写作《与总书记谈心》的过程中,青年学者们对这一根本问题进行了反复的极为认真的研讨。在“公有制:最有争议的问题”一章中,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思考的轨迹——且看这一章内的标题:“为什么人们会对公有制产生疑问”“问题的根源:公有制等于国有制,国有制一定只有一个模式”“人类走向:私有化还是公有化”“公有制到底好在哪里”“连西方都在搞公有制”“股份制——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好形式”“跨国公司——世界大同的经济基础”“再过10年,‘中国是否以公有制为主将不再成为问题”。
基于这样一种理论上的坚定和信仰,青年学者们系统地就总书记提出的一层又一层的关系阐发了自己的思考。这些思考不单是长远的展望和预测,而且就具体的建设性和操作性问题,提出了他们中肯的意见。他们说:“限于水平,我们完全有可能说错话,我们所谈的可能浅薄,可能片面,可能偏激,但我们的态度是真诚的,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坚定的。”
在中国开拓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业,无疑需要恢弘的勇气,但面对90年代纷纭复杂的国内国际局面,面对21世纪未卜的种种变数和前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大厦”还需要非凡的智慧和艰苦的劳动。
——引自《与总书记谈心》
“我们并不是要作‘意见领袖。”——当有人问及这些青年学者:他们是否认为自己的追求代表了当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主流时,“青年社科中心”的一位负责人回答说:“我们的责任是有的放矢,把自己的探索化为整个民族探索中的一个过程和一个部分。”
几位青年学者都告诉记者,讨论和写作的过程也是他们提高和深化自己认识的过程,有些人放弃了自己的观点,更多的人通过讨论丰富了对于江总书记讲话和对中国国情的认识。针对有人认为,这本书代表了变化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保守主义”倾向的说法,他们认为,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底蕴不会变,是中国的形势在变化。过去你想的说的,事实上做不到,于是就会发生冲突。但现在我们想要表达的,在这本书里都说出来了。还有一位著名的青年经济学家对记者说,经济学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就是尊重传统。发扬现有制度的优势有许多工作要做,关键是怎么做。如果不可能推倒了重来,那么尊重传统发挥现有体制的优势,趋利避害,可能是更具挑战性的改革。
可以想见的是,在“与总书记谈心”以后,“中国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年轻人们还在继续他们的思考和探索。去年,在《与总书记谈心》一书付梓之后,他们的另一部研究成果《1996——1997中国发展状况与趋势》已经出版。今年,他们还准备就“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制度建设问题”及“中国海外智力资源”等问题进行专题讨论。
读者或许关心“中国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青年学者们都是些什么人,下面这些就是他们中的一部分——
翁杰明(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法学硕士)
张西明(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秘书长、法学硕士)
张(tao)(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学硕士)
曲克敏(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军(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
许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助理、文学博士)
邢广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助理、法学博士)
陈东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经济学博士)
陆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
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经济学博士)
范建荣(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哲学博士)
金碚(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博士)
郭克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袁钢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欠发达地区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博士)
韩俊(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博士)
蔡(fang)(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博士)
刘靖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法学硕士)
何星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
李长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史学博士)
闵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法学硕士)
金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哲学硕士)
赵睿(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经济学硕士)4 (责任编辑:邱四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