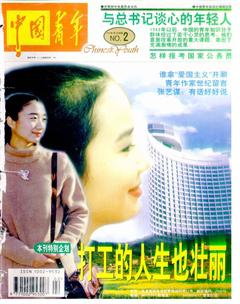青年作家世纪留言
江业成
关于新时期文学,10年以前,王蒙先生就说过:“有时候我感觉,这10年似乎是把——例如欧洲的——100多年的文学史压缩在我们新时期10年的短小阶段里。”当下个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人们自然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看重中国新文学的前景。作为跨世纪的青年作家,他们的文学观念自然也将直接影响中国的走向。借作协大会在京开幕之机,记者特意就几个共同的问题,走访了几个当前炙手可热的青年作家。
时间:1996年12月16日一20日
受访人:洪峰(1957年出生,吉林,男,本名赵洪峰,著有《东八时区》《瀚海》等)
王朔(1958年出生,北京,男,著有《顽主》《谁比谁傻多少》等)
残雪(1953年出生,湖南,女,本名邓小华,著有《黄泥街》《突围表演》等)
何顿(1958年出生,湖南,男,本名何斌,著有《我们像葵花》《荒原上的阳光》等)
徐坤(1965年出生,沈阳,女,著有《先锋》《狗日的足球》等)
李晓(1950年出生,四川,男,本名李小棠,著有《继续操练》《四十而立》等)
王安忆(1954年出生,南京,女,著有《小鲍庄》《叔叔的故事》等)
采访人:赵为民
你完成了哪一部作品之后,觉得自己是一个作家而不是一个作者了
徐坤:当我提起笔来创作的时候,就已经是带着作家的沉重感和使命感了。目前整个创作还没来得及分期,现在还在一个水平线上发展。
洪峰:我想不出中国现有的作家中有哪一个有胆量说哪部作品之后,自己就是一个作家了。我自己是在1986年写《奔丧》和《瀚海》时自我感觉好,但是很快就觉得不怎么样了。现在越来越发现不知道小说该怎么写了。每一个成功的作家一方面提供了经验,另一方面又设置了巨大障碍,要超越过去很难了,一个最微小的变化也是革命性的。
李晓:我是业余作者,不过从一开始就有我满意的作品,比如《继续操练》。
何顿:我是从能在《收获》杂志发表我的作品后,才觉得自己是一个写得比较好的小说家,从此可以靠写作靠我最喜欢干的事情来生活了。当时还在干装修,《上海文学》又跟我约稿,我就把一个将近60万元钱的工程扔掉了。
残雪:第一部作品——1985年写的《黄泥街》。
王朔:这种感觉是从1991年写完《我是你爸爸》才有的。我一直认为“作家”是个骂人的词儿,只有不要脸的人才敢称自己是一个作家,而且还侃侃地说一个作家应该如何如何,现在看有人这样写,我还起鸡皮疙瘩。也可能是我把作家看得太神圣了。我现在也不太认同自己是那种意义上的作家。
王安忆:我好像一直没有这种转换的概念,我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写作的人而已。而且现在越写越累了,要使自己满意,越来越不容易了。
你是否在乎你的读者是多是少
徐坤:在乎。否则我就写日记给自己看了,就不写小说了。
洪峰:没想过。我希望读者能读懂,但写的时候一想它,写作就会受到局限。
李晓:我希望读者多些,但没法在意。
何顿:现在不是很在乎了。出版商印一万册还是两万册,我觉得都差不多。我想读者如果认认真真去看,看得懂应该是没问题的。
残雪:很在乎!不是在乎读者是否看得懂,而是在乎读者群,越多越好。而且我尽量地做一些工作,让他们能够进来。但绝对不降低自己的水准和层次。写小说时不考虑这些,只是在小说之外做些工作。比如有人来问我,或者是对我的小说感兴趣的时候,我就尽量地跟他解释。另外自己也尽量地跟人谈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尽量地把自己的门打开,就看他是不是有勇气进来。我对大学生期望很大,高校里有一些人将来会是我的读者。每一个年轻人,只要是有诚意的,或者是爱好文学的人,都有可能读懂我的小说。我的小说不是让人们用语言能够表达出来的,只要他能从中看到个人,看到某种感受就可以了。现在也许没有看到,但是将来有一天,他读到的东西会起作用的,会让他看到他自己。
王朔:我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乎的。因为读者的多少决定着你的社会影响,甚至直接决定着你的经济效益。另外,我又是不在乎的,因为如果有一百个读者买你的书,就会有一百个动机,您要是挨个儿尊重他的话,那您也就完了。所以,在统计数字上我在乎我的读者多少,但在具体的接触上我不能在乎——你不能把什么话都当补药吃,那样能把你补大发了。
王安忆:我当然希望有很多人来看我的书,但我希望我的读者是质量高的人,可这又没法左右。我想我的作品也就是学生喜欢看。
你觉得获奖对文学创作是否有很大意义,有没有你最希望得到的奖
徐坤:获奖能进一步调动我的创作情绪,奖金同时也能改善一下生活。得哪个奖都不错。
洪峰:坏处极大!我是指国内的获奖。它引导作家越来越离文学本身远了,我非常憎恨它。我经常获奖,但国内的奖没有什么我看重的,国外的奖又不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能得的。我尊重诺贝尔文学奖,虽然我们的一些作家对它不屑一顾,但我不这样。因为它毕竟囊括了世界上绝大部分最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我们得不到,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和这个星球上更主流的东西一致,并不是什么翻译问题、政治问题。看看我们的作品,那里缺什么,其实哪一个作家都应该知道。
李晓:应该有意义,比如它可以树立自信,尤其是对比较新的人来说。
何顿:如果能获得国外的奖,刺激会大一些。但是在国内,我看到好多获奖作品,写改革的,写伤痕的……现在根本就没人去读它。获奖当时能刺激一下,然后就会成为自大狂,然后就不再写了,有很多这样的人,现在都很平庸。我从来就不去看奖,人一看奖就想不开了。如果茅盾文学奖给我一万块钱,我就把钱拿回来,抽几包好烟,比较潇洒地过上半年。
残雪:我觉得没什么意思,我不关心。能有奖给我,我也会挺喜欢的。有奖、有钱,说明你的读者对你的作品的一种肯定。但是我的作品大概还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我也就不去考虑。国内的这些奖,我不怎么感兴趣。
王朔:那必须得是公正的、权威的和确实令人信服的奖,一些势利小人会为这些奖打得不可开交,一般的人不会在乎这些奖。而世界性的、国际性的奖似乎只有诺贝尔奖。我觉得大家也都别说酸溜溜的话,这个奖谁得了,对谁都是非常重要的事儿。一个是他的地位可以一举奠定,另外,那一百万美金也确实不是一个小数。但是,您说我这一辈子就冲这个奖去了,得不到,我就一头磕死,那你也是活该了。但凡有一个中国人得到了这个奖,中国人这么好大喜功,到时还不定怎么臭美呢。
王安忆:我得的没有什么重要的奖。获奖当然令人高兴了,谁也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没有反应。但是,它又不能左右我的写作,我都是自己来决定写得好还是不好。比较看重的,诺贝尔?太高了,也就不想了。国内的奖,像茅盾文学奖,我不是很想,因为我知道国内评奖很复杂,我也不是他们所希望的那类作家。
在你成长为一个作家的过程中,是中国作家对你的影响大,还是外国作家对你的影响大
徐坤:少年时期只能读到国内作家的作品,青年时期“恶补”外国作家作品。
洪峰:全方位。我最小的时候读到的是中国老一代作家的作品,那时候没有别的,我不知道它在我心目中是何时坍塌的。1977年考上大学后读西方作品,读得凶极了。但是,我把人类看成一个整体,艺术是一种共同的语言,和用什么声音用什么音节去表达没有区别。我看书也不管它是用何种语言来写的,我只关心它讲了什么事情。
李晓:都有。比较起来更喜欢外国的。
何顿:我对文学感兴趣是从中国作品开始的,包括古典的,像《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红楼梦》。后来觉得不过瘾,又迷上了外国作品。现在又回头来看中国作家的作品了,是因为要比较,要了解行情,别人写过的我就不再写了。
残雪:中国作家中是鲁迅对我的影响最大,古典的喜欢《红楼梦》,外国作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卡夫卡。
王朔:我现在静下来想,还是外国作家对我的影响大。越是靠近我们这个时代的,对我的影响越大。俄国文学是我非常反感的,我认为他们是现代小说的反动,如果你要知道小说不能写成什么样,你就去看俄国文学。19世纪文学我认为已经一无可取了。可惜的是中国优秀作家很多,优秀作品不太多。比如优秀作家鲁迅同志,你说不上他的哪部作品影响你了,倒是鲁迅先生为人的态度狠叨叨的劲儿影响你了。这有点儿像蔡国庆,说是一著名歌星吧,哪支歌儿他唱红的?中国作品真正对我有影响的也就是《红楼梦》,它能把普通的人和事儿还原,写得栩栩如生。你可以不那么写小说,但你可以看到消失了的生活,通过文字得到生动、清晰的再现。像这样老老实实叙述的,在中国还不多,除了巴金先生比较笨地学习过,也是那么有文必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么写,但也没有了生动。
王安忆:小说这东西实际上还是外来的,虽然我们很强调我们中国有小说的传统,实际上我们所接受的仍然是五四时期带来的西方的民主、科学。
老一代作家普遍认为“作家应该对人生负有一种责任”,你怎么看
徐坤:青年作家的责任感应该比他们还要重,面向未来。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作品告诉大家,要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
洪峰:写作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东西,和别人没有什么干系。
何顿:真正的好作品,一个是靠题材,一个是靠“神来之笔”。“历史使命感”在心里有一点也可以,但不要给自己更多的压力,压制自己的写作。如果非要给人家指明方向,那让人家看教科书好了。现代人都活得很累,受的教育又很多。我不喜欢去指导别人怎么做或怎么活,那是中学老师应该干的事。
残雪:这个问题应该分开一下。我在创作的时候不考虑这些问题,不可能考虑。因为我的创作完全是一种个人的、封闭的写作,即兴地让自己的灵魂裸露出来。但每一个人不管他怎样封闭,他总还是一个社会的人,不可能完全脱离这个社会。所以责任感我也有,但是和老一辈当然是不同的了。我是通过作品,而不是直接讲出来的。有一个寓言,说一个人种树,只知道一棵一棵地种,根本没去关心其他的事情。他就是喜欢种树,种了好多树,过了好多年以后,那些树长成了森林。那森林不就是对别人有益了吗!
王朔:我觉得作家和普通人一样,比较脆弱,比较有限。他们没有超自然的能力。但在中国吗,言说者往往被赋予特别重要的意义,只要您敢当着人说话,您就得说出点儿让我们奔高枝儿的话。我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追寻真理追寻得太苦了。
王安忆:责任感的问题我同意,但我觉得责任感不是那么短期的,也不是那么具体的,不是今天晚上出现了什么政策,我就去歌颂它一下。从大的方面讲应该有,没有的话,一个作家的等级是要降低的。
你是否会拿出很大精力去涉足影视行业
徐坤:实在缺钱花的时候,还是要去触下电的。但我写的时候,绝对不会迁就影视要求,还是会按文学自身的规律、审美的规律进行创作。
洪峰: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去涉足。但不敢保证以后,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面对贫穷。我希望一直写小说。从语言角度来讲,写影视会把小说家的叙述感觉破坏得很彻底。但是,你也不必为此替文学操心,总会有人干。
李晓:我曾经写过几个乱七八糟的娱乐片。但在文学和影视中,我会更侧重前者。
何顿:肯定不会。上次杜宪让我自己改编我的《我们像葵花》,我听了一笑,任何心都没有动。将来不写小说的时候,会去玩电影,去抓钱,但是我现在还能写小说。文学是我梦想了十几年的东西,一个人把思考了10年、追求了10年的东西任意地丢掉,那这个人不是我们湖南人说的有点蠢气、有点宝气吗?而且我实在不愿意受导演的摆布和蹂躏,太痛苦。
残雪:从来没想过,绝对不会。现在还没有哪个导演能配得上导我的作品。假如有那样的人,我当然喜欢喽。但绝对不会拿文学去迁就影视。如果有配得上我作品的导演,我会跟他合作。现在这些人我觉得太低了。
王朔:我已经拿出很大精力涉足影视了。我现在只能是收拾残存的精力,看看该干嘛。我现在不是路路通,哪条路通,我就朝哪条路走了。哪条路都不通,我就原地坐下来,写一点文字性的东西吧。
王安忆:我的《流逝》被拍过电影。总的讲,我的作品好像很难拍成电影。我绝对不会把文学向影视上去靠。在我心目中,和电影比较,小说还是要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