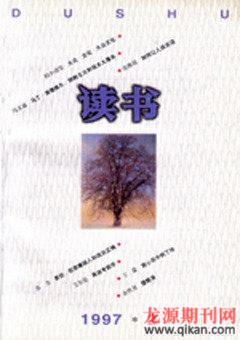罪犯、犯罪嫌疑人和政治正确
苏 力
《刑事诉讼法》修改重新颁布之后,法学界一片欢呼: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在这一点上终于与“世界”接了“轨”,是中国法治的一个重大发展。的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对刑事被告的权利保护的有关规定上有重大发展。但是,这些权利在文字上的规定并不必定保证其在实践上的实现;即使得以实现,也会引出随之而来的其他一些深刻问题,因此未必能得到公共选择的最后认可;甚至发展也并不意味着一定正确,因为任何法律从根本上都是顺应所在社会的需要,而不是必定迈向某个确定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发展也许只是一轮新试错的开始。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加注意,正剧也完全会演出喜剧或悲剧来。
这些宏论有点漫无边际,但也是有感而发,这就是被法学家认为是正确的称呼的“犯罪嫌疑人”。
据一些法律学者说,新刑诉法实际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其中要素之一就是一个刑事被告在被法庭判决有罪之前,任何人不得认为他(或她)有罪。据说,这是对刑事被告权利的重大保护。因此,在今年以来有关“严打”的电视和广播新闻中频繁出现的是“犯罪嫌疑人”这个词。警方抓获的不是“罪犯”,而是“犯罪嫌疑人”,哪怕这个人是一个越狱后潜逃作案的人。据说这严格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法治原则,是社会走向法治的重要一步,一切以法律为准绳。
可是,让我们假定这样一种情况:一个人入室行窃,让群众或给警察抓到了。而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不能说当场抓到了“罪犯”,而只能说群众(或警察)当场抓到“犯罪嫌疑人”?这会不会使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犯迷糊:既然是当场,为什么不抓获罪犯而去抓一些嫌疑人呢?警察在依法搜查一个有明显重大贪污嫌疑的人的住宅,面对着大量的黄金美元,他们搜查的不是“罪犯”的犯罪证据,而仅仅是“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证据?而据许多法学家的忠告,即使我们普通百姓或记者也不应当或不能说“罪犯”,而只应当说“犯罪嫌疑人”,否则,我们就是缺少现代法治观念,就是一个社会的法治不健全的表现,甚至是违法的。
也许这些法学家的解说是对的。可这话,怎么说起来这么别扭,而听起来也这么别扭;我怎么总有点“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感觉呢?直觉告诉我,这可能出了什么问题——尽管直觉并不总是可靠的。
其实无罪推定仅仅是一个司法的原则。法学界一般认为,最早明确表述无罪推定思想的是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他在一七六四年所著的《论犯罪和刑罚》一书中提出:“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中译本,页40)可问题是:不能被谁称为罪犯?从上下文来看,只能理解为法律不能称其为罪犯,或不能称其为法律意义上的罪犯,但不可能是禁止公众在其他意义上称其为罪犯。并且,贝卡利亚是在谈到废除刑讯时提出这一主张的。因为他要讨论的是法律意义上的“罪”与“罚”,而他认为这两者应当、而且可以紧密相联、相互对应的;有罪才可以惩罚,无罪则不能惩罚,由于刑讯是由司法机关对尚未被判有罪的刑事被告施加的惩罚,而这些被告完全可能是无辜的,或者可能刑讯的严厉程度超过了被告应受的法定惩罚,因此,贝卡利亚为废除刑讯而认为,在法庭判决之前,不能认定被告有罪。从今天看来,无罪推定是贝卡利亚用来支持他废除刑讯的一种逻辑的正当化方式、一种理论设计。他关注的是对无辜者和罪刑不相适应者的正当权利的保护(贝卡利亚也是最早从理论上提出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家,因此必须将无罪推定原则同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其理论体系的构成部分,而不应仅仅作为分离的主张)。尽管无罪推定原则此后又有所发展,特别是对司法程序中的举证责任规则有重大影响,产生了许多在我们看来是积极的作用。但其核心始终并不是一个称呼,也不可能禁止其他非司法人员在其他意义上称某个刑事被告为罪犯。因此,这一原则只是一个司法原则,而不是也不能成为一个泛化的、用来指导人们如何称呼认识刑事被告的规定。
而且坦白地说,我也不相信,有哪个社会的人们能接受这样一个脱离了司法语境而泛化了的原则。一个被强奸的妇女——假定她是一位坚决主张无罪推定且又有高度法治意识的法学家、律师或法官,在法庭判决之前,不能认为或说那位强奸者是罪犯?她丈夫——假定也是这样一位学者,仅仅认为那位强奸者是一个犯罪嫌疑人?而且否则,她/他们倒违了法?如果法律是这样的话,或者法律应当作这种解释的话,那么这种违背天理人情的法律或法律解释也必定是一个错误。我相信,在她/他们和其他一些相信她/他们的人的眼中,这个强奸者就是罪犯;警官和检察官在提起诉讼时也一定要认定这个强奸者就是罪犯(否则他为什么要对这个人提出诉讼呢?)。无罪推定原则的意义只在于要求检察官和警官,特别主要是法官和他所代表的国家司法机关在判案时不能先入为主地认定被告就是罪犯,而要以证据来证明被告是否罪犯,更不能刑讯逼供。而任何有意义的原则一旦被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会是一派胡言乱语了。
除了功利的原因之外,贝卡利亚之所以以无罪推定原则提出刑事被告的权利保护问题还由于西方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关于语言的哲学观。而后人之所以这样理解贝卡利亚,除了贝氏废除刑讯的理想一直未能实现、因此贝氏的话语一直被当作权威性正当化理由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这种西方语言观的绵延至今。这就是为后期维特根斯坦所摧毁的语言图像论。按照这种理论,语言是世界的真实图画,一个真实的物体只对应着一个绝对正确的语词,一个命题只对应着真实物体之间的关系,并因此可能有一套正确的语言。因此,在刑事法律上,罪犯就是法律判决后的那个人,判决前的那个人只是犯罪嫌疑人;真正的刑罚是国家对罪犯的惩罚,而对犯罪嫌疑人的惩罚由于不合法,因此不是真正的刑罚。世界上只有一套正确或精确的语言,因此为避免思想的迷失和误解,人们应当按照这套语言来说话。接受了这种哲学思维的人们(常常是一些学者,而不是那些缺少哲学指导的平民百姓)就很容易相信,使用了精确的、正确的语词就可以改变人们的行为。在此,我不想批判这种图像理论,因为自维特根斯坦、索绪尔以来,这种理论早已是无法成立了。我只想指出,如果严格按照这种理论,恐怕“犯罪嫌疑人”的名称仍然成问题:我们固然可以称这个被告为嫌疑人,但是在法庭判决这个行为为“犯罪”之前,我们恐怕也不能认定该行为是犯罪,而只是称之为“可能的犯罪”:因此,也许我们应当“更正确地”称犯罪嫌疑人为“可能的犯罪之嫌疑人”。用北京人的话来说,你累不累呀?不要以为我这仅仅是在抬杠、调侃、反讽或其他,事实是我们目前的法学研究很多就属于这样的概念游戏。我所舞的剑自然也就“在乎山水之间焉”。
其实一个语词,作为一个概念来使用时,重要的是对它的内涵的界定和使用范围的限定,而不在于它是否真实对应了现实。因为语词与其所指称的物从来不可能是对立的,其间的关系是一种专断的、临时性的关系。因此同一个语词在不同场合完全可能有不同的含义和功用,即使一些法律语词也不例外,更何况这些语词并不为法律所专有。社会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就和法律意义上的犯罪概念不同。毛泽东同志说过,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由于隐含的语境限定,我想没有一个思维正常的人会认为这是在制订一个刑法条文,抑或对某些行为作出司法判决。我们现实中的每个常人都熟悉各种语词的语境限制,能理解语词含义,并能在社会生活中自如、恰当地运用语词。请想一想孩子看到电影中的汉奸时说“他是个坏蛋”和一对恋人之间说“你是个坏蛋”时,“坏蛋”这个词以及“蛋”的含义和用法。
正是基于这一分析,至少我认为,普通百姓、新闻工作者、甚或是政府官员和法律工作者——只要他不是以公职身份代表政府或法院就某案说话(或者不会给人以这样的错觉)或在法律的专业场合——没有任何理由必须按照司法术语来严格区分罪犯和犯罪嫌疑人,他完全可以凭着自己的直觉、感情、思考、判断甚至便利而自由地使用他所愿意使用的任何一个语词。
当然,作出这一判断,我还有其他理由,甚至是更重要的理由。
八十年代中期,我去美国留学,作为外来者,我很快感到美国社会中有种种政治性的语言禁忌。例如,说话或写作中指称不特定的第三者时,应当甚至必须用“他/她”,而不能仅仅用“他”;后来,又有不少人主张,指称美国黑人时,应当使用“非洲裔美国人”;又说过去的历史(history)只是男人眼光中的历史即所谓“他史”,而要写出女人眼光中的历史即“她史”(herstory);又说称呼同性恋家庭应当是“单性家庭”。诸如此类,不胜繁多。而如果谁不这样说或写,他就是或者是在强化男权主义、白人中心主义等各种主义,就是在歧视妇女、少数民族、同性恋或其他什么人,并且也是在强化现有的歧视文化,一句话,就是政治上不正确。这种被称之为“政治正确”的社会实践在美国如今相当普遍,特别是在知识圈内已经形成了一种相当大的社会压力。在这种压力下,甚至某些学术问题也变成了学术禁区,不能进行正常的研究,例如不同种族的比较研究。
当年,我对此不仅感到新奇,而且也觉得这些政治正确似乎言之成理,尽管有时觉得有些别扭。但如果真的因此就能够促进社会平等和公正,我想,也许应当坚持政治正确。然而问题在于,情况并不如同政治正确者所相信的那样:语词和现实完全对应,大家都换一个词就能改变和创造一种社会现实。时间一久,我就发现这种政治正确不但效果很低——如果还曾有效的话,更重要的是它使我有一种“文革感”:如果不加限制,我认为很可能导致一种专制,一种语言和思想的暴政。
我在这里并不是要否认不同语词的运用对人们的行为确有影响,因此在可能情况下我们必须澄清语词概念的含义,显现其隐含义及与其相伴的社会行动逻辑。但由于语词与现实没有对应关系,因此任何语词都有局限。据此,我认为重要的在于理解具体语词的局限,而不在于发现“正确的”语词。仅仅是“正确的”语词甚至法律规定并不可能改变社会实践。就以“无罪推定”为例,法国大革命后的《人权宣言》中最早从法律上规定了这一原则,而事实是,大革命的革命法庭把许多无辜的人,或者是没有死罪的人推上了断头台,其中包括许多大革命的领袖人物。如果读过狄更斯小说《双城记》或看过这部电影的人,谁能不为那位同情法国大革命和平民的贵族的被判死刑场景而震撼呢?无罪推定的原则和犯罪嫌疑人的名称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拯救他,因为在当时革命洪流中,只是出生于贵族之家这一点就足以构成令当时的人们相信是充分的犯罪证据了。
我也不想否认语词可以有禁忌。任何社会实际上都有一些语言的禁忌,例如,我们在许多场合会说一些父辈长者“去世了”,而不会说“死了”或“新陈代谢了”(但这还是分场合的)。因此,从社会功能上看某些语言的禁忌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须的。然而,这类语言禁忌毕竟还是社会的,是社会习惯形成的,在一定意义上是人们通过多向交流(当然这种交流中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权势的因素)而自愿接受的,因此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契约的产物。而美国的那种政治正确,至少其中某些是少数人按照他们认为的正确观点创造出来的,并试图通过某种社会压力来单向度地强加于他人,不容你讨价还价。正是由于这一点,我感到那种咄咄逼人的、高人一等的政治正确中有一种可怕的优越感,构成了一种对个人自主性的威胁。它试图要人们统一按照一种据说是正确的思想去想问题,去说话,而不能按照每个人自己的感觉、思考和方便来说话。经过文革教训的、学习法律的我,自然不可能接受这种政治正确,更不希望在我们的法学中出现这种政治正确。
想不到的是,如今我们的许多法学家在中国居然也搞起这种实际上是政治正确的把戏来了。尽管是端倪初露,但要警惕的是这种政治正确是在加强法制建设或普法的名义下(因此具有极大合法性,同时又借助了强大的国家权力)进行的,积极推动和倡导这一中国式的政治正确的更多是中国的法学家,并且据说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包括刑事被告的)权利。这不能不引人警惕和深思。
为什么中国也会搞这一套?此刻回顾起来,其实中国历史上类似这种政治正确的东西也曾不少,例如文革中用的“请”而不能是“买”主席像之类。尽管这种事件随着一个特殊时期的过去已成为当今人们的笑话,但支撑这种话语并使之可能的语式(discourse,福柯的术语)在任何社会一直都存在,我们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这一语式的接受者、传递者,甚至可能成为强化者。因此,一旦时机成熟,这种语式就会从另一些渠道以另一些方式流露出来,弥散开来。而且,由于这种语式是同新的、合法化的、流行的、似乎是天经地义、无可辩驳的题目(例如现代化、启蒙、法治、民主、科学、权利)相结合而获得一种正当性,以致于难以为话语中的人们所察觉而令人窒息。
这一现象还表明,当代中国社会“知识”领域内的许多值得中国学者认真反思的问题,而且并不仅仅限于法学界。许多学者总是习惯把语境化的概念、命题、论断和实践一般化、普适化;总是认定所谓的历史的必然和真理,认定真理和谬误的截然对立;总是抱着自己的专业知识而忽视日常生活中的常识,认为需要对民众启蒙;拒绝对日常生活中细小琐碎问题的深思和反思。而一旦有可能,为了建立和保证被他或他们认定为真理的那些知识的权威和学科集团的利益,就会并非清醒地然而却是主动地同某种权力结合起来,不断扩张,硬要把他们的那一部分专门知识强加给整个社会,甚至忘记了它本来的追求。这种做法即使出于善良的动机,即使会带来某些可欲的结果时,也可能带来某些不可欲的、甚至危险的后果——“不经意处是风波”!
顺便说一句,贝氏《论犯罪和刑罚》中译本中有多处译作“罪犯”的地方(例如,仅第20页就有四处),在我所见到的英译本中均译作“被控者”(the accused)。由于中译者是直接依据意大利文本翻译的,并——据译者的译后记——经余叔通教授对照英、法、日等译本对全书进行了认真的审阅,而本文作者不懂意文,无法核对原文,因此不敢妄加猜测其翻译的对错。但如果贝氏真是如同今天法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严格界定罪犯为经法律判决有罪的人(我倾向于持这种观点),并一贯严格使用罪犯的概念,那么这些翻译就法律专业上看是不能迁就的、会误导中文读者的错译。
指出这一点,与本文的中心论点并无矛盾,相反是对我的观点的强调和补证。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日于北大蔚秀园
(《论犯罪与刑罚》,[意]贝卡利亚著,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3.9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