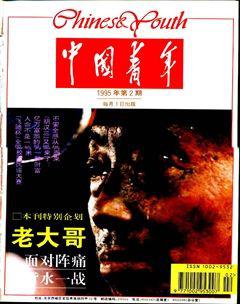不安全感从何而来
“我心里空得慌,对明天没把握”。这是本刊上一期《我为什么心里没底?》一文中诸多被采访者的共同感受。细读孙立平先生这篇《不安全感从何而来》,你将从一个社会学家的独到见解中不难知道,“心里没底”的“底”究竟在哪里。
一、不安全:一种普遍而微妙的感觉
近些年来,很多人感到一种越来越强烈的不安全感。这里所说的不安全感,主要还不是指由于社会治安的恶化而带来的那种不安全感,而是指一种很微妙的、朦胧而模糊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不安全感是以前程未卜、隐约的担忧、没有保障等感觉联系在一起的,但这种感觉又不是这种不安全感的全部。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感觉是发生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15个年头的今天。在这15年里,尽管也存在很多问题,出现了许多矛盾,但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我国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造就了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却出现了这种普遍的不安全感。这其中有一些很具体的原因,比如一些个人的生活出现困难,一些经营不好的企业、特别是国营企业的职工为自己的前途担忧等。但有这种不安全感的,并非仅是这一部分人,即使是没遇到这些具体问题的人,也照样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
二、难以把握未来:不只是个人能力问题
我认为,这种不安全感首先来自制度安排的不稳定性和不明确性。安全感的一个重要来源在于人们能够把握自己行动的结果,在于个人对用自己的行动解决可能遇到的问题的信心。而前题就是个人协调自己的行动与目标以及自己的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关系的能力。
那么,个人的这种能力是如何形成的呢?也许有人认为这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其实并非仅仅如此。人类的所有社会性活动都是在社会的环境下进行的,因此,人类活动的实际结果,往往并不取决于自己的能力和努力的程度,而是与活动发生在其中的社会环境有关。更具体地说,人们把握自己行动的结果,协调行动与目标的关系,必须以社会中有关的制度安排为前提条件。制度安排的作用在于,为个体行动者提供稳定的、可以预测的环境。有效的制度安排必须具备两个最基本的特征。第一,它必须是相对稳定的,不会发生频繁的、根本性的变化。第二,它必须是明确的,能够为行动者所预测。正是依据这种稳定而明确的制度安排,人们才可以对自己的行为结果作出较为明确的预测,从而制定自己的行动策略。这是人们的安全感得以形成的基础。
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社会中的制度安排已经很难起到这样的作用。目前的我国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一些原有的制度安排由于不再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生活而在瓦解或成为改革的对象,而新的制度安排又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个体行动者就很难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预期。比如说,企业制度在进行改革,但这种改革对个人
的就业和收入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人们并不是很清楚,从个人的角度很难预测。人们都知道住房制度和公费医疗制度要进行改革,但这种改革在什么时候会走到哪一步,人们也不清楚。大家都知道教育制度要改革,孩子上学要交钱,但在大中小学各阶段究竟各要多少钱,人们心里也没有底,这种缺少预测性所带来的就是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因为人们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问题,这些问题会达到一种什么样程度,自己是否有能力解决。于是,从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可测当中,就产主了一种朦胧的不安全感。可以说,这种不安全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未来的恐惧。
特别应当注意的是,中国的改革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渐进式改革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减轻震荡和痛苦的程度,从而使改革进程不致由于一时代价太大而导致失败。但同时,渐进式改革的最突出问题是将这一过程拖得过长,旧体制只能一点一点地改,新的制度安排的建立,也只能一点一点地进行。因此,在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旧的制度安排失效,新的制度安排尚未建立而造成的真空状态会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这就意味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是生活在一种制度安排极不确定的社会环境中,很难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有效的预期,很难对自己的行为与目标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换言之,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人们很难把握自己的未来。
三、重新定位:每个人都须付出艰辛
其次,这种不安全感也直接与社会结构的调整有关。现在许多人都在议论改革与利益调整的关系。实际上,改革不仅仅是一种利益调整,而且也是社会结构的调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大规模的结构性社会流动。也就是说,一些原来在社会中处于较有优势地位的人,可能会失去自己的优势地位,而原来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劣势地位的人,可能会改变自己的劣势地位。这种趋势是明显的,也是必然的。改革的实质性意义就在于它改变了社会中稀缺资源的配置制度。
原来在社会中处于优势地位、获得资源比较容易的人,现在获得资源可能就相对困难;而原来在社会中处于劣势地位、获得资源不太容易的人,现在倒可能成为获得资源较为容易的、地位较为优越的人。前几年有一种说法,说是中国最先富起来的,是从“山上”下来的人。也就是说,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刑满释放人员,由于一出来没有正式工作,最早走上了个体经营的道路,因而也就成了最早富起来的人。相反,原来条件最优越的国家干部和国营企业的职工,却有一部分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下降,主要表现在福利待遇开始失去保障,部分国营企业的职工连就业和工资也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地位的稳定感无疑会受到强烈的损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在社会结构迅速变动的时期,每个人都面临着一个在社会结构中重新定位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未来的社会结构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位置,在很大程度上会取决于他在最近几年的努力。这样就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形成一种普遍的以迫不及待为特征的焦灼心理。实际上,在这样的时期,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每时每刻都在受到挑战。哪怕你是一个百万大款,也不能保证你在今后会处于富裕阶层的位置上。而目前在社会中处于中游状态的人的这种焦灼感更为强烈。中游状态的特点决定了这一群人,稍微一不留神,就可能滑到下游去;而努力一下,由于自己还有一定的条件,就有可能进入上流社会。可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无论是为了上去,还是为了不下来,都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于是,心神不定,甚至焦躁不安,就成为一种常见的心态。
四、金钱与信仰:两者不可或缺
普遍的不安全感的形成和存在,除了与社会生活中制度安排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有关,还与社会中的两个最普遍、最一般的因素有关。这两个因素,一个是金钱,一个是信仰。它俩虽然一个最为实在,一个最为飘渺,但都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安全感息息相关。
如前所述,安全感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人们对用自己的努力解决生活中会遇到的问题的能力的信心。这种信心可以来自很多方面,如对自己能力的信任,对社会的制度安排的信心,对自己已有财富的信心等。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所有这些信心和信任往往都是与对钱的信心相联系的。比如说,你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这种信心往往是根据你的能力,你能有一个什么样的收入,这种收入是否能养家糊口的计算的基础上;再比如说,你对退休金制度有信心,也往往是与这样的一种计算有关,即每个月的退休金会有多少,能否维持你的生存;如果你是对你已有的财产有信心,这种信心也会表现在,这笔财产每月或每年的利息或其他的收益会有多少,在你没有其他收入的情况下,这些收益是否能维持你或你一
家人的生活。这些很简单的例子说明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即对钱的信心,是其他许多的信心的一个重要基础。
正因为如此,一个社会总是将人们对钱的信心作为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来做。实际上,如果一个人连对金钱都失去了信心,我们很难相信,他还会对什么东西有信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维持对货币的信心,实际上是维持对一个社会的信心。在这方面,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恢复时期的作法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当时,德国的经济处于全面的崩溃状态,以“20世纪的亚当·斯密”著称的弗赖堡大学经济学教授艾哈德受命进行经济改革,重建经济。艾哈德认为,要重建德国的经济,就必须避免走上滥发货币的绝路,使人们对自己口袋里的货币满怀信心,并愿意付出劳动去挣它。为此,艾哈德在面临极大压力的情况下,坚持稳定工资,不允许工资的增加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由于人人都希望只涨工资不涨物价,艾哈德的措施遭到普遍反对。但艾哈德认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应该不为民情所左右。于是他差不多跑遍了整个国家,向所有的人,特别是不理解他的政策的人进行解释。结果,在整个50年代,德国的生活费指数只上升了16%,而同期的英国上升了45%,法国上升了50%多。物价的稳定,既为经济改革创造了条件,同时也稳定了人们对德国社会的信心。实事求是地说,近几年来,我国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已在开始对人们的信心产生有害的影响。一个明显的标志是,对于一定数量的钱在未来能够干些什么,人们无从判断。比如说,假如你现在有50万元钱,这笔钱够不够你养老,你无法判断。因为你不知道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你这50万元在几年后还能值多少钱。即使你加入了有关的保险也不行,因为保险的金额是现在确定的,这当中并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所以你不知道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几年以后在你领到这笔钱的时候,你还能拿这笔钱做什么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不安全感可以助长人的贪婪倾向。因为人们不知道究竟要有多少钱才会有保障,于是只能多多益善。在我国,最近几年有人主张用一定的通货膨胀的方式来支持经济增长。如果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说,这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为此而付出的社会代价将是巨大的,尽管这种代价可能看不见摸不着。
同时,信仰的因素也是重要的,在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特别是在社会环境处于变幻莫测的状态的时候,信仰是人们的一根重要精神支柱。这也许是老调重弹,但无论怎样,信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在急剧的社会变迁时代,信仰既是人们的精神寄托,也是借以为自己的行为定位的手段。而信仰的缺失,无疑是造成和强化人们的不安全感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