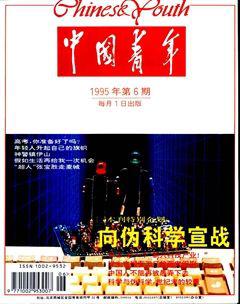年轻人,升起自己的旗帜
袁明
也许这是真的,我们对于生活感觉越来越没底了,这并非全由物质条件的不丰厚造成,而是我们今天的心灵必须为明天的生存忍受煎熬,这是一个沉重的代价。纯属物质基础方面的问题常常会使一个人激愤地发出“心里没底”的慨叹,就像天津那位工人和成都那位无业者一样;但是一旦人的心灵为自己的生存状态产生焦虑忍受煎熬时,即使他锦衣玉食养尊处优,恐怕也没法心里不慌,因为人是唯一能在遭遇尚未来临时会提前恐慌的动物。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心里没底呢?
当我们回首从前时,没有人会否认今天的物质生活水平比过去进步了许多,然而无法欣慰的是我们为生存历经动荡离乱之苦后才发现自己被抛入了精神的荒园,新与旧的碰撞,东与西的冲突,注定我们是一群失去精神家园的流浪汉!“在古老的沉积层上,断裂声一直不断”,这是文化学者眼里的时代特征。北岛在《履历》一诗中说:“当天地翻转过来/我被倒挂在/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眺望……”这是诗人眼中的时代人群。
马克思曾经指出,整个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无非是人类自身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在任何历史性变革中,人总是既作为变革的主体而参与,又作为客体而介入。只要外部的世界在我们的力量作用下发生了改变,我们自身,我们的心灵世界也就必然地无可避免地要随之发生相应的嬗变。只是,这两种改变未必彼此同步,未必协调。当外部世界的改变以汹涌的浪潮式变革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的心灵就会在被迫接受中产生焦虑。这种焦虑现在看来是如此普遍,以致凝结成一种情绪,一种普遍的对未来没底的灰色的情绪。
弄清我们的生存状态是有必要的,因为人生最大的可悲之事莫过于不自知地活着。这“好比两个同坐一辆列车的旅客,一个知道车到哪里而另一个则茫然无措一样,虽然两人都同处一列车上,但显然一个在路上,一个在家乡。”(北村语)“在路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想必是一种把自己牢牢抓在手中的信心感。有了这,我们才不会成为一只快乐的猪——明天进屠宰场,今天仍响亮地吃食。
然而,很难想像,一个人能在没有任何神圣的精神支撑的情况下而活下去,特别是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无可预知的生命旅途中时,活下去是艰难的,他必须选择一种支撑。在这个人的问题比人还多的世界里,我们能选择什么呢?唯有坚强。
所以,当我现在从容地倾听每一个在焦虑中生活的朋友讲述他们挣扎的焦灼时,我都特别感动。的确,生活是艰难的,而在现代文明无边的包围中,一个普通人想在这片土地上升起自己的旗帜决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它意味着我们一切的努力都要拼命适应现代生活的规则,而我们的目的地又在哪里呢?面对这个理想、道德、真诚无奈隐退,媚俗、渎神、欲望日夜狂欢的时代,我们因丧失信仰的根基而引发心灵的痛苦。然而,现代生活不接受投降,它接受斗争,不相信眼泪,它相信力量。我们只有以一种殉道者的坚强勇气,才能坚定我们的理想,寻回失落的人文精神并重新厘定心灵的坐标。
脱离具体的事实,那生活之河中曾有的激越与低沉、光辉与失落、浪漫与悲愁给予我的也只有一段丰厚的阅历、一些可贵的经验和一颗坚强跳动的心。很难说清现代生活的意义所在,但是在每一次面对不可预知未来的挑战时,我都支撑过来而没有垮掉,难道这不就是很有意义的吗?
其实,在这一时代里,坚强地活着本身就是生命价值之所在,也是人生目的之所在。
编后:关于“我为什么心里没底”的讨论受到了很多青年朋友的关注,编辑部收到很多来信来稿,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没底”的普遍心理感受。这些讨论令人欣慰。我们欣慰于这些青年朋友对自身和社会的自觉的反省意识;欣慰于他们的理性思考的不断成熟。我们希望,这次讨论能够成为我们更加自觉成熟的开端,成为我们在思考中感受快乐的开端。欢迎青年朋友继续为我刊提供更多的思考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