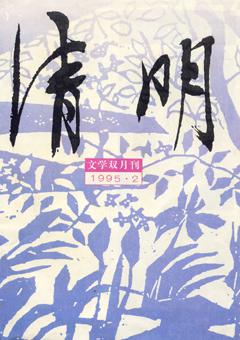海湾
聿 言
近海的村庄绿荫掩映、依山傍水,村后丘岭山脉绵延北上,渐次耸起巍峨。一条沙河在村前缓缓流向大海,两岸的沙岗上是浓郁的松林。
这是第一次回故乡留在脑海中的印象,一个根深蒂固的久远记忆。
那是饥荒最严重的一九六○年,我和父亲带了十多斤大米,坐船坐火车坐汽车。那时我还小,懵懵懂懂,不谙世事,记得在内河的船上我看见一条金色沙滩,沙滩在阳光下闪烁着银黄的光。我兴奋地指给父亲看,父亲望着沙滩不屑地说:“回故乡看看大海吧。”
父亲抗战时离家。离休后愈发有叶落归根的恋乡情结。父亲多少年前就开始念叨:“回去吧,有山有海,有沙子有石头,做几间房子是很容易的,每天看看大海,听听涛声,逛逛果园,我就满足了”。父亲念叨归念叨最终还是未能成行。于是父亲就从故乡的旧友处弄来县志和县区地图,于是父亲就有了看县志的嗜好,就长久地伫立在故乡的地图前,地图上就有了一条粗粗的红线,红线环绕海湾——那是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凝聚了他昔日的辉煌,是值得他一生炫耀的历史。
六十年代村里的房舍大多是祖上留下的旧宅,石头的墙,屋脊或草或瓦,用碎石或荆棘围起的农家小院古朴宁静。村前有一古槐,槐下有一石磨,一古井,蒙脸毛驴绕着带凹槽的石磨不停地转,井口的辘轳和石磨的吱扭声昭示着岁月的沧桑。
在故乡下车是傍晚,走在故乡的沙土路上,看见东边的滩岭上是大片的松林,松林上空血色迷蒙。有风拂面,隐隐听见涛声,父亲深深地吸闻着,说:“闻到海了。”
祖屋的土炕上坐着老少爷们,旱烟袋抽得吱吱响.烟锅子闪闪亮亮,煤油灯的火苗半死不活地摇曳着艰难。老少爷们儿都黑着脸不说话,不停地抽烟,咳嗽,叹气。
第一次回故乡没有欢笑,第一次去看海又赶上阴天,铅样的乌云笼罩着海湾,笼罩着一群饿得半死不活的人,回来父亲让屋前屋后的娘们熬米汤,屋前屋后的娘们来了,风箱有节奏地呼达呼达响,灶火呼呼地闪亮,把一张张菜色的脸映得有了红润,老屋里就有了欢快的气息。大锅的米汤熬好了,一时间老屋里喝得海响。
我们走时,爷爷送了很远,说:“常回来,别把故乡忘了”。
一九九四年八月处暑后的一天中我在故乡村后的北山上眺望原野;原野辽阔,那是两山问的一个小平川,即将成熟的花生,大豆、谷子、玉米和成片火样蓬勃跃动的红高粱。浓绿的原野上点缀着红砖红瓦的屋舍,太多的楼房使村落失去了他的原始古朴。远方的大海湛兰,绵延海岸的金色沙滩向无限的远方伸延,沙河水在高高的艳阳下流成了一条白色光带。
北山上的果园已经废弃,不结果的果树枝干道劲,老态龙钟,山下的果园青翠茂盛,果实累累。
我走进北山的小松林,松林里埋着我爷爷,松林外的高岗上埋着二十年代的老党员和抗日的老战士,也埋着村里过去和现时的一些为富不仁的人。一个人生于土地又归于土地,土地是人的归宿,生生死死的循环.人和土地难以割舍;归于土地享受了夏月秋阳、春雨冬雪的滋润和海风的抚慰。自然界对人类是公平的。人的心灵在自然的循环中得到净化和洗涤。海天相连的远方充溢着无边的静谧和博大的宽容,详和氛围让人感到心的空灵,城市的喧嚣归于沉寂,浮燥的心灵趋于宁静,让人看淡了小肚鸡肠的功利算计和商品交换的斤斤计较以及官场生活的谨小慎微和迎来送往的劳累。
田野的绿地里有劳作的人们,上工或下工的男女骑摩托或自行车在乡村的沙路上穿梭往来,新潮的服饰和彼此的招呼应酬妆点了野地的风景。
远处的山巅云雾缭绕,雾浓雾淡,山川变幻着姿容;大海上波光粼粼。潮涨潮落,风起云涌。
文革动乱之年的一个秋天,我和姐姐在武斗的枪炮声中回到故乡,那是一种落荒的逃难。父亲说:“回去吧.活下来一个是一个,打死了不值”。在故乡的日子我和姐姐脱笼鸟似地活跃在乡问,最值得回忆的是去赶海的日子,海湾的一隅有一片礁林,一汪汪未退去的海水清澄碧蓝,拨开水里的石头偶尔还能抓到海蟹,记得为抓住一只虎头蟹我让蟹夹住了手指,我吓得摔倒在水里哇哇哭叫。赶海的日子有时会碰到拉网的。看拉网时姐妹们都回避列松林里去拾蘑菇挖沙参去了。渔民们在沙滩上排一长蛇阵,一律赤裸,偶有腰间扎一塑料布,肤色黑黢油亮,隆重起的肌肉充满了活力,弯腰弓背哼哟哼哟的号子在空旷的海湾回落,号子沉郁,铿锵有力,是男子汉从肺腑深处涌出。弯腰拉纤的过程十分沉重,太阳缓缓地西沉和纤绳的缓慢上移几乎同步。起网时鱼在网面上窜跃,海鸥在海面低空翱翔,晚霞在波峰浪谷间汹涌扫荡。
文革中这海湾的一隅并不是避风港,记得半月内村里来了两批搞外调的,第一批是造反派,整我爹的,在村里理所当然地受冷遇。第二批是保我爹的,故乡的人盛情款待,中午做了一桌海鲜席,前屋后屋的娘们把平时吃高粱米,玉米面窝头省下过年用的白面拿出来包饺子,下捞面,烙煎饼。
我是带着一身的红疙瘩离开故乡的,是水土不服还是海鲜过敏我不得而知,爷爷说:“回去跟你爹说,在外边不好干就回来吧,自古忠孝不可两全,尽忠不能尽孝,尽孝不能尽忠,回来种地,一样地活人”。
海连着世界。
广阔的地平钱和蔚蓝的大海让人心胸开阔,狭隘的生存空间和浮燥的生态环境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使人在一定的地域文化和价值观念中无力挣扎,在自己给自己编织的网中倍受苦难。
我背着网远避喧闹的浴场,我向着僻静的沙河入海口走去,沙滩上留下了一条长长的脚印,我期望有捕鱼的收获,尽管那是很遥远的往事了……
太阳像烧着了似的在波峰浪谷上滚动。
脱了衣服,赤条条地站在绚丽的霞光里,我看见爷爷的身躯呈古铜色,苍老的褶皱像是身后的柏树皮。
爷爷站在海边,深吸口气,掬两捧水泼在身上,然后一步步走入沙河,爷爷扭腰,甩臂,哗,网在天上划了一个优雅的弧,又疆地张开一个臃肿的圆,只听,刷……,水面上霎时溅起一片金黄,爷爷一把一把悠悠地把网收上来,空的。爷爷把网顺好哗……又甩出一片金黄。
我全神贯注,站在岸上满怀希望地瞅着,可一网一网收上来,总是空的,我很失望。
太阳慢慢地升高,海面波光万顷,潮水愈来愈急。这时,一股道劲的海风拥着倒灌的海水急湍地涌了过来,浪叠着浪,浪连着浪,浪推着浪,爷爷从水里猛地一个趔趄,倒了下去。
“爷爷……”我站在岸边大叫。
爷爷挣扎着从水里站起来,笑哈哈地说:“老了,真的是老了,不行了,脚跟不稳了。”
爷爷走上岸,把网交给我说:“你来,学着撒”。
我学着爷爷深吸口气,掬两捧水泼身上,然后走进水里。我一次次笨拙地把网甩出去,网歪歪扭扭张开一个盆大的圆。我一点也不气馁,一网一网甩得极有信心,可网网总是一个歪歪扭扭的圆。
爷爷站在岸边,燃了一袋烟,一边抽一边笑。
我再次一将网甩出去,感到有点沉,慢慢将网收上来,啊!三条尺把长的大鱼。
我兴奋地拎着网,哗哗地淌着水,跑上岸。
“网打该死的鱼,网打该死的鱼呀”。爷爷高兴地哈哈笑着,把鱼取下,拴好,说:好运气,一定是碰到渔群了,网要是撒得圆,何止这三条,我来吧,你骨子嫩,看把嘴都冻青了”。
爷爷又把网撒开一个又一个臃肿的圆。
我在岸上焦急地瞅着。
很长时间过去了,大海浪涛翻卷,太阳已升上中天,可爷爷一条也没撒到。爷爷很疲惫地走上岸说:“鱼群过去了”。
我想:爷爷是老了。
我和爷爷走进岸边的松柏林里,坐在温热的沙滩上。沙滩像是一条金色的带子,缠绕在一片绿色里。爷爷又燃上一袋烟,吱吱地抽起来。我大口嚼着早上出门时从家里带来的玉米饼子。
爷爷说:“网打该死的鱼呀,海是那么大……我这一辈子也只打过一回大鱼,小时候的事了,也是你这么个年龄,你老爷爷带我来的。”
“你也只打到过一回?”
“是呀,只一回。”
我不再说话,茫然地望着大海,很骄傲很自豪地嚼着大饼。
天水相连,一色凝碧。
那年深秋季节的一个黄昏,爷爷去世了,爷爷在北山的松林里,望见了烟波浩渺的大海吗……
一年一年过去了,我肩上扛着那张网,又一次走到沙河的入海口,我已经能将网张开一个臃肿的圆了。
那天我没有捕到鱼,我并不感到沮丧。我完成了一次捕鱼的过程,这个过程让我感悟到人与人的偶然,人与社会的偶然,人与机遇的偶然。人生是短促的,偶然性实在是太重要了。
浑圆的太阳每天从海里升起,又降落在西边的山蚴里……
文革结束的那年我再回故乡村庄已面目全非,学大寨学出的低矮的红瓦房代替了世代的祖宅,高音喇叭立在村中央,整日不息地聒澡。村已被统一意志了,长期的公社化道路使乡民们失去了自由创造的空间,表面的虚华掩饰着生产力的衰败和不振;同龄的兄弟姐妹们失去了昔日的天真,苦涩的微笑、饥黄的面庞,和儿时如同隔世。去叔家,婶有力无力地说:“大侄子。你回来了,你婶家断了顿了。”说着泪水潸然而下。叔说:“你爷爷靠你父亲那俩钱供养着,没啥大问题,村里不行了,又开始跑关东了。”
我感到心里很苦。
回忆故乡充满了苦涩,故乡的历史是乡亲们和苦难和饥饿不懈的抗争史。
前不久海娃从故乡来,带着故乡的乡音和强犟在都市里跑业务。姐请了几天假,每天带他跑,姐既当向导又当翻译,把海娃难听的海湾侉话翻译成甜媚的吴侬软语,每有成交的希望,海娃总要请客,请客必喝白酒,又总是再三地和客户拼酒,客户不堪一击,甘拜下风,这时海娃总是为客户代酒,说你不喝我替你喝,你不干我替你干,姐每每使眼色示意其收敛,海娃视而不见,说我喝一个海湾人的豪爽和信义给他看看,朋友之问舍命相陪,业务还有什么不好商量的。后来我对海娃说,城市现在不兴这套,现在兴时喝文化,喝品位,喝娱乐,像你一脸的紫色,网状的色丝在底色上缠绕,一副酒精中毒的样子,长此以往,何以得了。海娃说:“咋富起来的,起步喝,发展喝,拉关系找门子喝,没关系没背景没后台,靠什么,靠咱死干硬干拼命干,靠咱海湾人的诚意和信用。不喝行吗,你们都离的远,要是近点,要是在家门口,我们也有个攀附!”
我无言以对,联想到海娃当年不愿去集上卖鸡蛋、水果的窘态,不由我对故乡人刮目相看。
一个古朴宁静的村庄正在消逝。
父亲已多年未回故乡,那片古朴宁静的海湾已经消逝,代之而起的是海湾的开发和建设,我们这些远方游子还能在故乡觅到一丝温馨,一丝乡情,一席归宿之地吗?父亲建一青石小屋围一圈荆篱的宿愿还有希望实现吗?海湾的风还有一丝腥成,村庄楼房内的大炕还有暖一屋老少爷们儿的火热吗?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方人恋一方土。
我思念故乡。
我为故乡祈祷。
责任编辑孙民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