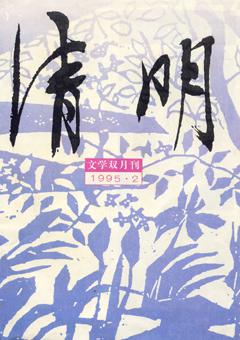野女人
顾 鸣
她是从外地嫁到这地方的。
这地方是奔腾的大江中的一个岛,十里长五里宽,岛四周长着绿茵茵的水柳和芦苇。这地方的男人在外种田打鱼。女人在家纺纱织布饲鸡喂猪,本本分分地过日子。这地方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离开这被水柳和芦苇围着的小岛,所以对岛外来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好奇。谁从江南岸十里外小镇买回一头猪崽.左邻右舍都要围拢来观赏一番,评头论足一番。何况是她,一个大活人呢!
他丈夫叫王三,是个吃了上顿愁下顿的穷光蛋。三年前,他娘病死了,他安葬了老母,将两间茅屋的杨木门上挂了把锁,拨开岛上浅滩的水柳和芦苇。卟嗵跳进了大江里,自然不是寻短见,他游到对岸,外出闯世界去了。岛上人都记得,跳进江里时,把一个破包袱顶在脑门上,怕江浪弄潮了可怜的穷家当哩。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三年后他回岛时,一身新衣衫,还带回一个天仙般的老婆。这女人二十四、五模样.脸儿自白的,眉儿细细的,眼睛亮亮的,鼻翼两边有几颗俏雀斑,就像荷叶上粘的露珠儿,映衬得眉眼更活泛了。岛上那些黑脸皮粗腰身的闺女媳妇们,站在她面前,自觉矮了一截子。莫非,这女子是深山里修炼千年的狐狸精,幻化成美女迷住了王三,白天为他浆洗做饭,夜里吸他的精血么?可王三说起话来,嗓门儿锵锵的,走起路来;脚步儿铮铮的,身骨子硬实哩,精神气旺着哩,不象狐妖附身的样儿。于是,当岛上人瞧见这女子张嘴说话时,嘴里镶着两颗亮灿灿的金牙时,又私下里猜测,这女子有十有八九是大户人家小老婆什么的,贪恋王三英俊壮实,跟他私奔的。这女子的口音侉里侉气的,小岛人只听那声音脆亮亮,宛如枝头黄鹂啼叫,就是听不懂她究竟说什么来着。王三介绍说,他的妻子叫柳儿,是北边人。北边?敢情是安徽地界上来的?王三摇摇头,说还要北哩。岛上人啧嘴咂舌了。前几年,来了几个要饭化子,说是老家在安徽,走了一个多月,到江南来寻活路。这女子从比安徽还要北的地方来,那路上得走多久哟!该不会是从外国来的吧。
谁也不叫他柳儿,这名字岛上人觉得拗口。根据岛上习惯,当面.都叫他三娘子,背地里呢,就称她野女人。
王三回来时,他那间茅屋快要倒塌了。
他割了十斤猪肉沽了十斤水酒,请乡邻帮忙将破茅屋修葺一新,又添置了锅碗瓢勺,好歹安顿下来。屋前有块空地,砍了几捆苇杆,围出了个小院。白天,王三下地干活去了,三娘子也不出去串门子,在苇杆围着的小院里忙忙碌碌。左邻右舍只在苇杆隙缝里见到她那好看的身腰闪来闪去,喂鸡啦撵猫啦,那侉里侉气的嗓门儿,听来蛮悦耳的。
半晌午,雄鸡伸长脖子打鸣后,苇杆篱笆的小门吱一声启开了,三娘子一手拎着菜篮子,一手端着米箩子出来了。胸儿挺挺的,臀儿扭扭的,几十步外就能闻到她身上的一股香味儿。遇见人,弯起眼梢儿微微那么一笑,算是打过招呼了。“三娘子,淘米煮饭哪?”“唔!”脸上仍然挂着笑,轻轻点点头,就这么过去了。走到水塘边,踏着伸进水里的木跳板,搁下菜篮和米箩,蹲下身。也不淘米.也不洗菜,对着一泓清水理起鬓发来。清水如镜,映进了蓝天白云,映进了绿草红花,她就映在蓝天白云和绿草红花之中了。眼皮儿有点儿酸涩,蘸点儿清水揉揉,顿觉爽快多了,揉着揉着,手儿忽然凝住了,双颊飞起了两朵红云。
几只白鹅游过来了,啄她篮里菜,啄她箩里米。她醒过神来了。嘘嘘地赶白鹅儿。白鹅儿扑扇着翅膀往池塘中央逃遁,搅起哗哗的水花,溅湿了花衣衫。
丽日中天时,她又挎着竹篮给丈夫送饭。竹篮里装着饭食和水罐。小岛巴掌大,王三耕作的那块地离村不过二里地,其实他可以回家吃饭的。可她偏要送饭。她说独自在家闷得慌,吃饭不香,她喜欢到野地里走走。她在黄泥小路上慢慢行进,有花蝴蝶撞在她胸上,有紫蜻蜓停在她头发上,她逮花蝴蝶。她逮紫蜻蜓,她都没逮到它们,她像孩子似噘起了嘴,她生气了。过一会又笑了,她被路边的野花野草吸引住了,于是他便弯腰摘采那些中意的花草,一会儿,竹篮里的饭钵和水罐都被野花野草盖住了。王三吃饭时,嘴里总能嚼出幽幽的野花味儿。
有人看到他俩头碰头在田头树荫下,躺着歇息,甚至还搂在一起滚来滚去的,把身下的小草都压得淌出绿汁来。庄稼人看不惯了。夜里在床上亲热还不够么?还要丢人现眼地在野地里鬼混!这太阳亮堂堂的,你们不要脸皮,老天爷还知羞耻哩。唉唉,这小岛好端端的淳朴乡风,要被这个北边来的野女人败坏啦。
王三家小院的苇杆门上倚着一支乌黑的枪。左邻右舍眼里瞄着这杆枪.宁肯绕道,也不敢靠近王家两间茅屋了。王家的厨屋里透出一股股鱼香肉香味,狗儿闻到了香味,流着涎水,要去钻王家的苇杆篱子,立即被主人喝住了,“畜牲,送死去哇,吃枪子儿去哇!”
这杆乌黑的长枪,是保长的。保长住在大江南岸的一个大村子里,他每隔一、二个月,总要到辖下的小岛来巡视一番。小岛树木多,岛儿也多,保长就打鸟取乐,子弹嘘嘘地飞,有时打着了鸟,有时打着了地上的鸡和鸭。不管是鸟是鸡是鸭,只要打着了,保长就乐呵呵地笑。玩够了,玩累了,保长就扛着枪,手里拎着鸟或鸡和鸭,走到岛上某家的屋前,“喂,来客啦!”笑呵呵地一声吆喝。屋主人听见吆喝,忙接灶神似地将保长请进屋里。男主人安顿好客人,就借故说田里活计忙,扛着锄出门了。自然,女主人一定会殷勤招待保长的。自然,这女主人一定是长得眉清目秀的。面目丑陋的女子家,保长是决不去的。保长就和这眉清目秀的女主人一直厮守到日落西山,才乘小舟回南岸。
王三在田里干活,觉得肚子饿了,抬头看看,阳婆已经爬到了中天了。翘首望望,通往村子的小路上没有妻子的身影。怎么不送饭来,莫非她身子不舒坦.病了?心里焦急起来.就匆匆回家去。离家百步远,他被乡邻们拦住了.都说:“你避避吧,保长在你家里!”王三一腔热血直往脑门心涌,推开众人,犟着要进自家的门。乡邻们抱胳膊的抱胳膊,拽腰的拽腰,人多势众,硬把王三拉进了村头的小酒店里,好酒好莱好言劝慰王三。小岛人心善,他们不愿眼睁睁地看着王三往虎口走。保长的那杆枪可不是吃素的。
此刻,保长在王三家里喝得有三分醉了。三娘子眼里含着七分妩媚,频频劝酒,“保长大人,俺家没鱼翅海参招待你,这肥肉瘦鸡准不合你胃口,可这糯米酒,你一定要喝了哇!”“喝,喝!”保长只顾瞄那花朵一样的脸蛋儿,瞄那鼓突突令他神魂颠倒的稣胸,那杯里的酒,大半顺着下巴淌了,蓝布长衫胸口湿漉漉的。保长情不自禁,趁三娘子俯首斟酒的当儿,佯装过意不去,“够了够了,再喝要醉了!”手轻轻那么一抬,撞击到女人胸口鼓突的地方。保长象被马蜂螯了一下,惊叫一声,猛地缩回手来。看那手背,早已沁出红殷殷的血珠儿。这女人胸口里藏着针哩。保长脸色讪讪地,闷闷地喝了口酒,闷闷地嚼着鸡翅膀。
三娘子依旧那么媚妩地笑着,说:“保长
大人,喝酒啊!”“够了够了,这酒辣!”保长苦笑着,起身告辞了。怏怏地,乘船回南岸去了。阳婆才偏西,天色还早,保长是第一次这么早离开小岛的。保长爱女色,喜欢自愿跟他上床的女子。强扭的瓜不甜,不甜的瓜他是不肯偿的。瓜总归会熟的,熟了的瓜总归是甜的,保长不急,保长在这方面极有耐心。
王三回到家,见自家婆娘端端庄庄坐在堂屋里绣花,衣衫整齐,头发不乱,不禁喜出望外,乐颠颠地扑过去要搂她的腰,她推开他,指指自己的胸。娘哟,胸襟里插了十几根缝衣针。王三愣住了,眼角湿了,拉着婆娘的手,呜咽着说,“柳儿,苦了你了!”她浅浅一笑,“这保长还算知趣,要不然,我裤兜里还藏着剪刀呢。哼,他敢撒野,俺就敢绞断他那骚根儿!”
保长离开小岛后,三娘子依旧每天给丈夫送饭,依旧在田头的树荫下搂搂抱抱。不过,岛上人也见怪不怪了。岛上的男人心里痒痒的,虽不敢在野外放肆,但到了夜间,也不知不觉学着王三的样儿和妻子恩爱亲热起来,男女间的乐趣增添了许多。
三娘子除了在家煮饭喂鸡操持家务,空闲来就坐在小院里绣花。这地方的女子几乎都会绣花,土布做的头帕和围兜,都用红线绿线绣上牡丹鸳鸯什么的。就是绣得过于简单粗糙,牡丹是圆圈和长方形组合的,鸳鸯呢,则成了似鸡似鸭的怪物。乡下人也不甚讲究,不管怎么,好歹算是个点缀。当三娘子把她的第一批绣品展示在乡邻面前时,可把大伙看傻了。那荷花牡丹,叶是叶,花瓣是花瓣,一片花瓣的颜色也深浅不同,活脱脱跟真的一样。每隔十天半月,王三背了一包袱绣品到南岸的小镇去卖。他不乘渡船,就像几年前离家时一样,头顶着包袱凫水到对岸。绣品好卖得很,刚摆出来.就被镇上的姑娘嫂子们买去了。回来的时候,王三脸上笑得能刮下蜜汁来。回来时他乘渡船了,他买了许多吃食,有酒有肉,还有云片糕桂圆核桃什么的,装在高腰篾篓里,沉得很哩,王三身子载不动它们哩。
邻居孩子闯进王三小院里玩耍,三娘子总是眉开眼笑地拿出云片糕桂圆核桃款待他们。“来,洗洗脏脸,洗洗黑爪爪!”一盆清水变成了浊水,孩子们那积着黑垢的脸肤变得水灵鲜嫩起来。又打开胭脂盒,指甲盖儿撮那么星点儿,在那水灵鲜嫩的脸颊上再添那淡淡的两朵云霞,是女孩儿,还要用烧焦了的半截的火柴棍儿,画两弯细细的月牙儿。哦,一个个脏小子脏丫头,经这么一打扮,成了金童玉女啦!
三娘子这么爱孩子,她自己怎么不生一个呢。邻居婶嫂子们密切注意她的肚皮。好几个月过去了,那肚皮总是鼓突不起来。嗨,闹了半天,这野女人是绣花枕头,不生蛋的肥母鸡!于是,王三沐浴在怜悯的眼光里了。眼看王三这一户要绝代了,百年后没人在坟头烧纸添土,挺可怜哩。
保长又来小岛打鸟了。中午他没吃饭就离开了小岛。走的时候,他脸色很难看。出鬼了,小岛上的俊俏女子都学三娘子了,胸口衣襟上都插了针了。他心里恨恨的,乘渡船到江心,他端起枪.对准小岛。呼呼呼,把打鸟剩下的子弹全打光了。
保长上了南岸,遇见了王三。王三从小镇卖完绣品回来,嘴里哼着俚歌小曲,脚下生风,喜气洋洋。
“唷,王三,拾到金元宝啦,瞧你乐的!”保长说。
“保长,又上岛打鸟啦,打到不少吧!”王三说。
“屁,鸟毛也没撩到,岛上的鸟都变精了!”
王三无话,和保长擦身而过继续赶路。保长探头望望王三背篓里的酒肉和各种吃食,喷喷嘴,说:“王三,你好福气,讨了个仙女似的野女人做老婆!”王三笑笑,还是无话,和保长背道而行。保长望着王三的背影,呸地吐了一口痰,那痰粘稠,腥臭。
一个月后,王三失踪了。人们在小岛下游二里多的芦苇滩上找到了他的尸体。英俊的王三已经面目全非了。鼻子和眼睛被鱼吃掉了,肚皮被水泡得发绿,隆起如孕妇,爬满了苍蝇。此地习俗,野外暴死的人,尸体是不能进屋了。王三就躺在他家苇杆小院里。尸体刚抬进小院时,三娘子嚎哭着扑过去,众人忙把她拦住,那尸体已经溃烂,碰不得了。三娘子挣扎几下就昏死了过去。醒来,她也不哭了,沉默地跪在尸体旁边,她的头低垂着,秀发遮住了她的脸。尸体上的苍绳,围着她前后飞舞,有的苍绳钻进头发,停在她的眉眼上,她无动于衷,就这么一动不动地跪着。太阳热辣辣的,尸臭熏得人反胃欲吐,众人都退避到院外了,院里就剩下孤零零的三娘子。众人站在院外不敢离开,怕三娘子有意外。果然,三娘子身子一歪,倒在地上,又昏过去了。众人将她抬进到院外,七手八脚地将她弄醒。用清水替她擦脸时,众人发现她的汗水黄粘粘的,怀疑她的苦胆破裂了。胆汁渗在汗水里了。大伙劝她,“人死不能复生,你别把苦水闷在心里,放声哭吧,把苦水哭出来吧!”三娘子摇摇晃晃地又进了小院,低头跪在王三尸体旁,一动不动,不哭。跪着跪着.身子一歪又昏倒了。众人又把她弄醒,醒后她又跪,还是不哭。众人见这样下去,三娘子非自己把自己折磨死不可,趁她昏迷时,将王三的尸体装进棺里埋了。
三娘子醒来,不见了王三尸体,说了句:“冤死的夫啊!”哭出声来了。
王三的坟头被青草染绿后,保长来小岛打鸟了。保长有三个月没踏上小岛了。小岛没什么变化,仅仅多了一个王三的坟头。三娘子白衣白裤,在坟头烧纸钱,纸钱灰随风乱飘,飘到保长脸上。保长顿生恻隐之心,两脚不知不觉向坟头走去。三娘子听见脚步声抬起了脸。保长吃一惊,三娘子穿了白衣白裤,竟比以前更楚楚动人了。保长想,她肯定不是凡人,她是天上下凡的仙女,只有仙女,才有这么美。就在这时,三娘子突然嫣然一笑,保长顿时感到自己仿佛化作了一滩水……
这天夜深人静的时候,王家的茅屋里突然传出了一声枪响。那声音沉闷、有力,好像憋足了气的车胎猛然炸开了,在静夜里显得格外撼人。人们从睡梦中惊醒,纷纷向枪响的地方探头探脑,但谁也不敢靠近。“那是保长的枪!”有人小声这样嘀咕。
第二天早晨,一个更惊人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小岛:保长死在王家茅屋了:他赤裸着身子,脸被猎枪的霰弹打得血肉模糊。四肢痉挛着,看得出死前曾进行过痛苦的挣扎。三娘子不在屋里。后来,人们在王三的坟前发现了她,她的身体已经僵硬了,但脸上的表情仍是那么安祥,那么美丽……
责任编辑季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