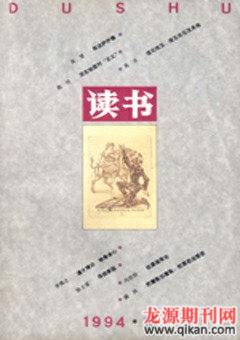儒家思想与自我
传 圣
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有一本不厚的论文集,名字叫《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换的自我》(Con-fucianThought:SelfhoodAsCreativeTransformation)。大陆的中译本,易名为《儒家思想新论》。说“新论”,并不错,因为无论是经典的中国哲学家,还是后来的中国思想史家,似乎都没有想到要把自我,selfhood,ego,作为思考的出发点。
儒家学说说到底,不过是成圣成贤之说。外王只是内圣的推论与结果。而整个成圣成贤的思想脉络,是自我论的。成圣的基础、目标、途径都是在个体的生命、或自我中实现的。因此完全可以在自我论上建立新的儒学。杜维明教授无疑这样做了。
然而我们不应高兴太早。当我们细心地考虑自我、自我论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在西方或中国思想与用语中,当我们讲“自我”时,不是将“自我”与自然、道、上帝、道德原则等对称,而是将其与“他人”,由他人组成的“社会”对称。“自我”,谁要说这两个字,就让别人也让自己把眼光集中在“我自己”上。“自我”即“我自己”:不是我与他人的共同的地方,也不是我的社会特性,而是我的独特性。为了显示出,或说清楚“自我”、“我自己”,就要把目光从共性、社会性、高踞于你我之上的原则中移开,专注“我自己”的独特性。
自我论可以是主体论的,但这种主体论中的主体是不同于你、他,即所有人的那个独一无二的主体。这个主体有别人无法代替的独特的经历、感受、世界。它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与他人、你、社会、你们、他们对称的。这是自我的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含义。
很显然,这种意义上的“自我论”在人类思想史上是很晚才出现的。在道德、宗教、理性主义(总之使人关注共性)的时代,不可能有完整的自我论。这种自我论在中国尤其缺少。显然,对自我独特性的认识,并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价值肯定下来,首先是艺术对人类的贡献。
给不同个体的独特性以地位,不仅强调人的尊严,而且强调“我自己”、我个人的尊严,把我的独特性当作尊严的一部分要求被承认、被尊重,把我的独特性当作人与人交往中的一条定理与价值,这在思想史上出现更晚。要为之立法,所谓保护人的隐私权(当然隐私权或隐私并不等于自我,但要求尊重隐私权必以发达的自我论为文化前提),则是更晚,或干脆是当代的事情。承认、尊重“我”的独特性,并视此为一项基本价值,这不妨作为自我论的第二层涵义。
这样一梳理,我们便很难同意杜教授的革命。因为如果不能在儒学中发现对“自我”、“我自己”或孔夫子,或子路,或冉牛,或卫灵公等人个性的独特性的承认、描述(第一义)与辩护(第二义),我们便不能说儒学中有一条自我论。同样,若不把儒学再行视为对个人自我的独特性的辩护,便不能视杜教授的儒学研究“新取向”为恰当。
儒家思想,其实是“去我论”或“勿我论”。《论语》有个教条叫“勿我”。王阳明把人的“去私”过程看作是艰难困苦的。儒家要做的,是去掉独特、怪僻、个人或私下、自私性的东西,而让完全抽象的、社会性的、超越个体的原则占统治地位。他们的兴趣自始至终在于发掘日常的、个人心理的独特体验中浮现出来的共同的东西,是共同性,社会性,而独特性、个性被儒学的思想筛子筛掉了。这不是儒学的缺陷,而是它的特点。因为儒家并没想建立一套完整的人的学说。同样,在儒学中也完全看不到自我理论的另一方面内容,即为个人的独特性、私自性、私下性、不可替代性,总之,一切可以归结为遗传、教养、身体状况、社会遭遇等等的东西的辩护,为它们的存在的合理性而辩护。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见解,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有自己的生活、行事方式——当然这要在不侵犯别人的前题下,这种有条件的自我辩护论,不仅不是儒家提倡的,也是儒家学者连想都不敢想的。
(《儒家思想新论》,杜维明著,曹幼华、单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3.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