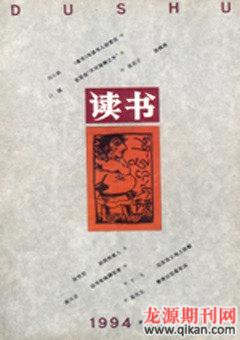好之乐
我总是不相信“命”,但总是私下里思忖:只怕“运气”还是有的。在我求学的过程中有那么几件事、几个人令人无法忘怀,它们支持着我所谓“运气”说。
我少年立志,想学建筑学,考上同济建筑系之后,我便开始打听,谁是“大师”?持何种“法器”?如何向他们学习?这类想法,虽说极幼稚,倒也给自己造了几个“神”,于是乎,便真诚地信奉了起来。
诸“神”中,第一人应该是当时同济建筑系的系主任——冯纪忠教授。我入学的时候他已步入老年,几乎不上课。我这种一年级的毛小子,是见不到他的。只是看见他的杭州“花港观鱼”方案在“设计革命化”运动中大受批判,说是个“道士帽子”,是他那个“反动”的“空间理论”的代表作云云。我一时也闹不清是什么回事,只记住了冯先生的学问是“道士帽子”下的“空间原理”,反正谁也说不清,只好自己去“悟”。时势造“英雄”,我竟与“禅”早早地挂上了。
正当我“悟”它不出,百思不得其解之际,文化革命来了。这下子冯先生的境遇更惨了。当时,我正值大学二年级。我对自己的评论是:热爱毛主席,忠于他老人家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却还是想弄清楚冯先生的“空间原理”。于是我开始收集批判“空间原理”的文章,并试图偷偷地与冯先生接触。
当时,据知内情者说:冯家是不做饭的,冯师母弹钢琴,手指不能做粗活,冯家与“黑画家”林风眠是世交,讲求西方艺术,要批斗,要将他劳动改造。于是,平常见不到的冯先生被通知到系里做“苦力”。我想去接近他,又怕人家看见,说我划不清界限。
苦于怎么也看不懂那些批判“空间原理”的文章,自己“悟”也“悟”不出个道道,我一时冲动便“铤而走险”了。一天下午我趁没人,请了冯先生到一间没人去的公共教室里去向他“求教”,冯先生当时摸不清我想干什么。神色颇为茫然。等我说明来意,他便松了口气。当我问及有关“空间原理”的问题时,他便笑了,然而他笑而不语,只觉得他笑得善,笑得惨,我便不忍心追问。我们俩似乎也同时意识到这个“学术讨论”大不合时宜,甚至会闯祸。我一时也不知如何结束这次谈话,匆匆离去只记得先生说了那么一句:“这个问题一下子说不清楚……”一九七○年我就是带着这个“说不清楚”的问题,对“空间原理”的悬念,离开同济,去了甘肃武都——一个我更陌生、更不清楚的地方的。可是,我还是觉得自己“运气”。我在学术界最为难的时候,让老师笑了,并告诉了我有些东西“一时是说不清楚的”。言下之意,要懂么,有过程,需要时间。二十年之后,在一次学术会上,我又见到了冯先生,跟我握了手,说了声尚记得我,我心里一酸,“先生老了许多……”因为当时周围人多,我没说出个所以然。那是一九八九年,我已中年,“空间原理”的问题,已不必再去烦先生了,只是想看看他——我青年时期心目中的“英雄”。
在江南大才子中,还有两人:童
承蒙潘谷西与刘先觉两位先生的爱护,兼有我的师兄朱光亚先生的帮助,我被从甘肃招到南京工学院历史与理论教研室当研究生:攻读“西方建筑史”。导师挂名童
当时,文化革命刚结束,关于西方现代艺术的著作很难找到。弄到一本台湾出的译著,作者把中文当英文写,令人费解,加上我又从事“革命现实主义加浪漫主义”的美术活动多年,说什么也接受不了那些用“新”名词所堆砌起来的文句。好在南工建筑系旧资料极丰富,我找到了一本SigfriedGiedion(一八八八——一九六八)的Space,TimeandArchitecture,才勉强摸出了个头绪。在写论文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现代艺术的那一部分,我还是很吃不准自己对cubism的理解,时间紧,心里烦,一时悟性没了,真想去问问童老先生。童先生年事已高,天天在资料室看书,做卡片。我们都守“规矩”,不敢去烦他。当时我实在是被Picasso的那些五花八门的画儿搞烦了,心想,无论如何得麻烦童先生一次,于是,我便向童老凑了过去。出乎意料,童先生极随和,而且幽默。他为我对cubism的所做的解释不是言语,而是个动作;他把头左晃晃,右晃晃,然后说:“Cubism是也。”我一时“悟”了此间的时、空涵义,心中大喜。那是一九七九年的一个早晨,在原老中央大学,中大院的一楼,建筑系资料室内。过后我把这件事讲给在北京的林乐义先生听,他高兴地直夸童先生,说我运气好。去年我又在闲谈中告诉了张锦秋先生,她觉得挺有意思,并劝我写出来告诉大家。
见杨廷宝先生是我在老师面前最尴尬的一次体验。当时,我由潘谷西先生带领,去景德镇做陶瓷博物馆方案。我随潘先生去是学古建筑的。回校后,一时高兴,仗着自己能弄两笔山水,便将方案的某些部份用“意笔”画了出来,潘先生很谦虚,说是请杨老来看看。杨老请到之后,良久,观而不语,末了,冒出一句话来:“画画墙上挂挂可以,光好看造不出来可不行。”我顿时一下子明白自己做事冒失了。古建筑构造不清,画这种东西乃是“花拳绣腿”,几何无知而胆大!事隔多年,我每每想到杨先生的批评,心里就发毛。我也时不时用他的话告诫自己与我的同仁和我今天的学生。
我在南京我最后一位恩师是刘光华先生,刘先生出身于美国Penn-sylvania大学,是贝聿铭的同学。刘先觉先生出国后他是我的硕士论文的导师,也是我答辩的主持人,这是位乐天派人,他对我宽容我是心里有数的。他从未正面批评过我,大概是念我没功劳也有苦劳,勉为其难做那个“现代艺术”论文不易。事后,他还与前来审阅我论文的罗小未先生商量,打算叫我继续做下去跟他写出“博士”论文。可惜,先生因无法解释的原因,拂袖而去,定居到了美国,我亦同时失去了在他引导下继续深造的机会。在先生的教诲中我记得最牢的一句话是“你要研究西方史,英语不好不行。”事隔十年,去年刘先生回南京省亲,我那位好心的师兄朱光亚专程找到刘先生,安慰先生道:“吴家骅记得您,他后来去了英国,写完了博士论文。”可惜这次我一直没机会再见到刘先生,跟他说几句体己的话……
我现在已近知天命的年纪了,步入老年之际,也更明白人终究是要死的绝对真理。人一旦死了,留下的只是一片寂静。这时,没有尊卑、贵贱,只有一个绝对的平等,求知只是那些自称“知识分子”的人走向死亡过程中的乐事,犹如儿童的戏耍。其间,也许有规律、有方法。学子的悟性固然重要,好老师的作用亦不可忽视。
我说自己运气好,是指我遇到了良师。他们都是一些“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的真人。虽说,他们去的去了,走的走了。他们都给我留下了对人生的理解:“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