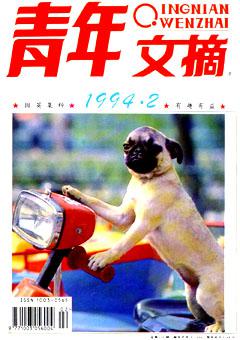一份电报
青 闫
邮递员在罗莎·桑罗瓦太太的房前下了自行车,走上前轻轻敲了敲门。门不久便开了,但开门的动作却不慌不忙,从从容容。对邮递员荷默来说,那墨西哥女人长得很美。看得出她一生都在忍耐,现在也是这样,她的脸上挂着温柔圣洁的微笑。她端详了一下荷默的脸问道:“你送电报来了?”
这话似乎问得很蹊跷,因为荷默的工作就是送电报。尽管如此,他还是感到自己做错了什么,似乎该对发生的一切负责,他很想直截了当地说:“我只是一个邮递员,桑多瓦尔太太,很对不起给你送这样一份电报,这就是我的工作啊。”但他很难说出口。
“谁的电报?”墨西哥女人问。
“G大街1129号罗莎·桑多瓦尔太太”,荷默说。他将电报递给那女人,但她并没有去接。
“您是桑多瓦尔太太吗?”荷默问。
“请”,那女人说。“请进来,我不会英语,我是墨西哥人,电报上说什么?”
“桑多瓦尔太太,”邮递员说:“电报上说……”
但那女人却打断了他的话:“你必须打开电报,给我念一下,你还没打开哩。”
“是,太太。”荷默毕恭毕敬地说。
他颤抖着打开电报。那女人弯下腰拣起被撕破的封皮,尽力抚平:“谁寄的电报?是我的儿子胡安·多明戈吗?”“不是,太太,”荷默喃喃地说。“电报是陆军部寄的。”
“陆军部”?“桑多瓦尔太太”,荷默如讲一个难堪的话题,快速说道:“您的儿子阵亡了。也许这是一个错误,每个人都会出错的,桑多瓦尔太太,也许不是您的儿子,或许是别人的,电报上说是胡安·多明戈,也许是电报报错了。”
“噢,别害怕”,那女人说。“进来吧,我给你拿糖果。”她拉住他的胳膊,走进屋中央的桌边,让他坐下。“男孩们都喜欢吃糖果。”她说:“我去给你拿糖果。”她走进另一个房间,转眼之间就端来一个旧巧克力糖盒。她打开糖盒说:“给,吃糖,男孩们都喜欢吃糖的。”荷默挑出一块糖,放在嘴里嚼起来。
“你不会给我送坏电报,”她说。“你是一个好孩子,活像小时候的胡安。来,再吃一块。”她又让他拿了块糖。
“这是我们自己的糖果,”她说。“我是特意为胡安·多明戈做好等他回家吃的。现在,你吃吧,你也是我的孩子。”说着她突然抽泣起来。
荷默想站起来跑走,但他知道他得留下来,他甚至认为他的余生也许会呆在这儿。如果那女人请他做她的儿子的话,他是不会拒绝的,因为他知道该怎么办。他站起来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道:“我能干什么呢?我到底能干什么呢?我只是一个邮递员啊。”
(徐明、李守钰摘自《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