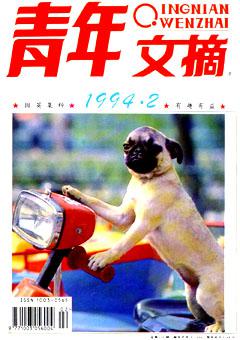孤独的人头
张晓然
在一则可怕的故事中,几个居心叵测的医生把活人的脑袋割下来,放进注有他们发明的药水容器中,使之存活。几十年后,这个脑袋还能思维、发音、观望……
如果这颗脑袋的确具有活力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推测一番它的生存形式。
它圆睁双眼,在淡褐色的药液中炯炯有神盯着玻璃瓶外的世界,首先,我能肯定它没有食欲。因为它没有肉体的负累。也就没有常人那强健的、无间断的消化功能,所以它对物质不会有渴望和贪念。你在它面前摆上美味佳肴、金银万两,它都无动于衷。
其次,我认为这颗单独的脑袋没有性欲。它的头颅以下部分所有的器官都丧失了,自然没有性意识存在。如果有美女在它面前一丝不挂,它也绝不会产生淫荡的想法,而只能把胴体当作一件绝妙的物体来欣赏或者品味,客观地说,它能够进入最纯粹的审美境界。
另外,我觉得它最富品格的是它已摆脱了人际是非,不必扭曲自己的人性。虽然,这枚人头已被粗暴地割去了与之关联的肉身,但它因祸得福,终于能够保全思想的自由和贞节。它无求仕途,所以不必卑躬屈膝,它断念功利,所以不用去孜孜以求,它既然无身,也就根本不需为身外之物而处心积虑。
所有这些,都使它活得比有身体的人潇洒得多、轻松得多。但是,这具头颅也有它无法比拟的疲累一面。生命是一种运转,它去除了体能性的运转,但保存了头脑思想的运转,它成天不停地思维运作,因而头脑非常沉重。在迢迢长夜,它思索黑暗对人类的影响;晨曦微露,它又考虑光明与大地的关系;婴儿降生,它琢磨生命的涵义;男女相爱,它又无尽地沉思情感的哲学伦理。政治的奥秘,经济的荣衰,文化的宽泛,它都绞尽脑汁地去归纳、分类、剖析、批判、辨别,从而得出相对的结论……这些,既构成了它存在的固有形式,也成为了它存在的全部内容,单调而乏味。
突然有一天,罪恶的医生被揭露,人们要来救活这颗脑袋。善良的使者给它安上最珍贵的躯体和四脚,还输给它汩汩流淌的血液,可是,孤独的脑袋却含着智慧的微笑,死了。
它死了。由此我悟到,在任何时代,灵与肉都是不可分割的。
(崔砥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