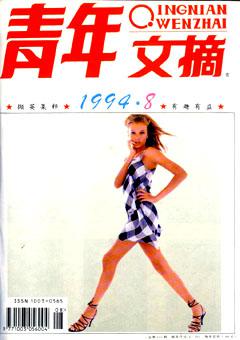陈纳德将军和我
陈香梅
生命像一盏灯,像一个谜,有时甚至像一个梦。我和他相识复相爱时,明灯相照,满室生春;我们婚后,几经忧患,几经巨变,许多时日过得扑朔迷离,生命似谜;后两年里,大半时光消磨在病院中,有时唯恐他已被死神夺去,此情此景,只有身历其境者,方能体验个中滋味。
1937年,陈纳德将军被邀来华参战时,我还在香港念书。直到1943年我在昆明加入中央通讯社工作时,我们才第一次见面。那时他是美国14航空队的司令官,我是中央通讯社的女记者,在一次记者招待会散后,陈将军走过来和我握手,并问姓名,我告诉了他,他大笑说:“原来就是你,你可知道你的父亲还托我照顾你呢?照我看来,你已很会照顾自己。不过,请不要忘记,我是你父亲的朋友,有什么我可以帮助的地方,尽管告诉我好了。”
在昆明的两三年当中,大家都为工作忙,我们见面也只是限于公事而已。有时我单独去看他,也是采访新闻。不过,在这段期间,我们渐渐地稔熟了,大家也偶尔谈及生活方面的小事情,说些笑话。那时陈将军有个秘书,会画漫画,他为我作速写,可是不太像,让陈将军看见,他说:“这张像片就送给我吧。”我说:“不好,太丑了,改天送你像样的。”时适有摄影记者在旁,马上为我们拍了一照,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一起照相,如今尚留着做纪念。
1945年夏,抗战结束前两月,陈将军因与美国国务院闹意见,反对他们的对华政策,毅然辞职返国。十四航空队举行欢送晚会,大家都希望和这位飞虎将军谈一两句惜别和祝福的话,因此整个晚上我们都没有机会在一起。10点已过,我准备走了,陈将军走过来说:“你不和我握手就准备走了吗?”我这个平时那么会说话的人,一时竟不知道怎样回答,同时又觉得四周的人都在注意我们,不易脸红的我竟然脸红了。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一瞬间,我们两人似乎都发现一种异样的情感在作怪,突然发现自己在热爱着对方,常常见面毫无感觉,一旦发现心底的深情时,我们竟要分别了!
抗战胜利后我也离开昆明,转到上海工作。这期间,日子只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地打发过去。圣诞前,我得到陈将军返华的消息,我想起了我们在众人面前说不出话的那种窘态,连到机场去接他的勇气都没有。晚间,他邀我吃晚餐,在座的还有前任美军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鲁克斯将军和几个朋友,他们对于他的来临都表示欢迎。席终已10点多了,我就想先告辞。陈将军说:“等一会儿客人走了,我送你回家好了。”于是我只得留下。客散后,陈将军说:“你坐一下好吗?”于是我坐下,大家又是好一阵的沉默。
我说:“你打算在上海住一个时期吗?”
他说:“不,我很快就要回美国去,不过我将再回来。在我离开之前,我想要求你一件事——我想要你答应我的求婚,那么明春我回来时,我们就可以结婚了。”他说这些话时似乎费了很大的气力,而我则更是不知应当怎样回答了。
记得当时我曾说道:“我们大家了解不深,怎可以顷刻之间就谈到结婚的问题呢?”
他说:“我很久以前就一直爱你,我不敢对你表示,因为我还有太太。如今我已获得恋爱的自由,我希望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做我的终身伴侣。”
圣诞节,是亲人团聚的日子,陈将军约我到家中度节,我没有答应。他那时和友人魏劳尔夫妇同住,我想到古人“亲极反端”的忏言,不想在这团圆的节日和他见面。他送给我的圣诞礼物是一瓶法国香水。盒子里面有一张卡片,写着“给我最亲爱的人”。我看见这行小字后,心绪飘然,如风吹落叶,不知所止。
新年过后,陈将军再度返美,约期一二月内归来。才相逢,又复忆相逢,别后我才知道我是多么地想念他。白天,我数着日子,计算着他的归程;晚上,我梦着他,从一个梦,又转到别一个梦,一点新愁,寸心万里。一个月后,他回来了。我被矛盾的心情支配着,我没有到机场去接他。我有点怕,我怕寂寞的情感。
晚上,他的电话来了。他说:“你生病了么?”我说:“我很好。”他说:“你为什么不到机场来接我呢?”我没有话好说了。他说:“我的车子马上来接你,我想见你。”没有等我回话,他的电话已经挂上了。我住的地方离他的住所,大概也有二三十分钟的路,然而在我看来竟是一刻如年,心中巴不得车子开快一点。入室,他起立相迎,两人握手,未通片语,但觉魂飞魄荡,不复更有此身,四目相疑,恍如隔世,一缕情丝,从此无法解脱了。
静夜里,灯影下,我们计划着婚期。那时我的父亲和继母刚自美国归来,他们当初不赞成我们的婚事,可是后来经过陈将军的一番表白,他们也无异议,只有一个条件,他们要带我到杭州的西子湖畔静思数天,归沪后再作决定。
正是初冬时分,西子湖畔游人不多,我对着山光水色,了无心绪,尽是离绪,尽是相思。三日后,陈将军来电促归,匆匆就道,抵沪之日,距圣诞节只二周,作嫁衣裳还未剪裁,而我们已把婚期定于12月21日举行,那是1947年。
在上海静安寺路有一家法国人开的服装店,名为“绿屋夫人”,我在那儿定制过几套晚装。圣诞前两周,我到“绿屋夫人”那儿去做一套新娘服装,老板娘寻根问底地要知道我和谁结婚,并说若我不告诉她,她无法为我把那袭嫁衣在12月20日前做好,于是我只好据实告诉她,我将与陈纳德将军结婚。
“噢,他原籍也是法国人。”老板娘兴奋得不得了,量身段时几次用针刺痛了我的皮肤,若说她是第一个预知我与陈纳德将军婚事的人,也不算言过其实。
新婚之日,丈夫订了一个以千朵玫瑰做的花钟,象征着挚爱的永恒。当他把一枚戒指戴在我的无名指上时,我的手指有点发抖。溢满的幸福,常使我有点惶恐,为的是怕乐极生悲。
我们在婚礼在上海虹桥路华美村举行,除了证婚的基督教牧师以外,有我的双亲,做女嫔相的姐姐,做男傧相的詹德尔医生,叶公超,美国驻沪领事,空运队的副经理魏劳尔夫妇,陈将军的秘书长舒伯炎夫妇,霍德华系报纸的远东代表方士华夫妇,泰莱夫妇等。茶后,9时晚餐,酒醒人散,寒意正深,围炉并坐,情深如许。但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得永恒相守,不羡天上神仙矣。
我们初婚时,卜居虹桥路华美村。该处境地清幽,无市声之扰,屋后有园地,植瓜蔬、种花果。三春花放,九月蝉鸣,自有一番幽趣。我们常在清晨起来,到楼东看日出;晚间无事,在月影下散步;有时邀二三密友到家里玩玩纸牌,声声竟乐,逸兴横飞。
还记得初婚后的圣诞早晨,我和丈夫一同到外滩的办公室上班,记得那天连开电梯的工友也放了假,于是我们一口气跑上七层楼。办公室内寂寞无人,只有他和我两人上气不接下气地相对大笑。我煮好了浓咖啡,陪他工作了一个上午。从此我们为他的办公厅取名七重天,这是我们两人的秘密。
丈夫虽勤俭,但生性豪爽,一点也不吝啬。那时我们住在上海,政府明令所有市民一律要把黄金美钞送到银行去换金圆券,丈夫那时不但以身作则,每一个月领到薪水即着秘书把美钞换作金圆券,存入银行,他还劝所有外籍职员一律服从政府的命令——自大陆来的人一定还没有忘记金圆券的风波。
太阳是咸的,月亮是甜的;太阳是一曲雄壮的军乐,月亮是一首诗意的短曲;太阳高高地照遍大地,月亮静静地影满人间,这是西方的美与东方的美不同之点。然而,我们既爱太阳,也爱月亮。
我们分别来自西方和东方,起初,我们仅是被一道围墙阻隔着,我们非常陌生;可是当我们走出围墙以外之时,我们发现我们呼吸着同一的空气,我们原来就是生活在同一地球的人,虽然萍水相逢,可是相知极深。
婚后,我们有两个女孩子,大小只相差一岁多一点。丈夫对于孩子无尽的钟爱,他曾对我说:“20年后,30年后,孩子将代我来做你的好伴……”
1958年,丈夫陈纳德将军因肺癌病逝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纽奥连市。我们婚后不过十度寒暑,生活有说不完的使人落泪的使人快意的回忆。只恨春光短暂,曾几何时,春残、月落、人杳!
(朱霞摘自《海外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