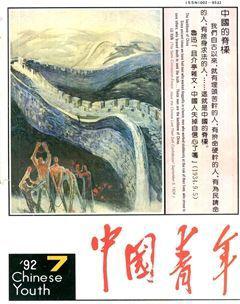左右为难的青年楷模
改革开放给我们这一代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和前景,也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顿和迷惑。我们在进取开拓的同时,也步入了艰难的思索,重新审视社会、审视自身。
本文记录的是一群青年佼佼者的心路历程。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成绩卓著,辛勤劳作,被授予“新长征突击手”、“劳动模范”等光荣称号,是党团组织树立的青年楷模。也许正是这些特殊身份,使他们在探索的道路上走得更艰难、更痛苦。
如果你仔细倾听,你会听到他们的灵魂深处有什么东西在嘎嘎作响。那是现代意识和传统观念在碰撞,新老体制在交锋。
良心,是花环还是锁链?
(她长得十分秀美文静。她是中国西部第一个特级美容师,有一双灵巧的手,创造美的手。谁都不会想到,这个看似柔弱的姑娘竟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包袱。)
在领导心目中,我一直是个埋头苦干、顺从听话的“好孩子”。20几岁就成为本市的特级美容师,很不错。在15届亚洲发型化妆大赛中国赛区中我不负重望,获得第一名。同行们当时很吃惊,西南山城怎么会冒出这么个女状元。一时间我被誉为“明星”,奖励、表彰、上报纸、授称号等等接踵而来。当然,我对此看得很淡。
我所在的门市部是个老字号的国营企业,由于管理不善,一直处于微利状态。80年代末,主管部门下决心投资10多万搞起了山城第一家美容服务。那时我熬更守夜,经常干到凌晨一两点钟,从来也不计较别的。我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只要我能在这小小的美容间里给山城增添美和欢乐,我就心满意足了。别人曾对我说,你有这么好的技术,干吗不去干个体挣大钱?我说,为人民服务嘛,什么钱不钱的。
可是1989年我确实离开了国营单位,不得不去干个体。那是我有生以来最痛苦的日日夜夜。因为领导不理解我,我实在干不下去了,便负气出走,去深圳自费深造美容专业,然后回到山城开起个体美容店。我每天给顾客纹眉、纹眼、美发,充分发挥了我的专长,干得轻松愉快,随随便便一干就要顶在国营一个月的收入。你想想,光纹一双眼就可以挣500多块啊。
钱赚得多起来,我的心却渐渐不安了。我想,我是国家培养的,老前辈们手把手教我拿刀型剪,我成功之后党团组织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我只顾自己赚钱对不起良心。虽说国家政策鼓励个体经营,我个人开美容院不令收入丰厚,而且没有人指手画脚,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可是我总觉得干个体有很浓的自私自利的味道,我毕竟是个受过党团组织教育和表彰的青年啊。
我终于下决心回到国营单位。我仍然像以前那样努力工作,并着手带徒弟传授技艺。谁知我干过一段个体后,对国营企业的有些管理办法越来越看不惯。比方说,分配不公,平均主义,技术好的贡献大的和技术差的贡献小的收入相差无几。我提出来,领导就说我不听话,觉悟低。我很委屈。我觉得这不是几块钱的事,而是对一个人能力的评价问题。要是图挣钱,我到这来干吗?我的心很矛盾,一方面后悔不该回国营单位,一方面又感到我的良心得到了宽慰。
我盼望改革。可是改革的春风好像被三峡挡住了,刮到我们这儿来零零星星的不解渴。比方说,我们的上级主管部门为了搞活企业,准备松绑希望把租赁承包落实到各门市部,但分公司不愿意放弃盈利企业的管理权,这样,我所在的单位只有责任和义务,没有权利,企业不死不活的,大家的心劲儿不高,我感到窒息。我失望了,又一次想走。
走也不那么容易。良心不让我那样做。窝在单位里不能痛痛快快地发挥自己,干个体又觉得自己不够高尚,我真是左右为难。但愿有一天我能大彻大悟。
单靠觉悟还能维持多久?
(她是万里长江上唯一的女船长,曾被收入《世界名人录》。10多年来,她驾船平安驶过近百万公里航程,人们称她是“平安天使”。报刊上曾多次报道她叱咤风云的事迹,却很少有人知道她心中的苦闷。)
干我这行的要用女人的心,借男人的胆。
当船长的确是苦差事,夏天热得头昏脑涨,冬天雨雪纷飞,为了不挡视线,必须打开挡风玻璃,任凭冷风吹得眉毛结起冰。夜深人静时,为了能看到长江上漂浮的导航灯,驾驶室里不能有光亮,你得全神贯注盯着前方,不停地呼喊号令,一喊就是4个小时。我越开船心越虚,真不知什么时候会飞来横祸。不怕你见笑,我这个“先进分子”有时也挺虔诚地给何仙姑和观音供奉圣果,祈求神灵保佑。
我所在的船队有成百员工,可乘坐1400多旅客。春运时“川军”出川,农民挤满了厕所、过道,一下子超载一倍多,我每次驾船,脑子里的神经都要绷断,这上千人的性命就在我手上啊。
过去我头脑很单纯,党叫干啥就干啥,从不讨价还价,大家都一样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嘛。可是我现在头脑越来越乱,越来越复杂。因为很多事迫使你不得不去想。
这几年来,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我们的船上就是一个小社会,你能看到许多令人费解的事。我经常看到一些教授含辛茹苦教了一辈子书,外出只能坐三等舱,一块干馒头当顿饭,心里很难过。而那些个体户野经理们却风光得很,坐二等舱还要包饭,有的人竟公然向我提要求,问我有没有小姐服务,真叫人气愤。
现在我们航运业的情况令人担忧。第一线的船员很苦,待遇低,因此许多青年不愿学技术,水手不愿当舵工,因为学技术就意味着要多担风险多受累,报酬也增加不了多少。有的人正道挣不来钱,就走歪门邪道。比方利用职权之便,从甲地到乙地倒腾香烟,或是“代黄鱼”(将自己的工作铺位卖给乘客,自己随便蹲在哪个角落)。过去,我对这种损公肥私的行为处理得很凶,抓住一件处理一件,可是我的手慢慢软了,有时干脆睁只眼闭只眼。我的内心很矛盾。不处理吧,是我这个当船长的失职;处理吧,现在物价这样贵,船员结婚生孩子买房子都要钱,不这么干又怎么办呢?我只能是洁身自好,管住自己。在大家积极性普遍不高的情况下,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单靠“先进人物”的觉悟和奉献精神,又能维持多久呢?
有时我也胡思乱想。我想,像我这样的船长,要是为个体户、集体企业走一趟水,就可以顶一年的收入,我干吗苦苦耗在这里呢?很多人这样干了,毫无顾忌,可是我就不行,因为我头上有一顶顶“先进”和“劳模”的桂冠,各种红本本得了不知多少。有的人说,你这个“先进”是用钱买的,我问“何以见得”,他们说,你要是去挣大钱,不就当不了先进了吗?我听了只是苦笑。
我觉得我付出的辛劳和得到的报酬是不相称的。可是我不愿提出来。因为一个人伸手向组织要这要那,多少有点不光彩。别人特别是领导肯定会大吃一惊,啊,你这样的“先进”也斤斤计较,还讲不讲“奉献”了?
不过,有朝一日我提出这个问题遭到批评的话,我一定会这样回敬他:社会主义最讲公平,第一线的船工累死累活,要养活整个航运系统数不清的机构和闲人,这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吗?
做人,还要不要认真?
(他1米8的个头,当过足球队守门员,现在是一名律师。几年来他忠于职守,打了几百场官司,被团市委评选为本市十大杰出青年之一。)
我可以说是党团组织一手培养的,属于“根红苗正”的那一类,一路顺风,28岁就当了领导,据说是市级机关最年轻的处长。后来我怀着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愿望,当了一名律师。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就应该认真依法办事。党和政府是这样教育我们的,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做起来太难太难了。
有时是无法可依。比如去年打了我国第一桩雕塑创作权的案子,我和同事当了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为了打官司,我们跑了文化部、全国美协等单位,找不到一个关于雕像创作权的规范。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我们根据法律理论和事实打赢了官司。令人可气可笑的是,法院为这场官司跑了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耗费了上万元,而最后败诉方只赔偿了几十元。
更令人恼火的是有法不依。某个领导打了招呼,干预案件审理,说一句“这事就这么定了”,依法办事就要大打折扣。我经常为此抗争,有的同志就劝我说,中国现在就是这样,太认真了就行不通。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认真让我付出了代价。我曾为一桩重大经济案的当事人打官司。案子很复杂,牵涉的人很多,上上下下都有。我决心要把案子搞个水落石出。谁知说客频频登门,劝我装糊涂,让我听上级领导的话,否则会影响我的前途。我不听这一套,拿出一股不搞清楚誓不罢休的劲头,结果传言四起,说我接受了当事人的好处,否则不会那么卖力,我有口难辩,心力交瘁。
最近领导又一次批评我,说我“不听话”,当了先进就骄傲了。领导的批评对我很有触动,我想,我应该好好调整我自己了。也许,我没有必要那样认真?
如今,“困惑”似乎很时髦,有的人遇到问题连想都没想,张口闭口就是“困惑”,以示新潮。本文的主人公并非如此。他们渴望追赶时代的脚步,更大限度地展示自己,发挥自己,同时又不愿意丢弃传统中优良的东西,为此他们真诚地困惑着,犹豫着,彷徨着。
真实的困惑是有价值的,它往往是我们走向新生活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