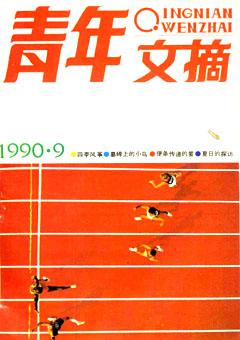四季风筝
1990-01-01 09:08蒋祖烜
青年文摘·上半月 1990年9期
蒋祖烜
记不清什么缘由,那个仲夏的中午,我要横过绿茵的广场。
一个浓黑影子跳入视角,蓦地抬头,一位老人和他手中的白线,远远的线两端,是一只蝴蝶风筝。那老人全神贯注,一忽疾猛一忽迟缓的东南风,戏弄得风筝左摆右倾,上翻下跃。显然,驾驭不易,滚圆的汗粒摔落下来,但蓝莹莹的天色里,终有了优雅的鸢影。
我怔住了,好一阵才恭敬地问:“夏天也能放风筝?”
“只要放,四季都能飞!”他爽朗的声调里露出不容置疑的自信。那爽朗,吹皱了我快要冻结的心湖。
三年了,那情、那景仍分明地映在我的心上,那是我最滞重的日子。无数的失意,我以为,没有了柔煦的春风就没有了飞翔,也没有了舒展的长空。
老人与风筝,示我哲意?
我爱风筝,童稚的记忆里,翻飞的风筝占了一半以上。
接着,知道只有春天能放风筝;
接着,知道只有孩子才放风筝。
等一切都知道以后,却只能站在讲台上评析《风筝的故事》,从报纸上读潍坊的“风筝节”,或远远地暗慕高楼平顶及小河沙滩上那些忘我的孩子了。
风筝,划出了天地间的距离。
今春末,我困居在桃花仑的一间小屋内,无奈地等待着康复。医嘱:不宜动,不宜读,不宜油荤,不宜悲喜。天光不晓,友朋不来。我腿杆蜡软,翅膀缒铅,潜意识里满是叹息,我走不动了,我飞不起了!
一封远方的来信突然摆到我的病床边,信封里只有一张纪念卡,卡片上是几只跃动的风筝,背面有几行字:
“飞的翅膀,
能占领任何季节!”
我3年前的诗句。
不是吗,虽然夏风强劲,秋风轻淡,冬风凛冽,远不及春风那般温柔,但毕竟是风。有风,就必有风筝的翱翔!
心就这样又被撩拨得热乱起来。好吧!就算与春风永别了,还有夏,有秋冬,风生水起,仍有放飞的日子。
我怀想那个夏日,那位老人,那只不择季节的自由轻扬的鸢尾鸟。我要去重温那炎热的风。
(何永生摘自《经济日报》)
猜你喜欢
东坡赤壁诗词(2022年2期)2022-04-15
小雪花·小学生快乐作文(2019年8期)2019-10-07
课外生活(小学1-3年级)(2019年6期)2019-07-19
诗潮(2018年5期)2018-08-20
湖海·文学版(2017年4期)2018-01-09
足球周刊(2016年16期)2016-10-20
小天使·一年级语数英综合(2015年2期)2015-01-14
幼儿时代·故事妈妈(2004年4期)2004-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