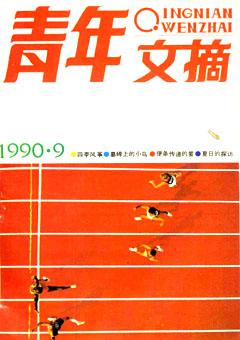美丽的邻居
泰戈尔 兰 天 绍 康
我对隔壁那位年轻的寡妇,怀有一份深深的爱慕之情。我把这份纯洁的感情埋在心底,就连我最亲密的朋友——纳宾,也不知道我的心事。
可是,爱的激情,就象山上的溪流,不能停留,它要找到一个缺口倾泻而下。我开始写诗了。
真是巧得很,我的朋友,纳宾,此时也如痴如狂地作起诗来。他的诗体很旧,内容却永远是新的。无疑,那诗都是为心上人做的。我问他:“老朋友,她是谁呀?”
他笑着说:“这个连我也还不知道哩!”
说真的,帮纳宾改诗倒使我感到十分痛快。我象母鸡替鸭子孵蛋一样,把按捺在心中的激情一倾而出,他那几首抑扬的诗,经我大胆地修改,变得更加情真意切了。
为此,纳宾惊诧地说:“这正是我想说而又表达不出来的呀!”
我说过,我对那女人怀有的是一份深深的爱慕。
有时,纳宾会头脑清醒地说:“这诗是你作的,写上你的名字拿去发表吧。”
我说:“哪里的话!我只是随便改改罢了。”
我不否认,我常常象天文学家观察天空一样,呆呆地望着隔壁的窗户。
终于有一天,我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的下午,我看见那美丽的邻居站在那里仰望天空,那乌黑发亮的眼睛显得忧虑不安。那是一双渴望的眼睛啊!那淡淡的愁思,就象一只归心似箭的鸟儿,然而它的归宿不在天上,却在心间。
看着她那心事重重的神态,我几乎不能自制。我于是决定做宣传工作,号召破除寡妇不能再嫁的旧习俗。
纳宾开始和我争论了。他说:“寡妇守节意味着一种纯洁的美德,如果寡妇再嫁,不就是伤风败俗了吗?”
我没好气地说:“可你要知道,寡妇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她们也有痛苦,有欲望。”
我知道纳宾有时顽固得象头牛,要说服他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可这次却出乎意料,他若有所思地叹了口气,然后默默地点了点头,赞同了我的意见。
大约一周过去了,纳宾对我说,如果我肯帮助他,他愿意首先和一位寡妇结婚。
我真是高兴极了,热情地拥抱了他,并说无论他结婚要多少钱我都支持他。于是他把恋爱的浪漫史告诉了我。
我这才知道,一段时间来,他暗暗地爱上了一位寡妇。发表纳宾的诗——倒不如说是我的诗的那几本杂志居然传到了那位寡妇手里,是那几首小诗在起作用。
我说:“告诉我她是谁?不要把我看作情敌,我发誓,我决不给她写诗。”
“你胡说些什么呀?”纳宾说,“我又不是怕和你竞争。我冒这么大的风险真不容易,好在现在一切都好了。告诉你吧,她住在19号,就是你的邻居。”
如果说我的心是铁锅炉,也要被这突如其来的“铁水”溶化。我说:“这么说,这是归功于那几首小诗了?”
纳宾说:“不错,这你也知道,我的诗做得并不错嘛!”
我暗暗地咀咒,可是,我咀咒谁呢?咒他?咒自己?我自己也不知道!
(曾广岩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