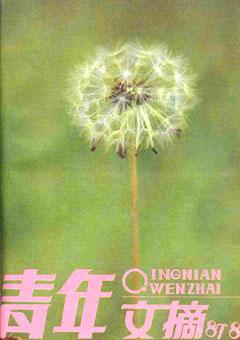候鸟飞来了
(苏)弗·利金
无论生活多么维艰,只要热心播种,辛勤耕耘,秋天里,当候鸟飞来的时候,必会有幸福的收获。
护士拉丽莎·瓦西里耶夫娜在战争中几乎失去了听觉,和她曾经相爱过的男朋友死去了,不久,患心脏病的母亲也去世了。现在,就只剩下她孤零零一个人,这是够令人心痛的。她才三十来岁,这种形影相吊的生活使得她心灰意懒了。在这种情绪之中,随之而来的是容颜衰老,她还觉得,精神上也衰老了,周围世界变得越来越荒僻和遥远。
她楼上住着一个叫柳德米拉·彼得罗夫娜的校对员,在一个出版社连续工作了几十年。柳德米拉·彼得罗夫娜是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经常把活带回来干。有一次她匆匆忙忙、兴致勃勃地来找拉丽莎·瓦西里耶夫娜,声音洪亮有力地冲着她耳朵嚷了一通:
“您呀,亲爱的,看您那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愿意帮我看校样吗……您念稿子,我看校样,这样我改起来就快得多,您也有收入了。”
“我倒是挺乐意,”拉丽莎·瓦西里耶夫娜大声说,“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胜任。”
“肯定能胜任……这事包在我身上了,”沃尔任娜很有把握地说。“您自己先看一遍,明天咱俩就着手工作。”
她把校样留下来,于是拉丽莎·瓦西里耶夫娜开始读这部长篇小说。
“您千万别着急,亲爱的……读的时候得不慌不忙。”第二天她们坐下来校对时,沃尔任娜说。
拉丽莎·瓦西里耶夫娜开始用低沉而平静的声音读起来,沃尔任娜偶尔叫她停一停,在校样上进行修改。
“您瞧,”她相当满意地说,“您瞧,咱俩合作得多好。文学可是个好东西,它能美化一个人的生活,启迪人的思想,说得更确切些吧,再也找不到比书更好的朋友了。”
她们校对了那个长篇,不久沃尔任娜又带回另一份校样。同时拉丽莎·瓦西里耶夫娜还背着沃尔任娜偷偷地买了一本俄语详解辞典,因为经常会碰到一些她不认识的字。
“一个人的生活之所以丰富,在于他能行善,”沃尔任娜大声地对着她的耳朵说,“这种机会是无穷无尽的。而只要做了一件善事,跟着就会有另一件,此情此景和候鸟飞来毫无二致:只要看见头一只鸟,跟着就会发现一大群。”
“谢谢您,柳德米拉·彼得罗夫娜,”拉丽莎·瓦西里耶夫娜小声说,“能给您帮忙,我感到很高兴。”
如今拉丽莎·瓦西里耶夫娜房间里经常摆着一摞摞校样。她还慢慢学会了使用一些有时象楔形文字的校对符号,还经常亲自在页边上标出来,好让沃尔任娜注意到错误地方。
有一次,她正拿着取来的校样,在楼梯上碰见了熟悉的邻居——俄语教师尼古拉耶维奇·乌斯季耶夫。乌斯季耶夫一年前丧偶,如今过着独身生活
“我早就想来找您了,拉丽莎·瓦西里耶夫娜,”他说,“但总下不了决心。是不是您上我家来呢……得劳您的驾了。我有件事想找您商量。”
“好吧,”她说,“您什么时候方便呢?”
他们约定第二天六点以后,等乌斯季耶夫下班回家,她去找他。
他那套小小的两居室房间乱七八糟,显然是没有工夫收拾,厨房的煤气灶上放着几只没有刷洗的锅。
“拉丽莎·瓦西里耶夫娜,我不知道您对这会有什么看法,”乌斯季耶夫窘促地说。“不过,也许您能抽出些时间来帮我料理一下家务吧……我太忙了,除了在学校上课,还在夜校讲授文学。我的要求就是:您自己买菜时,也捎上我的一份,做饭的时候也分一份给我。这就给我帮了大忙了……当然,还得看您方不方便。我的嘴并不刁,吃什么都没意见。条件是这样的:为我们俩买东西的钱都由我付,您就只出力,而且花多少钱由您说了算。”
他一直觉得很难为情,时不时将头发弄得乱七八糟。
“您说什么呀,”拉丽莎·瓦西里耶夫娜说,“我看得出来,您一个人生活有困难……您一会儿跑牛奶店,一会儿跑面包铺,您哪里还能有时间!老实说吧,我有好几次也想向您提:我自己买东西的时候,也给您捎上一份,这对我不费什么力。”
“这可太好了,”乌斯季耶夫吁了一口气,“我也就是因为您这个人心肠好,所以才敢来求您。”
如今拉丽莎·瓦西里耶夫娜的生活中又增加了一项义务。她已不再象一般为自己买东西那么匆匆忙忙、不挑不拣了。总要想方设法去找一些好吃的东西,有时候还跑到集市上去,等岛斯季耶夫回到家,他的煤气灶上已经摆好做好的饭菜,只需热热就可以吃了。
可是有一次,乌斯季耶夫突然自己上门去找拉丽莎·瓦西里耶夫娜。
“对不起,”他挺严肃地说。“您对我的关心我当然很感动,但我请您再也别这样了,否则我就只好不请您帮忙了。”
“这是怎么回事?”拉丽莎·瓦西里耶夫娜顿时警觉起来。“我做了些什么呢?”
“您听我说,我只不过是以同志的态度求您帮我料理一些家务,但绝不要求您为我洗衣服。”
“难道我洗得不干净?”她问。
“不是的……我只求您以后可别再干这种事了。”
“为什么呢?当然喽,如果我要感到困难,或者觉得讨厌,我就不会这么干了。”
“您这人真好,”乌斯季耶夫说。然而,拉丽莎·瓦西里耶夫娜没听见这句话,他说得声音轻极了,也可能他这是说给自己听的。
“您知道吧,”柳德米拉·彼得罗夫娜有一次大声地说,“拉丽莎,文学作品里经常谈到善与美……如果尼古拉维奇·乌斯季耶夫能看出您是多么难得的一个人,,您的心有多么好,难道这就不是善与美吗?!你们两人也就不会都那么形影相吊了。”
“您怎么啦,”拉丽莎·瓦西里耶夫娜惊惶地说,“您在说什么呀,柳德米拉·彼得罗夫娜,我不过是真心实意待他,别的什么想法也没有。您干吗说这种话呀!”
但柳德米拉·彼得罗夫娜搂住了她,老太太个子矮一些,只见她那双闪闪发光的圆眼睛从下往上瞧,拉丽莎·瓦西里耶夫娜两手捧住她的脑袋,俯下头来吻了吻两边脸颊。
“您什么也不明白,”她只这么说。“一个女人家应该注意打扮自己,可看您梳的是什么头啊?”
拉丽莎·瓦西里耶夫娜来到理发馆整容了一番,使她看上去年轻多了,那脸也舒展开了……不管怎么说吧,已经教会她看校样的柳德米拉·彼得罗夫娜就是她生活中的善与美,还有那位郁郁寡欢、拘谨腼腆的乌斯季耶夫也是善,而且不仅仅是善,可能还超过善良的感情,不过这件事不必去想,让它珍藏在心底好了,永远也不要让人们知道。
已经是5月末,黄昏来得很晚,而且这甚至不是什么黄昏,不过是一种缓缓地向窗口贴近的烟霭,是那么温柔可爱。当拉丽莎·瓦西里耶夫娜把校样给沃尔任娜送去的时候,在楼梯上碰见了乌斯季耶夫。不过她觉得,他好象既不打算出去,也不是从哪儿回来,而是就这么站在楼梯上,象是在等人。
“瞧,已经是夏天了,”当她上到他站着的那层楼梯平台,他说。“再过一个月我就放假了……到海边去,到波罗的海或白海去。”
“您是得休息休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她说。“因为您连晚上也没闲着……”
她本来想问问他晚饭做得好吃不好吃,他却自己先说了:
“拉丽莎。瓦西里耶夫娜,您可是把我惯坏了……惯得我不知怎么样生活才好啦。对您说了吧,当一个人看到别人的心肠是那么好,他可能会因为担心失去它而感到恐惧。”
“您最好还是到波罗的海去吧,”她没把话听完,就说道。“还是温暖的气候好,我们这里冬天长。”
她向楼上走去,他却还站在楼梯平台上。柳德米拉·彼得罗夫娜给她开门,接过她手中的校样。
“好哇,”她翻着一张张校样说,“您已经学会标校对符号了,错句和错字也都找到很对……现在您还得学会另一门艺术。”
拉丽莎·瓦西里耶夫娜询问地看了她一眼。
“学会在生活中也能找到失误和不妥之处,而且尽可能纠正它们。”
她这两句耐人寻味的话说得很清楚,也许她知道尼古拉耶维奇·乌斯季耶夫还站在楼梯平台上,也许她已经知道了任何人也不该知道的事。
“啊,亲爱的,生活有多么好呀,”老太太说,“还没有一个作家能把这美好的东西好好地表现出来。”
拉丽莎·瓦西里耶夫娜拿了后面一部分校样,带回自己家去。乌斯季耶夫还站在昏暗的楼梯平台上,她对此感到不可思议。
“看来,还是您说得对,”他说,“还是您说得对……波罗的海比白海还是要暖和些。”
就连拉丽莎·瓦西里耶夫娜本人也不明白,为什么她没把校样带回家,而是随乌斯季耶夫一道下了楼梯,然后两人一同在5月黄昏中朝远处走去。不过最使她感到不可思议的还是:她什么都听见了。整个世界以及它的气味和色彩她都感觉到了;现在要让她听到、感觉到它们,已不再需要那些气味和色彩使劲地喊了。(汀新缩写)
(插图,辛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