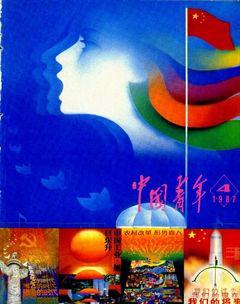不仅仅是为生存
蒋丰
数以万计的保姆大军走入都市的千家万户。有人指出:她们是中国的“阿信”。
由此,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而北京的保姆群,又以其数量之多而更加令人瞩目。
请看北京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的一组数据:
1985年,北京市区日平均流动人口总量为897500人。这就是说,在北京城区,每6个人当中就有一人是流动人口。若从流动人口在京所从事的活动看,当保姆的占3.24%。
再请看北京市三八家庭服务总公司提供的一组数据:公司自1983年底创办以来,已为用户介绍了16000多位保姆;各区的家务服务公司,已为用户介绍了12000多位保
姆;靠乡里关系“滚雪球”进京的保姆约有30000人。据抽样估计,北京市需保姆80000人,即每20户家中就有一户需要保姆。目前只有500000从业者,缺额较大。
应该说,北京的保姆群是中国保姆群的缩影。
敏于观察中国的外国人士注意到了中国的保姆问题,他们的疑虑是:
生活并不富裕的中国一般干部、科技人员,怎么会雇得起保姆?
保姆群体的出现是不是中国农村经济承包责任制引起的两极分化的后果?
时值上学年龄便远涉他乡受雇于人的小保姆,是否因为家境清苦、艰难?
国内社会各界有关人士也注意到了城市的保姆问题,他们的焦虑是:
由于雇用保姆而造成经济拮据的年轻夫妇,势必使自己正常生活遭到冲击、影响。怎么办?
由于主、雇之间供需关系的紧张,雇用保姆的费用与日俱增。如此恶性循环下去,怎么办?
由于年轻保姆在一对年轻夫妇家庭中的出现,造成主与雇之间的“第三者”现象。家庭结构不稳定,致使社会矛盾增加。怎么办?
……
众多的疑虑和焦虑,众多的困惑和问题。
她们为什么出走?
——北京建国门“保姆市场”采访手记北京的保姆市场分为有组织的和自发聚集的两个部分。
有组织的保姆市场系指北京市妇联主管的三八家务服务总公司和各区妇联及街道办事处主管的30多家家务服务公司。他们通过妇联在全国各地的网络,从广大农村招聘保姆。来者需有地方介绍信,用户需有个人身分证和单位证明,双方洽谈妥当,要在合同书上签字。人们都说,“这里雇的保姆保险系数大。”但是,这里常常供不应求。
自发聚集的保姆市场系指没有地方介绍信而靠私人介绍来的、漫天要价的、被用户逐出的、自己“甩耗子”的小保姆们的集合地,主要分布在朝阳、海淀、东城、西城四个城区。其中,和平里、劲松、三里河、中关村、建国门五处规模较大。五处中,又以安徽保姆聚集的和平里为最。这里往往又供过于求。
自发聚集的保姆市场与有组织的保姆市场各有优劣,处于竞争态势。探寻到小保姆心灵的轨迹,是我采访的目的。人一般是在不危及切身利益的情况下易吐真言。因此,我选中了建国门立交桥旁自发聚集的保姆市场。
每天上午,这里都聚拢着几百名要做保姆的和已做保姆又要“跳槽”的年轻姑娘。当然,其中也有数量不大的中年妇女,更夹杂着少量男性农民。他们是保姆的兄弟、侄子,步女人的后尘,也闯进京城“混碗饭吃”。
趁着雇主们还不多,我邀了几位口音各异、地域不同的小保姆在墙根儿聊了起来。我提的问题简单明了:你们为什么到北京来当保姆?
——“你们城里人都以为我们是因为家里穷才出来的。我家可不穷,一溜儿五间大瓦房,一年到头吃白面,日子好过极了。我刚17岁,说媒的就踩破门槛儿,讨厌死了。爸爸硬是作主要把我嫁给一个木匠,说他有手艺。我嫌他胡子拉碴的岁数大,不和他换手绢,不要他家的彩礼。爸爸用擀面杖打我。一气之下,我就跑出来了。”(笔者:出走原因之一——逃婚。)
——“我是安徽无为县的。知道吧,我们县在北京当保姆的有万把人。也不一定是穷,就是有这个习惯,曾听我姥姥讲,前清的时候,无为的人就出去给人家当佣人,但多是在江浙。后来抗战的时候,新四军七师师部就设在我们县。解放后,很多人进京给老干部当保姆,蹚下了这条路子。我嘛,家里有吃有穿,中学毕业后在县城一中的食堂干临时工,一月拿60多块,蛮舒服的。可是,我总想在大北京住上一段,过过首都的生活,也算这辈子没白活。城里人能出国开开洋荤,我们能进京就够不错了。刚干了两个月,人家又把我辞了,说是找到一个河南来的保姆,不用我这个安徽的人。哼,我还不干了呢!我在这重新找主,没50块钱不干。”(笔者:出走原因之二——传统习惯与开眼界。)
——“我4岁那年死了爹,娘又狠心改嫁出门,我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后来,我们家承包了9亩地,但没有劳力能干,只好让别人代种,干认倒霉。去年,爷爷又死了,我和奶奶只好靠吃棒子面活着。这不,邻家张婶把我带出来了。临走时奶奶差点哭死。要是这两天再找不到主我就回家,死也要和奶奶死在一起。对,我是穷逼出来的。能赚点钱给奶奶寄回去,就知足了。”(笔者:出走原因之三——生活贫穷。)
——“俺上高中时成绩挺好,全班数一数二的,可毕业后考了三年也没考上个大学。俺娘说:老赵家祖坟上没长那颗蒿子,甭瞎费劲了!爹也让俺准备出门子,哥嫂又嫌俺在家白吃饭。不中!谁说姑娘家念书没用?谁说姑娘家就该早早嫁人?俺不信这个邪!俺要到这大城市,帮工也干,看孩子也干,但要找个文化高的知识分子的主儿,能帮俺念点书。俺上高中时,作文还在全校喇叭里广播过。俺还想写书呢!您给俺帮忙介绍一家吧!”(笔者:出走原因之四——希望改变生活环境。)
——“我是黑龙江肇东那疙瘩的。好几天没人和我唠嗑了。你问我家经济情况?不就是要问穷不穷吗?要说也不穷。这几年靠养鸡赚了不少钱,盖了三间大瓦房。可也没存住钱,头年我哥要娶媳妇,见面礼花了400元,送红礼花了600元,下礼(定婚礼)又300元,加上结婚那天的开门礼、起床礼、起脚礼、洗澡礼、谢媒礼整整干了2000多块钱。对,我们那疙瘩都说‘儿子结婚如鬼门关,不死也得昏三天。眼看着家里拉下的饥荒,弟弟也有人来说媒了。我跟妈商量出来干几年,补上这饥荒,我自己也弄点好嫁妆。只要给钱多,我不怕活累。”(笔者:出走原因之五——补饥荒与挣嫁妆。)
我又找了一些小保姆聊,她们离家出走的原因大同小异。虽然我不可能象社会学家那样作出科学的统计数字,但成千上万个年轻保姆涌入都市的原因,则由此可见一斑。
年轻保姆群出现的更深层思考
——采访中的思想散记
孤立地谈论保姆问题,似乎很难把握它的实质。若把它投放到中国社会改革进程的宏观背景下去观察思考,不难从中获得新的启示。
中国农村具有极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实行“大呼隆”和“大锅饭”时期,业已出现的剩余劳动力被禁锢在贫瘠苍凉的黄土地上。进京看病,尚需赴省会开个证明,就不要再妄想进京“混碗饭吃”了。当改革浪潮撞击原野,这块板结的土地呈现松动,三亿五千万农业劳动力中,产生了30%左右的剩余,出路何在?乡镇企业是其一,如温州模式。男性可以奔波劳碌在乡村的土路、城镇的公路和通往大都市的铁路这一条条“线”上。年轻的女性步出家门,失去父母的爱抚和温暖,她在闯世界时也难摆脱女性的某些习性,希望有一个相对安稳的“点”,于是,她们进入家庭。
北京市的保姆,来自全国24个省的287个区县,占全国县城的20-25%,勿庸讳言,中国广阔的田野上,大多数人仅仅解决了温饱问题,少数人则连温饱也尚未解决。欲摆脱贫困,无技术、无资金、无信息,所有的只是质量结构上有严重弱点的劳动力。而今输送保姆进城,成为一些地区摆脱贫困的措施之一。因为这样做,不需要资源、资金、资料,结果是获益非浅。1984年安徽无为县仅保姆寄回家的钱便达200多万。某县郝店乡进城当保姆的有750人,一年寄回家乡20多万元。
近年来不大提缩小三大差别了。是的,差别不是靠人为就能缩小的,它往往搀杂在历史的过程中。许多小保姆进京念头的萌生,是从电视、电影、广播或亲属对北京的介绍开始的。历史给她们创造了进京契机。初入京都,高于农村的现代化不免使她们眼花缭乱,城里人的优越感又使她们心理难以承受。一位小保姆来到一个家庭,听“教导”说好东西都应该放进冰箱,几天后,她把照相机也放进了冰箱中的冷冻箱。另一位小保姆,仅仅在用户家呆了三天便辞别,问其原因,并非用户待她不好,而是她受不了雇主的“那股劲”。但是,她们毕竟进城了,她们在“阵痛”中改变着自己,开发着自己的“城市意识”。“黄山来的姑娘”想学唐诗,小保姆更想学做饭——将来回村开饭馆,学缝纫——将来回乡摆摊,学绘画,学英语——将来回去当民办教师……走出封闭的乡村,是一代农民素质提高的起点。
尽管京都市民对小保姆的议论纷纷扬扬,但都日益感受到她们的不可缺少。据调查了解,用户中工人占32.5%,干部占32%,知识分子占15.3%,个体户占11.2%,农民占7.4%,其它占1.6%。
“战斗的早晨,紧张的中午,疲劳的晚上。”这是很多人对每个工作日的形容。作为休息日的星期天,也常常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被称为“家务劳动日”。人们渴望减轻繁重的家务劳动。另外,北京市260多万户,其中76万户是双职工,但婴幼儿入托率只有38%,其余62%的婴幼儿仍要靠家庭抚养。1982年北京市育龄妇女为274万人,到2000年将增加到300多万人。在托幼事业发展缓慢的时刻,千家万户只能求助于家庭保姆。
是的,家庭保姆的社会功能愈益显露,她们的命运也就愈益融入整个城市生活发展的大趋势之中。而由此产生的各类问题也将在改革中日趋明朗,并不断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