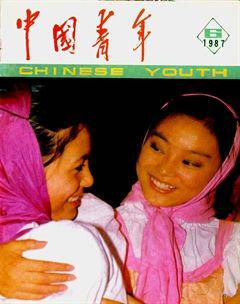知识产权、冒牌货与法
大约是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所说,写文章分两种:一种是写而不卖,一种是卖而不写。李杜苏辛的诗词可能属前者。是否“藏之名山”,未知,但绝无沿街叫卖之事。若李白摆摊,以一字千金计,《蜀道难》定可致大富。作家而成职业,作文而兑现钞,是晚近的事,和古之“润笔”并不相同。按字计酬,按篇索费,是文艺作品和学术作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出现才开始的。这就使卖而不写的现象被大家注意起来。既不写,何能卖?情况的确复杂。一种是彻底的卖而不写。所卖何物:试将王蒙换汪梦,汪梦乃尔大名;且把屠格涅夫换司马文峰,汝却不著一字。下笔万言,贝娄之抒情,契诃夫之状物,川端康成之心理分析,悉收笔下,大段照抄,整块拼装……多快好省拿稿费。但此般技术,颇为危险,殊为少见。一种是,半彻底地抄,此法精义,在于巧夺:抄情节、抄人物、抄观点……拟将北海道雪纷纷,化作漠河镇纷纷雪;且看论者侃侃,原来都是普列高津论文提纲,用此种方式追名逐利,真伪难辨,法有不逮之处,故而诸多效尤,一时泛滥。
另一方面,由于复制录制日见发达,不仅作者有被窃之虞,出版商亦频涉被盗之危。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会尚未播映,早有精明的出版商在街头兜售该晚会的歌、曲磁带。一部畅销小说付梓之际,已被人象偷高考试题一样抛了出来,影印复印,以高于该,小说定价5倍以上的价格倾销。对一般的消费者,这也许是无关宏旨的事;虽有被敲之感,但毕竟偶尔为之。但作为出版者,则是一笔多么大的经济损失!你想,你辛辛苦苦组织的一台节目,请作曲家,请歌手,请乐队,做难以言表的复杂组织工作,这样的劳动,原是可以有优厚补偿的。现在好了,袖手者只须在你苹果园的苹果熟了的时候来采摘就是了。这样的洗劫,你经得起么?这冤哉枉哉的事情,难道不应与盗财窃宝视为一般无二么?
诗文也好,书籍出版也好,我认为,至少在现在是具有商品属性的。不然的话,为什么被采用的稿件要付薄酬,为什么书肆里的图书都有定价。读者要汲取精神食粮,就如同要用人民币买米买面一样。这和我们所厌恶的“商品化”的说法是不同的。“商品化”是指,写作、出版甚至包括演出,全不顾世道人心,一味地捞钱。譬如,那种思想肤浅、格调低下、用恋用爱用尸案用艳史掏读者腰包的就是。即使如此,凡属于被买的稿子,被卖的书籍,都具有商品的属性。既然是商品,就有经济利益关系;既有利益关系,也就同样有了法的关系。我们以往处理这种事,声讨多于制裁,是一大欠缺。某人直接地或间接地抄了别人的作品,众人异口同声地骂他“文抄公”就是了。赔偿乃至加倍赔偿的事极为罕见。而象复印、翻制之类的事,简直就不算是桩事。我发现,旧的图书多半注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而新的图书,却几乎没这条规定。兴许是觉得此番标注,未免小气,大有垄断文化成果之嫌疑。细一想,不尽然。这很可能与我们在这方面仍缺法这根弦有关。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一部出版法,但 一定应该有是铁定无疑的。不然,这类讼争会没完没了,也无所遵循,文化大盗小盗也就愈发猖狂。
涉及智能、知识、技能方面的成果,大都有这种问题。据我所知,国外的一些技术窍门,我们得花钱买。因为涉外,是纯粹的买卖关系,所以也无话可说。即使国内,恐怕也有个技术专利权问题。或许有人说,专利云云,岂不是“技术封锁”。问题并不这么简单。上学,是要交学费的,你怎么能说这是文化封锁呢?同理,一个企业或研究所花了时间花了钱,好不容易发明一项技术,你抄走图纸资料就去生产,就去赚钱,合适么?你要学,对不起,请花钱买。否则,谁还愿意花钱搞科研,赔本搞发明呢?又譬如,一乡办啤酒厂,酒卖不出去,于是开印“五星啤酒”的商标,贴上卖,合适么?且不说达不到“五星”质量,即使是达到乃至超过“五星啤酒”,也不能如此张冠李戴啊。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版权、专利、商标等等诸法,是为了制裁侵权行为,保护当事人利益的。这些法的实施肯定会有助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否则,就杜绝不了冒牌名著,冒牌五粮液,冒牌发明家……
米博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