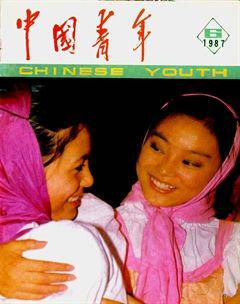米沙的命运(报告文学)
贾宏图
如果命运朝你胸口打了一拳,你不要后退。无论如何要前进!这才是勇敢。
——奥斯特洛夫斯基
A.1958年明媚的夏日。随着他胖乎乎的小手在钢琴的键盘上调皮地划过最后的一串流水般的音响,少年宫剧场里响起了潮水般的掌声。他走到台前,右手举过头顶,向观众致以少先队员的敬礼。这时,他一眼看见了坐在观众席上的妈妈—尼古拉乌沙克娃,那位穿着浅蓝色连衣裙的俄罗斯妇女。他好象听妈妈对他说:“OueHbxopowo,Muwa!”(太好了,米沙!)“快看呀,二毛子!”不知台下哪个孩子喊了起来,引起观众席上的一阵哄笑。小胡泓在笑声中跑下台,他哭了,泪水滴落在胸前的红领巾上。少年宫的老师一再劝他,他还是放弃了下一个节目—小提琴独奏《花儿与少年》,尽管他的小提琴水平是高于钢琴的。
“妈妈,他们为什么叫我二毛子?”
“米沙,你听妈妈说,二毛子没有什么不好!”
妈妈告诉他,外祖父是来中国东北修铁路的俄国工人,他把自己的三个孩子献给了中国革命。妈妈是解放军四野的护士,爸爸是东北抗日联军的营长。他们相识在炮火连天的战场,结合在绿色的军营中,而他是伟大民族友好亲善的结晶。
米沙不哭了,他搂着妈妈的脖子非让她讲爸爸的战斗故事。此刻,他多么想立刻见到爸爸。这时爸爸正在遥远的欧洲。解放后,这位解放军团职干部被党送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水电专业,毕业后又被送到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等国家进行为期三年的学习考察。
妈妈告诉他,昨天晚上,她梦见爸爸回来了,站在窗下的丁香花丛中喊她:“安娜,我回来啦!快让我看看米沙长多高了!”今晚,米沙也梦见了爸爸,他走下飞机,向他跑来,一手捧着鲜花,一手拿着一枝小冲锋枪,——那一定是给我买的。他笑了。
B.1970年严寒的春日。
“爸爸,爸爸!”他急切地呼喊着,一把推开门。妈妈倚卧在那架破铁床上,身上盖着旧毯子,零乱的白发披散在她满是泪痕的脸上。他一眼看见桌子正中摆着的一个木制的盒子。上面是一朵白色的纸花。
他是3月16日在完达山下的兵团连队接到家里的电报的。电文写得很清楚:“父病故速归。”可他不相信46岁的爸爸会死!这是使人难以接受的现实,老抗联战士、共产党员、电机专家,死在我们自己的监狱里!
他想起他和爸爸那最后的一别。那是1968年2月14日,爸爸起得很早,让妈妈装好饭盒。本来研究所已经乱套了,可他每天还是按时上班。他穿上大衣要走了,又转身回到胡泓的床前,把他叫醒,摸摸他的手,亲亲他的脸,告诉他:“外面太乱,别出去,在家看书!”就在这一天,爸爸被抓进监狱。
也就在这一年的冬天,胡泓穿着浅黄色的大衣,钻进了北去的列车。可是,他并没有摆脱厄运,荒原的原始的劳动他并不惧怕。可怕的是他失去了应该得到的信任。他是一个艺术的精灵,13岁时竟能把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从头拉到尾,而不差一个音符。可现在他却无缘登上连队那用土坯堆起的舞台。他教的学生都上了团里宣传队的“威虎山剧组”,可他还在山下边。师里要成立宣传队,他写了一封长信毛遂自荐,这封信又转到连长手里。他遭到一顿臭训:“你也不搬块豆饼照照,自己是什么货色!”部队文工团来招兵,他大显身手,放下小提琴,又拉手风琴,接着又唱大号男高音,最后还交上一个剧本和一个舞台布景设计。可惜,胡泓和招兵的人都是空欢喜,他的“档案”令人望而生畏。
他苦闷,多少次跑到连队附近的白桦林,象野狼一样嚎叫;他徬徨,在欢度新年之夜,他竟顶着大烟泡在荒原上游荡……今天,他简直绝望了,他抱着爸爸的骨灰盒哭啊,喊啊!仿佛要渲泄心中的一切忧怨和不平。
“孩子,不要哭了,你爸爸不喜欢你这个样子!”妈妈因为爸爸的死,突然瘫痪了,可她的心是坚强的。因为她曾经是一位革命军人,她象高尔基笔下的母亲,她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巴维尔。
琴声,铿锵的琴声,又飞出这间木制的俄式花园小房。33310*22270*这是贝多芬的《命运》。
歌声,低沉的歌声,又飞出这间木房雕花的窗口。“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这是列宁最喜欢的《三套车》……
C.1974年风雪迷漫的冬夜
这是海拔3000多米的青海高原的一个高炮连队。
满脸胡须的新战士胡泓刚刚下岗,他抖落军大衣上的积雪,又使劲跺了跺脚。汽油桶里嗞嗞燃烧的木柈子烤得他暖洋洋的。他毫无倦意地从铺下拿出一本稿纸,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又开始了他的边塞文学生涯。
谁能想到,无情的命运之神,又把他从北大荒掷到了青海高原。父亲死后,他滞留在哈尔滨,顶起了破败的家。起初,他给人家补鞋、磨刀、打洋铁盒,后来又干起木匠活。下乡前,他在电子仪器厂当临时工时考取了五级木工。当时他才16岁。为了使人看不出他的年龄,他竟天天不洗脸,整天戴个破帽子。听说刮脸能长胡子,他一天刮两次。
家境稍有改善,他又拿起了琴。他不信,凭自己艺压群芳,凭自己在哈尔滨业余文艺爱好者中的声望,就考不上专业文艺团体?一次又一次的初试、复试,一次又一次精彩的表演,他总是过五关斩六将,可一到政审,他又总是“走麦城”。人家说,要当文艺兵,必须走后门。他坐火车跑到西安,去找一位在军队任高职,又走红的亲戚,可人家不愿理睬他。他又自报家门地跑到兰州空军文工团,不要任何待遇地当了一阵子“临时工”,这下子感动了上帝。文工团派出干部三闯关东,到兵团调他,可都碰了壁。第四次,胡泓和部队的同志一起来到了兵团,还请军方的一位要员写了信,他总算摘下了“知青”这顶帽子。
胡泓雄心勃勃要大干一番。连着写了几个剧本,人们却看中了他的高个头,宽肩膀和一手好木匠活,于是他成了舞台美工。他仍然干得很来劲。同时他还十分狂妄地说:“中国应当有贝多芬,有莎士比亚,鄙人要当中国的贝多芬和莎士比亚!”还有相当“过激”的话:“不是说百花齐放吗,怎么只有八朵!”于是他被光荣地派到连队,长期深入生活—来到了这青海高原的高炮连。时间不算短,连着在高原上两年没人理睬他;生活也倒相当丰富,馒头蒸不熟,白水每天分半碗,白天端枪站大岗,晚上打扑克谈女人。为了不辜负上级的期望,他不停地写,什么高原战士的风情,可爱的藏族老阿爸……几十万字的稿子写出来了,可找不到读者,只配摞起来当枕头。
有一天,他心血来潮地给战友们朗诵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不顺心的时候暂且容忍;/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会到来。
“这是谁写的?”一个小伙子问。
“普希金。”胡泓答。
“啊,肯定是个老毛子,是你舅吧!”
胡泓眼里闪着泪。
D.1984年金色的秋天。
胡泓坐在南岗区人民医院昏暗的放射线科那间小屋里,仿佛浪迹天涯的游子回到了宁静的港湾。对他来说,X光医生的工作是清闲的。
他是在历史转折的1976年复员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的。一下火车,望着那既亲切又生疏的一片片建筑,他竟泪水蒙蒙。这座美丽的城市并没有对他这多情的儿子表示出热情。他想到文艺团体去重操旧业,可那里容不得一个青海高原的大兵。在区文化馆当了几个月又编又导又演又唱的临时工,可终于被有门子的人挤掉了,尽管那个人连简谱都不识。后来,他被安置到南岗区医院,倒也心安理得,分配他当X光医生,他胜任愉快,而且很快在技术上高人一筹。总算有了可以挣钱吃饭的看家本领。
生活平静如水,他和别人一样成了家。妻子是医院的护士,她对他好,他认为她可亲,他们很快就结合了,又很快有了女儿。奶奶给她起名叫Bepa(维拉),俄语的意思是信心、信念。而他却愿意称维拉的谐音“月亮”,因为他喜欢月亮的皎洁、清高。他深深地爱着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三岁就开始跟他学琴的小女儿——小月亮。
也许是妈妈的死,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这位和中国人民一起饱经忧患的俄罗斯妇女,在人民开始了崭新的生活的时候,她悄然离去了。妈妈的晚年是在读书中度过的。她读格林的童话,读托尔斯泰的小说,而她最喜欢高尔基。妈妈临终时说的话是:“米沙,给我念念《海燕》吧!”他回答妈妈说:“我不能当一辈子企鹅!”
他有一种预感:我们到了人尽其才的时代。他把突破口选在文学,他的处女作《黑雪地》被《青春》杂志登载在显要位置,这是一篇描写劳改释放人员奇特爱情的故事,歌颂被压抑的人性。而第二篇是描写当代青年爱情生活的,其中也有他自己的影子。《你自己寻找太阳》,小说的题目好象是胡泓的宣言——他自己要去寻找太阳。
这一天,哈尔滨最大的商场秋林公司的家具部,突然人群熙攘。这个城市的公民崇尚高雅家具,可眼前这一套家具令人叹为观止。这是一套欧风家具,式样古朴华贵,颜色浓重高雅,最精彩的是家具表面上刻工相当精细的浮雕。酒柜上刻的一个窈窕的少女坐在椰树下吹笛,左右两边是展翅欲飞的小天使,梳妆台上刻的是一个拉提琴的风流潇洒的男士,旁边是两个弹竖琴的侍者。1850元的要价并没有吓走鉴赏家们,交款处排起长队,售货员只好宣布让人扫兴的消息:这套家具在运往商店的路上,就被人定了货。这套家具的设计和制造者就是胡泓。
几天前,他正式辞去了医院的工作。几天后,他的名字出现在哈尔滨日报上。又过了几天,芦家街17号,他的家里宾客盈门,来定货的,来学艺的,来搞联合的,个个面带微笑。转瞬之间,他成为哈尔滨成千上万个专业、半专业木匠中的佼佼者了。为了扩大生产,他在客厅里也安上了电刨、电锯。“这回米沙可发大财了!”邻居们这样说。连楼下那位最老实的老头,也三天两头向他要酒喝,名曰收取“震动费。”每次胡泓都慷慨解囊。
E.1986年多采的春天。
哈尔滨火车站,永远喧闹的广场。
5月21日,广场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新奇的建筑。过往的行人大吃一惊:昨天这里还是个空场呢!这是一座风格别致的建筑小品,它由两部分组成,一侧是个圆顶的塔楼,另一侧是由铁皮拱形屋顶的小洋房,占地面积50多平方米,整个建筑都是木制的,精巧典雅,让人耳目一新。这又是胡泓的作品,他以此向养育了他的母亲城市再表点心意。
胡泓在去年年底又出人预料地关闭了办得正兴旺的家具店,这等于每月扔掉一个四位数的银行存折,人们疑惑不解。胡泓象一个永不满足的追求者,他要的不是金钱而是艺术,为家具鉴赏家们增加几件室内摆设,已不能使他欣慰,他梦寐以求的是为这座风姿绰约的城市再献上几首凝固的乐章。于是,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小伙子成立了这个建筑装修队,并以他不满四岁的女儿“小月亮”的名字命名。因为他对这两个生命寄予一样的期望。他为每个队员亲手设计了一套背上印有月牙标记的夹克衫,他相信中国的月亮和外国的一样圆。
成立会开得相当庄严,在队旗下,胡泓代表队员宣誓:小月亮的宗旨是为艺术,不为金钱,每个人都要有献身精神,创办哈尔滨第一流的建筑企业,建设哈尔滨第一流的工程,要为历史和后人留下永恒的纪念!
第一炮就打响了!这群以普通工人、待业青年组成的队伍,完成了哈尔滨第一个由本地人干的室内装修—哈尔滨摄影社。行家说,不比香港人搞得差,而且省了一大笔钱。汽车出租公司基建处的一位干部来这里照相,当即和胡泓敲定,请他设计站前的调度室。这时他们已请过许多专家,提出多种方案,都不尽如人意。3天后胡泓拿出5份图纸,张张令人惊喜,经专家审定,终于选定了现在干的这一个。
迎着春风,这座建筑小品象亭亭玉立的少女,站在火车站广场上。它那美好的形象印在报纸上,出现在荧屏上,过往的旅客也争着和它合影留念。有人说它象童话中白雪公主住的小屋,有人说,它象欧洲的乡间别墅。
在蒙蒙春雨中,胡泓和一位年轻的法国外交官在这座建筑前进行了一次非官方的谈话。他是法国驻莫斯科的商务参赞,他在这个城市住了5天,竟4次来到这里,明天就要离开此地,今天又冒雨来了。
“我很欣赏你的才华!”
“如果时间充裕,我会搞得更好!”
“这么美的建筑小品,莫斯科现在也没有!”
“我们会搞更多莫斯科没有的东西。”
F.1986年酷热的夏天。
胡泓大步走进松花江畔的雄伟建筑—友谊宫,心里不禁一阵激动。50年代,爸爸妈妈经常领他来这里参加舞会,看望支援我们建设的外国专家。可是后来,专家们竟不辞而别了。久违了,友谊宫!
在二楼一间布置典雅的会议室里,聚集着这座城市的十几位建筑设计专家,他们来自实力雄厚的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省和市的建筑设计院。这是一次招标审定会,标的是中国哈尔滨玉泉狩猎场建筑群体设计。这是我国建设的第二个狩猎场,中南海经常来电话过问,市政协组织社会名流、贤人智士多次论证它的建设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