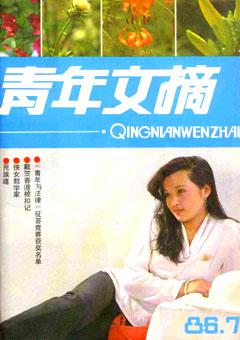文学家室名琐谈
1986-11-01 04:16张宜清
青年文摘·上半月 1986年7期
张宜清
我国不少文学家喜欢给自己的书屋、居室命名,藉以表明志向、寄托情怀、以为自勉。
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把自己的书屋称作“绿林书屋”。因为鲁迅支持学生运动,当时的一班“正人君子”诬蔑他为“学匪”。鲁迅认为这诨号有杀机和“可死之道”,便索性以“绿林”命名其书屋,以回击那些无耻之徒。
著名诗人、学者闻一多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把故乡湖北稀水的书屋取名为“二月庐”。当时,每逢暑假他回到故乡稀水,充分利用两个月的假期,在“二月庐”认真读书。
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叶圣陶,二十年代后期给自己的居屋题了“未厌居”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室名。1929年他的小说印行,书名就叫《未厌集》。他说:“自家一篇一篇地作,作罢重复看过,往往不象个样儿,因而未能厌足。愿以后多多修炼,万一有教自家尝味到厌足的喜悦的时候吧。”数十年来,叶老始终涉笔从严、未能厌足。
著名作家、文物专家沈从文,青年时代居住在北京湘西会馆,房屋狭窄,潮湿,经常散发出霉味,他便戏题居室为“窄而霉斋”。沈从文至今脍炙人口的一些早期作品,大都诞生在这座“窄而霉斋”里。
著名作家姚雪垠,二三十年来赶写数百万字的历史长篇小说《李自成》。姚雪垠给自己书屋取名为“无止境斋”,以表虚怀求索之志。
著名小说家张恨水在抗日战争时期,住在重庆市郊南温泉的三椽茅屋里。这茅房顶上铺的是山上的茅草,大雨一来,屋内水流如注。久而久之,哪里漏水都有数了,于是,每逢阴云四合之际,张恨水和家里人将盆盆罐罐各就各位,等待漏雨。张恨水幽默地为这个茅屋取了一个名字:“待漏斋”。
(摘自1986年4月5日《光明日报》)
猜你喜欢
人物画报(2020年7期)2020-01-05
鸭绿江·下半月(2019年11期)2019-10-21
高中生·青春励志(2019年4期)2019-05-09
北广人物(2018年31期)2018-09-05
第二课堂(小学版)(2018年3期)2018-06-12
小天使·四年级语数英综合(2016年8期)2016-08-23
儿童故事画报(2015年8期)2016-01-27
儿童故事画报(2015年8期)2016-01-27
儿童故事画报(2015年8期)2016-01-27
儿童故事画报(2015年8期)2016-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