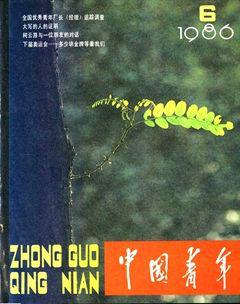大写的人的证明
陈晓轩
读懂他,也许就读懂了你自己。——题记
引子
他想站起来。是的,站起来。
用两只脚掌撑住地。腿好轻,轻。稍一用力,身子就飞起来了……不想飞。只想站起来。站直,站稳,然后开步走。用腿。腿不听使唤。抬不起来,抬不起来……沉。沉得象铅,象钢,象学校操场上那副自己从未举起过的杠铃……
他睁开眼。还是那间病房,还是那张病床。已经躺了一个月,明天就要出院。临出院前老做梦。腿的梦。刚才又是。
一个月前,一节货车车厢从他身上滑过。双腿几乎齐根轧断。同时留在车轮下的,还有那只经常挎在肩上的拾煤渣的竹筐。
他把手伸进雪白的被单。他总以为两条腿还在。他不断地缩回手,又不断地摸过去。
明天出院。
明天将把他的人生分作两半:一半留在梦里,一半属于那个未知的世界。
那是1966年。他13岁,明天出院。
他绝没想到自己面临的是这样的处境:
“断脚杆!”
我叫曹前明!
“曹跛子。”
曹前明这个名字似乎已被遗忘。
他坐着手摇车去学校。这手摇车是肇事单位铁路局的赔偿。刚进门,一个牛高马大的同学拦住去路。
“跛子,下来。”
“做什么?”
“玩玩你的车。”
他不给,那同学便一把将他推下去。他挣扎着,滚动着,然后仰面躺在地上。在那个同学眼里,这模样很象一只甲虫。
他去告诉老师,老师找了家长。第二天,“牛高马大”又出现在他上学的路上。
“你还敢告老师?”话音未落就是一个耳光,“你再去告。告一次我就打你一次。断脚杆!”
他不愿再去学校。他只在家门口的街上坐坐。
一群孩子围住他。这个拍拍头,那个戳戳肩膀,然后“啪”地一口唾沫就吐在他后脖颈上!
孩子们怎么会这样?!
倒不如反问一句:在那个年月里,大人们又是怎样?
他要工作。他去找街道居委会。
“让我去糊纸盒吧,糊纸盒也不用腿。”
“不行,安排不了。”
“我去那个做橡胶鞋底的地方。我不怕脏,不怕臭,我只拿最低工资。”
“不行,安排不了。好人都安排不了!”
所有的拒绝都不是光用语言完成的,它还包括脸色、眼神、口气和手势。这些东西都比语言本身更富表现力。
表哥结婚,请去他们全家,唯独不请曹前明。让一个没有腿的人坐在席面上,表哥觉得脸上不好看。“你这个废物!”这是父亲在对他说话,“就这么让我养活你一辈子啦?”
母亲呢?母亲附和着父亲。
曹前明作过一个非凡的努力。他要为家里盖一间房。
曹家三代七口人,挤在两间共24平方米的小屋里。他盖的房子,面积将与两间之和相等。而且,一个人干,不请任何人帮忙。
他摇着小车,蚂蚁搬家似地运回砖头、石灰,再一点点地和泥,一块块地砌砖,爬上爬下地丈量,直至盖顶。他干了将近一个月,房子完成了。尽管非常简陋,毕竟是间房子!
这个努力本可以告诉人们许多东西。你让一个四肢健全的人试试看,一个人?盖间房子?
不错,父亲笑了,但这笑容没有维持多久。是,人们也惊讶了,却不过是惊讶而已。没有谁指出这件事情的价值,没有谁表现出对曹前明态度的改变。鄙视的照旧鄙视,不安排工作还是不安排工作。这一努力导致了违背初衷的绝望。曹前明认定: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并不把他当作人。因为他没有腿。
一个不幸的人得出一个不幸的结论。
这不仅是曹前明个人的不幸。
一年以后的曹前明就变得让人不认识了。他异常灵活地用两只手走路,手镫上镶着4厘米厚的钢板,哪个敢出恶言,蹿上去就是一家伙;他神鬼不知地潜入火车站,从装满货物的车厢里甩下一个个包装箱,下面接应的同伴便怀抱而去。
盗窃为了生存,打架则出于报复。不是拿我不当人吗?好,我就教你放明白点儿。你一条命,我半条命;我不怕死,你呢?
他打过几场死架。一帮小兄弟争先向他靠拢、致敬,他被推为成都腐青路一带的“舵爷”。在那个畸形的圈子里,他得到了畸形的肯定。曹前明对此想得十分简单:我不管那许多,谁拿我当人,我就和谁来往。
这是那个不幸结论的延伸。1975年,他顺着这条路走进监狱。
曹前明的入狱原因,带有那个年代中常见的蹊跷,我们姑且不去考证。他自己说:“照我当时那个路子走,进监狱也毫不奇怪。回过头来看,在那地方呆了三年,倒埋伏下我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机。”
正是在那里他开始了认真的思考。对自己,对人生,对世界。他很幸运,和他同监关押的,一个是白发斑斑、知识渊博的教授,一个是目光犀利、为人爽快的原刑警大队长。与这两位人物平起平坐地相处,为曹前明在精神上和哲学上洞开了另一个世界。三年后,当曹前明重新坐上手摇车,回转身来,向漆成黑色的监狱大门望了最后一眼的时候,他已经为自己的人生定下一个昂奋的基调。
那是1978年一个秋日,多雾多雨的成都碧空如洗。
曹前明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他不失尊严地谢绝了往日小兄弟的拜访,也不再为了随便一份什么工作去向随便什么人苦苦哀告。他用两个月的时间学会了修自行车的手艺,然后在车水马龙的路边摆了个地摊。
学这门手艺不容易,他挺直了身体,也高不过最矮的自行车;办这个营业执照更难,要不是那个姓陈的女民警奔走,便可能拖到猴年马月。但是,以后的路不管多难,他都将不再旁顾,不再回头。他相信这路,也相信自己。
“快看快看,一个跛子修车!”
他连眼皮也不再抬一下。车修好了,主顾试骑一圈,满意地走了。围观的人群却不散。“嗬,还真行啊。”这称赞比那呼叫高出了一个境界。人们啊,还是少些愚蠢为好。
昨天的摆摊处,今天突然被屙上几堆屎。他不动声色,换个地方照摆。莫非你敢把这整条大街屙满?几次寻衅,
几次忍让。街对面那几位同行举着香烟来赔罪了。“曹哥,你真有气量!”他点上香烟,淡淡地一笑:“人,靠本事吃饭,别耍把戏。”
一个小偷欺他行动不便,端起车摊的钱箱就跑。他靠手摇车抓住了这个窃贼。旁人气不忿,齐声喊打。曹前明说:“谢谢大伙儿,你们都别管了。”他给小偷买了顿饭,然后把钱箱里剩下的钱全掏出来:“这钱送你了,我什么话也不说,你夜里睡不着觉自己好好想想。”
那小偷,一个18岁的孩子,给他跪下磕了一个响头。以后还写过信,告诉他:恩人,我改了。
曹前明的地摊发展成铺面,每月有了二三百元固定收入。他1981年娶了妻,1983年得了子,他拥有了一个普通健全人能够拥有的一切。
即便故事到此结束,也已经有了大团圆的结局。但对曹前明,这却只是个开头。他所能证明的,远非仅限于此。
曹前明向妻子宣布了一个决定:爬峨眉山。
他的妻子叫覃清兰。按照通常的分类,曹前明属伤残人,覃清兰属健全人。健全人覃清兰算不上漂亮,但说端庄清秀绝不过分。再按照通常的对象原则,覃清兰的自身条件绝对具备媒人接连上门的资格而不致四处寻找出嫁机会。但是覃清兰嫁给了曹前明。
覃清兰反对把自己这个举动称作“高尚行为”,也不同意简单地用“心灵美”解释其意。她觉得如果这样认识问题,是“对我丈夫的不尊重”。她说:“我看上他了,所以就嫁给他了。”
曹前明先后谈过八个对象,第八个是覃清兰。他说:“我是挑了又挑,最后选中清兰的。”他说:“社会上仍然有很多人对我们看不起,所以我们找老婆的条件就更得苛刻些。”他说:“我选中清兰,是因为她贤惠,懂人。”他说的不是“懂事”,而是“懂人”。
覃清兰感觉到:在这个男人身上,蕴藏着一种强烈的愿望。他不甘平庸,早晚会干出些令人吃惊的事情。覃清兰钦佩并且信赖这个男人,她决心尽自己所能,给这个男人以支持和帮助。这大概就是曹前明所说的“懂人”。
尽管如此,当丈夫宣布了决定,妻子还是吃了一惊。
“爬峨眉山?!”曹前明递过一份报纸,那上面有条消息:美国一位断腿A级妇女,登上一座海拔1,500米的高山,被授予世界伤残人登山运动者金杯。
“可是峨眉山3,000多米呀!”
“3,099。”
“这……太苦了。”
“我知道,你是懂我的。”
妻子不再说话。
几天以后,1983年5月1日,曹前明在覃清兰的陪伴下,来到峨眉山脚。
峨眉,于四川西南拔地而起。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这是诗人的描述;从报国寺到主峰金顶,计115华里山路——这是测绘队的丈量数据;每年几百万游客至此,能走完全程的不超过一半——这是峨眉山管理处的估计;此处公元六世纪前即有庙宇落成,未曾闻有无腿之人光顾——这是万年寺主持方丈的追溯。
曹前明来了。他两臂撑着两只石锁形状的手镫,臀下垫着一个用皮带缚住的小方凳,走向这座天下闻名的大山。
在进山处,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劝他:“你到了这里,峨眉山就算来过了。照张相留作纪念,回吧。”
曹前明说:“我要到金顶去照相。”
工作人员转而鼓励说:“好样的,争取十天爬上金顶!”
在万年寺,一位年过半百的出家人恭恭敬敬地走过来,称他为兄弟:“还了愿,请早些到客房歇息。”
曹前明谢过长老,转身出了庙门。“我是来还愿的么?”他问自己。曹前明的“愿”,那位长老连同他的普贤菩萨未必理解。
在洗象池,一群半途而返的登山者围住了曹前明。“别上啦,我们都受不了,下来了。”
曹前明说:“我受得了。”
几分钟后,那群登山者又追了上来:“你走到哪儿,我们走到哪儿!不然没脸回去了。”
当他到达离金顶还有十华里的七里坡时,这样的追随者在他身后已经聚集了将近一百!
不必去描述这个没有腿的攀登者一路的艰辛,这种时刻,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让曹前明自己讲,也就是一句话:“到后来,我就没有知觉了。”
但覃清兰是有知觉的。她脚上打满了血泡,两条小腿肿得脱不下鞋。她用毛巾为丈夫一次又一次擦去汗水,她的手帕被丈夫手上渗出的鲜血染成全红,她几乎是哭着扔掉丈夫臀下那当座垫的方凳——那用铁条箍住的方凳已经散架。
请读者自己想象这个场景:
一个只有半截身躯的人在前,成百四肢齐全的人随后,再加上那被鲜血染红的旗帜一样的手绢……
这是何等壮丽的进军!
曹前明终于攀上主峰,走向峨眉山金顶,他看见,那颗圆圆的硕大的太阳,正沿着眼前带状的山峦,向下砸去。他想跳,想喊;他想把头高高昂起,发出摇山撼岳的大笑。覃清兰突然蹲下来,抱住他的肩,哭了。从峨眉山下来,覃清兰问曹前明:“前明,你还想做什么?”
是啊,我还想做什么?刚一回成都,他就径直闯进省体委,宣布:“我爬上峨眉山了!”
你爬上峨眉山了?你?爬上了……峨眉山?你是谁?干什么的?怎么爬的?用了多长时间?
“两天!”两天?!你……赶快在这登记,填表,写清楚点儿,我们可能以后找你。你要是搬了家,可告诉我们一声!
我还想做什么?
他在成都一下子成了名人。所有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只要听说此事,莫不对他肃然起敬。他可以从最拥挤的小巷到最宽阔的人民广场,骄傲地抬着头,满不在乎地走来走去。他驾驶着已装上发动机的手摇车经过十字路口,警察会向他点头致意;省运动队颇有声望的教练,老远要跳下自行车,走过来同他握手。当然还有记者恭敬的提问,领导亲切的接见等等。这一切,在他不堪回首的往昔,可曾敢想过?当然想过。而且,正是由于想过——刻骨铭心地想过!他也是个人。
那么现在呢?
我还想……
1984年6月27日,曹前明坐在美国哈佛斯坦大学游泳馆的跳台上。这是国际伤残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赛场。
这就是他想了一年,准备了一年的事。他将不仅代表个人,而是代表一个民族,去和别人较量较量。
他参加的是A1级比赛,报了游泳个人项目的全部。五项比赛分两天进行,蛙泳、仰泳、自由泳昨天赛完,他的成绩是两个第四,一个第五。这个成绩如何?不妨参照一下:在奥运会(健全人)上,我国游泳选手的最好成绩是第八名,接下来便全在20名以后。
头天晚上,领队和他谈了话:“蝶泳、混合泳不要硬挺,游不下来没关系,我批准你技术犯规。”
“可我还没拿牌啊。”
“大家都看到了,你尽了很大努力。”
曹前明摇摇头。大家都看到了。我还没有拿牌。没拿牌就不能升国旗。中国国旗。
“中国国旗……”夜里作梦,他就这么喊。同屋的伙伴都被这几个字惊醒。
他坐在跳台上,两手撑着两个边,静静地等待着发令枪。这枪声只会为他再响两次。他突然意识到,原来,为这枪声,他已经等了那么多年、那么多年!
出国前,他的教练汤国荣嘱咐:“入水不要图远,行进不要图快,转身不要图省力,关键的关键是:始终保持平衡。”
离家时,他的妻子覃清兰叮咛:“比赛的时候,你什么也别想。”
他静静地等待着那枪声。
两次枪声响过,美国哈佛斯坦大学游泳馆内,国际伤残人奥运会比赛场中,两次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同伴们为他欢呼着,“咔咔”作响的镁光灯将他包围着。他不说,不笑,不动,只是凝望着那因他而升的他的祖国的国旗。
两行滚烫的泪,淌过他冰凉的面颊。
尾声
1985年底,曹前明当选为四川省伤残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他拿出很大精力联系省内各地的伤残人同伴,为他们分忧解愁,帮他们规划前途,替他们奔走呐喊。他先后为省伤残人运动队举荐了五名运动员,为数十名伤残人解决了生活、工作、治病等问题。他还打算亲手组建一支中国伤残人排球队。
他依然开着修车铺,依然从事着游泳运动,游泳之余练习投掷。他的心里,依然“蕴藏着那种强烈的愿望”。
他只有半截躯体,但他是个必须大写的人。
他使我们自省。在他面前,我们面对着一道共同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