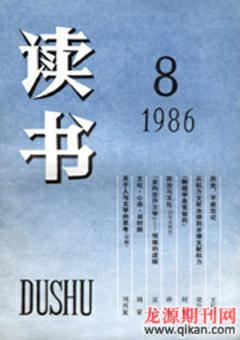三对对立性格形成的六面体
季 秋
当一个人,在生命旅途中已经困顿苦恼到象哈姆雷特那样诅咒自己的出生时,他也会高叫道:
“难道有谁问过我,我愿不愿意到这个尘世上来作客呢?我毫无理由地被丢进这个愚蠢世界里来接受一直象诅咒般压着我们,只有死亡能够给我们免除的那个命运……”
类似哈姆雷特的人,在各种各样人生的任务、目标、责任下,痛苦地喘息着,支撑着,已经看不到那理想之星的光芒了。可是,在这时,忽然看到瘦骨伶仃的唐·吉诃德的永远满足的微笑,哈姆雷特会号啕大哭,会活着从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会把自己的多余的聪明扔掉,宁愿寻一匹瘦马,跟在唐·吉诃德的身后,永远陶醉在唐·吉诃德发自肺腑的欢笑中。为了得到唐·吉诃德式的快乐,需要同时得到他的愚蠢,对信念教条式忠诚的愚蠢。有了这身盔甲,充满了自信,在世人的讽刺、嘲笑中,唐·吉诃德本人永远幸福。
可是,如果唐·吉诃德在人生旅途中,感受到哈姆雷特那种灵魂的侵蚀,睁开慧眼,看清自己半生疯疯傻傻的蠢事,直线式思维对社会的破坏,美好的理想导致处处开倒车,会羞愧地一下子从他的老马上跌落下来。
哈姆雷特与唐·吉诃德的相见,太有意思了。只有他们相互衬托,各自的特点才会显出本身的优越性来。矛盾的解决是两极向着各自的对立面转化。失去对立面,本身将无法存在了。哈姆雷特和唐·吉诃德的绝对隔离,只会充分暴露他们性格上的不足。
鲁多夫·洛克尔在他的奇特的文艺评论小册子《六人》中把不同名著的典型人物组合起来,满足人们不可遏制的探索精神。
在《六人》这本小册子里,这样两两成对的人物还有两组,都能给读者以新的启示。
一个是想避开一切尘世的事物,好叫自己的心灵免除任何负担的浮士德,一个是完全与人生溶合,处处去追求感官幸福的唐·璜。当他们分别孤立存在时,你会在他们各自的局限前踟蹰、迷茫。可是鲁多夫让他们彼此谅解了:
浮士德向唐·璜承认:
超脱肉体地追求真理是不可能的,撒旦让我看见的只是我自己的身心。认识只能认识我们自己的存在。在局限的时间、局限的存在中,要去理解无条件绝对真理所包含的一切相对真理,本身就是谬误。认识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吧,除此没有任何超脱时空的真理。
唐·璜向浮士德承认:
一切肉体的追求也只能是相对的,被时、空所限制的。每个欲望都能达到的躯体与每个欲望不能达到的躯体,腐烂后,有什么区别呢?你纵然没有得到你所渴望的理解,你的奋斗也并不是没有用处的。你的努力会成为后人世代相承的遗产,一份热烈的渴望的遗产,将来有一天精神的国土就会由它产生的。
和尚麦达尔都斯和诗人阿夫特尔丁根被鲁多夫拉到了一起。
诗人是善的精灵,他的心包容着世界,燃烧着同胞们所受到的一切苦难。可他如果不明白社会上为什么还会有和尚麦达尔都斯——人类恶的化身,他就永远不能解救他所爱着的同胞。
生产力是逐步发展的,与其相应建立的生产关系也不可能人为地制造出来。人性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性本善”论、“性本恶”论都不准确,人性深深地打着生产力水平的烙印,麦达尔都斯的“恶”,也除非是喝了魔鬼的药水引起的。意识变化的根基不在意识本身。没有把人类从恶意识中解救出来的救世主,那怕把麦达尔都斯砍上一万遍也无济于事。阶级的消亡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但革命固然可以消除生产发展的阻力,暴力却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
在和尚麦达尔都斯面前,阿夫特尔丁根的蓝色的花枯萎了。一切脱离求实精神的理想都会象那朵蓝色的花。改造这个社会的信心,不在《圣经》上,不在《福音书》上,不能幻想把麦达尔都斯们都化为圣人。世界该怎么存在就让它怎么存在吧。盼只盼诗人们的肩臂更结实一些。
社会存在本身不就是很美好的吗?谁看不到这一点,谁就不配有理想的蓝花。文艺复兴诅咒中世纪,可没有中世纪又怎么会有文艺复兴?在肯定了中世纪后再来看文艺复兴,才能理解为什么文艺复兴又融化、消失在新的时代精神中了。
在理想的光辉下,存在显出自己丑恶的一面,可包括这丑恶一面的存在都结结实实地站在那里,比未来的理想现实得多。它本身也曾是过去的理想,它比将来的理想有着更充足的在现实中存在的理由。在这一点上,将来的理想奈何不了它,只有承认它。没有理想的人,将同现存的一切一起灭亡。充满生命力的只有理想。所以在鲁多夫笔下,麦达尔都斯对诗人说:“啊,亨利希,凡是专门顾到自己的人,他的痛苦是多么地可怕,他永远感觉不到别的灵魂的温暖,永远感觉不到那个慈爱的‘大众,只有在‘大众中‘我才能够我到它自己。”
在这本小册子中,三组矛盾,六个典型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人的意识的一个完整的立体。鲁多夫在列位大师们肩臂上架起了自己的云梯,以这个六面体的精巧组合,使读者得以更深地理解这六个典型——从组合起来的完整的人性中去体验他们各自的意义。
(《六人》,〔德〕鲁多夫·洛克尔,巴金试译,三联书店一九八五年六月第一版,1.1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