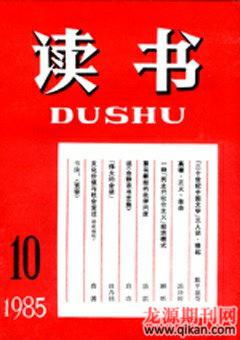读《许政扬文存》所想到的
程毅中
看到了刚出版的《许政扬文存》,在高兴之余,不禁又感慨万千。政扬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快二十年了。他在一九六六年遭迫害而辞世,留给我们的只有这一本篇幅不多的文集,还是好几位朋友煞费苦心收集起来的,真是太少了!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我辗转听到了他不幸的消息,无法表示自己的哀痛,只能默默念诵李商隐的诗句:“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
我上燕大时,他已经上研究院了。当时中文系全系只有二十儿个人,我们因此有忘年(年级)相交的机会。今天重读他的残稿,还象从前一样,给我以许多知识和启发。
政扬对宋元小说戏曲语词的研究,是化了多年心血的。尽管遗留下来的文稿不多,给我的印象是文辞委婉,立论严谨,真是文如其人。他并不是一个专攻考据(以往所谓的朴学)的学者,然而继承并发扬了清代以来不断有所发展的优良学风,竭力做到了“例不十,法不立”。他解释一个词语,一般地总要找出十来个例证,然后再下判断。当然,他在论文里并没有列举出全部的例证。只要看一下《文存》中《宋元小说戏曲语释》(三)的“香
政扬的辛勤耕耘取得了收成。他的论文有不少新的突破。例如在“三都捉事使臣”条中,对“三都”的解释提出了讨论。有人把“三都”解释为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三个部门,《语释》则从“都”字探索唐代的军队建置,一直发展到宋代,“大凡百人为都”,从而考证到宋代开封府防备盗贼的街卒,也分设营、都等编制,所以开封府的捉事使臣也可以按都分置。
“一笏、一锭”条,提出一笏究竟多少的问题。曾有人认为一笏即一镒,二十四两。《语释》引证《墨庄漫录》和《可书》所载宋徽宗赐给米芾白金十八笏的故事,得知一笏即五十两。继而考证“锭”字的起源,并不如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所说的始于元代,而是宋、金时已通行。又据《云麓漫钞》“炼银每五十两为一锭”的记载,证明一锭就等于一笏。接着又考证了元代银钞一锭,最初也相等于银一锭;钞一贯,相等于银一两。不过后来钞逐渐贬值了。弄清了这些事实,也就纠正了钱大昕的一些说法。归纳起来,才作出结论:“一笏即一锭,也就是一铤。”政扬把这个结论,写入了一九五八年出版的《古今小说》注本。一九六四年《人民日报》报道,陕西长安县发现的唐代丁课银锭,正是五十两一锭,其规制正与政扬的假设吻合。可见千载以前的名物制度,经过周密的研究,也是可以比古人弄得更清楚的。
《文存》中的《话本征时》是一篇力作,表明他从语词的考释,进而推论作品本身的年代了。《简帖和尚》,以往文学史家公认为宋代话本,主要依据就是《也是园书目》把它列为宋人词话,政扬却从话本中的一句插叙发现了问题。《简帖和尚》讲到皇甫松“叫将四个人来,是本地方所由”,作者表白说:“如今叫做连手,又叫做巡军。”政扬注意到新词“连手”、“巡军”取代了旧词“所由”的现象,考证出“所由”的名称流行于南宋之前,而“巡军”则设置于元代。还根据开封府没有左右司理院的制度,说明话本并非宋代人所作;而从其他一些细节又表明,它的诞生离开宋亡还不会太远,应该归入元人作品的行列。这是一个新的发现。以往我们以《也是园书目》作为唯一的依据,对“宋人词话”的说法深信不疑,未免有片面性。当然,政扬并没有忘记作必要的说明:“小说创作于元代这一事实并不妨碍它的题材可以来自宋时。”在这里,我也想插一句话,《简帖和尚》的题材,大致可以肯定它来自洪迈的《夷坚支志》景集卷三《王武功妻》条,那就在南宋以后。话本作为一种说话艺术的底本,在传说、传钞、传刻过程中不断有所修改,是不足为奇的。小说可能始创于南宋,到了元代或明初写定时,自然会加上一些时代的标记。这对我们区分宋元明三代的话本造成了许多困难。如果说《简帖和尚》的确切年代还可以作进一步探索的话,那么《戒指儿记》的时代特征就更为明显了。因为以商人子弟而点报驸马,只是明代才可能有的事。政扬从典章制度上找出了确凿的证明,才象老吏断狱一样下了判断:“可以得出结论:象阮华这样的商贩子弟,会去应选驸马,对宋代的人说来,是完全不能设想的。同样也可以得出结论:话本《戒指儿记》只能是明代人的手笔。”
政扬并不满足于对语词和年代的考证,也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如《论睢景臣的<高祖还乡>〔哨遍〕》也是一篇力作。他从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特征,说明其为元代现实生活的反映,而不仅是一个历史题材的演述。“作者所描写的对象,主要是现实生活,而不是历史”。通过精细的分析,挖掘出汉高祖和乡民两个形象的典型意义,比较深入地探索了《高祖还乡》艺术构思的特色。本文的某些问题当时曾引起讨论,政扬也虚心地表示过,自己“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学理论和古典文学方面,都还只刚刚起步”。然而,过了三十年之后重读这篇论文,还给人以新鲜之感,并没有使人觉得有简单化、庸俗化的毛病,尽管它决不是完美无缺的结论。《向盘与红顶子》一文对《老残游记》作了十分精辟而细致的分析,肯定地指出刘鹗的政治立场是反动的,但书中也有从生活中概括出来的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形象。刘鹗在《老残游记》里所写的三个封建官僚的形象,“显示出了自己独特的、深刻的暴露现实的力量”。政扬认为:“在《老残游记》一书中,真正激动人心的,不是刘鹗的反动的说教,而是体现在形象中的生活;并不是老残心爱的那个‘外国向盘,而是那些引起他无穷憎恨和不断的抗议的站笼、夹棍、拶子……,一句话,那个血染的红顶子。”政扬这些平允而明快的剖析,是很有说服力的。他提出的问题也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形象与思维的关系问题,当时还没有引起评论者足够的注意,而且在某些简单化、机械化的思想指导下,往往强调作家世界观的决定作用到了不适当的程度。政扬在介绍《老残游记》的一篇短文中,明确提出了形象大于思维的论点,这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
政扬对宋元时代的语言、历史、地理、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方面都作了全面的考查,因此除了小说、戏曲中的语词之外,还研究到了《清明上河图》里的桥名问题。他对画中的一座大飞桥作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三点理由,说明它并非相传所说的虹桥;又举出三点理由,说明它是汴京内城角门子外的下土桥。证据确凿,论断精密,这在中国美术史上也是一个新的发现。于此可以看出政扬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厚修养。他不仅对宋元小说戏曲有独到的研究,而且对中国文化史的许多方面以至外国的文学、艺术,都曾广泛涉猎。我还记得,他在读书读到疲倦的时候,往往翻阅一些西洋名画集之类,欣赏一下美术作品,作为精神调剂。过后,又全神贯注地钻到书里去了。他读书很广,鉴赏力很高,是我十分钦佩而又学不到的。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一书,就是他介绍我读的,他说:“读了这样的书,可以激励自己多读一些书。”今天,我读了他的《文存》,同样也产生这样的感想,可以激励自己多读一些书。《文存》所收的文章,以宋元小说戏曲的语释为主,但除了专门研究小说戏曲的同志需要参考,其他爱好中国文学的同志也不妨一读,从中也可以得到一些启发并学到一些治学的方法。
政扬平时积累了大量的笔记和资料卡片,有许多只是小纸条,在文化大破坏的一场风暴中随着他才华未尽的生命一起被毁灭了。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损失!如果不是这场浩劫,他一定会给我们留下更多几倍的成果,那怕是未曾整理的资料也好。这本《文存》里所保存的一部分成果,都是他四十岁以前做出来的。在我们这个平均寿命不断增长的国家里,当时他还是一个青年人。周汝昌同志为《文存》写的代序说:“‘文化大革命完全毁了政扬的心血(最主要的是他多年精力之所聚——惊人数量的网罗宋元一切图籍的资料卡片功夫),也毁了政扬的精神生命和生理生命。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这种损失,‘大到什么程度?我不必做出什么‘科学估量。我只想说,象政扬这样的学人,在我们这一代说来,乃是难得多见的极其宝贵的人材,一旦充分发挥了他的作用,在我们的学术史上将会焕发出异样重要的光采。”我觉得这些话并不是朋友们的私言。现在这本《文存》的价值恐怕不能以现存的篇幅来衡量,它表明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代学者曾在宋元小说戏曲的领域里进行了辛勤的开垦,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既为后来者铺垫了路基,也为青年人指引了治学的门径。
政扬的生平和学术方面的活动,汝昌同志在代序中已有了简括的叙述。我不能多作补充,只想到一点:政扬体弱多病,在学校时就经常发病,饮食极少,可是他苦学不废,真到了“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境界。后来听说他的病情日益严重,还是抱病坚持工作,以致他的身体始终不能康复。如果他在生理上能够保持健康,也许在精神上还能顶得住那次暴风骤雨的打击。因此我想到,对于忘我工作而超过自己负荷能力的同志来说,还是要爱惜自己,当然更需要社会的关心和爱护。政扬逝矣,他的学术文章还是有顽强的生命力的。
一九八五年三月
(《许政扬文存》,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第一版,1.0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