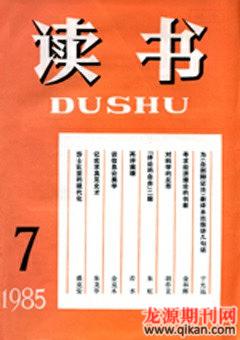谈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
东方望
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属于通俗小说,同流行歌曲一样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不过“通俗”和“流行”都是说明其读者之广;也许从所谓“接受美学”的观点来看,这是不可忽视的;若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表现,这也还是不妨试作粗略考察的吧?
不算清朝的,只作为现代的东西,不管那些《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以及《包公案》、《施公案》、《彭公案》之类,只从五四运动前几年算起。我略略回忆一下,值得提出而确实流行过的,“武侠”类可举出陆士谔、不肖生(向恺然)、还珠楼主(李寿民)以及香港的梁羽生。金庸的,内地见不到,可不算。至于《荒江女侠》虽拍过电影,也可不提,那是没有特色一闪而过的。“侦探”类有写福尔摩斯和亚森罗频的,近年才译出的克里斯蒂和松本清张的。还有些某某侦探案之类算不上流行,连亚森罗频的名声也比不上福尔摩斯。这个英国侦探的案子先译成文言,后改译为白话,解放后又有新译本,最近还加上电视连续剧,真是至今不衰。此外还有一些反间谍小说。
一排名次就可看出这两类小说虽都流行,却有一点大不相同:“武侠”是国货而“侦探”是舶来品。解放后出版过“反特”小说,也是从苏联译过来的。自己创作的始终打不响。“武侠”却象中国的武术一样“独步全球”。现在的电视剧《霍元甲》、《陈真》,出于香港,不大地道,也还是国货。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公案”为什么不能发展成为侦探小说?这个问题先让大家考虑吧。
一提到武侠小说,为什么我立刻想到这几个作者?可以查看一下。
陆士谔是上海的中医,写小说并不是他的专业,但他可以作为那一时期的同类作者的代表。他的小说题目我记不起来,内容特点却很明白。一是正当民国初年,他突出了满汉矛盾,着重写雍正时期的剑侠。雍正夺嫡,组织“血滴子”暗杀集团;由文字狱而全家被害的吕晚村的女儿吕四娘成为刺杀雍正的剑侠。二是他宣传了内功和所谓武当派。传说确有其人的甘凤池(《儒林外史》的凤四老爹)屈居雍正八侠之末,而“不见经传”的虚构人物却高居前列,显然是为了便于对内功作神奇的描写。这两个特点不但风行一时,而且到梁羽生的《武当一剑》、《七剑下天山》还写明末清初和内功剑法。因此我不能不提起开这个头的陆士谔。
向恺然曾去日本,早年署名“不肖生”写过《留东外史》,书不好却出了名。以后他写起武侠小说,大出风头。《江湖奇侠传》中的一部分故事演成电影《火烧红莲寺》,成为一种典型。另一部《近代侠义英雄传》宣传了霍元甲。这两部都是一集又一集,没有写完。这也开了写不完的连续小说之风。他写的和前人有所不同。一是他是湖南人,把湘西的“辰州符”写得神乎其神,不仅是“祝由十三科”的巫术,而且加上了神怪的成分。二是他本人和精武体育会有关系,懂武术,内功外功都写的偏于内功,写了霍元甲时期的真实加虚构的英雄侠客。他写的不是满汉的种族矛盾而是提到对外的国家矛盾了。这一点在近来的香港电视剧中还可见到。此外,他的文笔和构思也超过前人。他写的放木排的辰州“排客”和人斗法,吴大屠夫访师学艺,罗某为师报仇,“窑师傅两斗凤阳女”等故事很能吸引那时的好奇的青少年。解放初报载他进了湖南文史馆,还在讲精武体育会。
“平江不肖生”搁笔多年,张恨水占了通俗小说的头把交椅,但不写武侠。抗战结束后出现了署名“还珠楼主”的李寿民,轰动一时。他的《蜀山剑侠传》写了五十多集还未完,在上海曾编成连台戏上演。他没有继承不肖生的武术宣传,而发展了不肖生的神怪故事。他写的“蜀山剑侠”,开头并无足奇,几回以后忽然出现“绿袍怪”,从此愈出愈奇,编造了幻波池和峨嵋“开府”的大故事,再套进小情节。他同时写几部永远“未完”的长篇小说,《青城十九侠》、《长眉真人传》等。除人物繁多和情节离奇之外,他也有不同于前人的特点。一是他是四川人,延伸了不肖生的湘西巫术而大写西南少数民族巫术。二是他把“法术”现代化了。什么“空谷传声”,分明是无线电话。所写的法宝仿佛原子弹爆炸。他的有些希奇想象物可以看出是在二次大战以前想象不出的。“剑”已经不是“一道白光”了,脱离了荆轲、聂隐娘等的传统。他写的两派斗争也明显不是传统的世袭宗派斗争,有了现代的影子。解放初他还出了一本小说,写西南民族。在序中说,他听了领导文化的同志对他谈话,有所觉悟,作了自我批评。以后他便销声匿迹了。
“武侠”在大陆绝迹以后,在香港仍连绵不断。梁羽生参加了一九八五年的作协代表大会,写“武侠”的作家也得到承认了。从我所见到的他的几本小说看来,他继承了以前的一些特点而抹去了“神怪”色彩,改写成“神奇”。他注意了小说作法,企图加一些“艺术性”。他继续发挥内功胜过外功的近代传统观点。他的小说也有改为电影的,和流行的武打片中硬碰硬的“功夫”有所不同。他想突破传统的为消遣娱乐而写的束缚,但仍未能解脱出来。
从以上的约略考察可以看出,这些小说和古代的侠客描写貌似而神非,明显是随社会文化推移而有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从古到今对于武术有两种想法:一是武打,以力和术取胜;一是超出武打,以内功不战而胜,甚至由神奇到神怪。古时虽有“妙手空空儿”的故事,但到现代才大发展。这是一种趋向,也是我国的一个独特传统,讲究以柔克刚,以弱敌强,以内胜外,仿佛是精神力量超过物质力量,和外国的击剑不同。目前电影和电视中表现的是硬碰硬,不是小说中的软碰硬了。是不是又要有变化?还是退了回去?
中国的“武侠”和外国的不同。欧洲有过中世纪骑士(唐吉诃德所摹仿的),印度有过刹帝利(武士),日本也有过武士。中国始终没有形成这样的稳定的社会阶层或集团。从司马迁写《游侠列传》以后就不见有史家再写,只唐代传奇中还有一点。社会上没有职业性的武士,却有打斗的宗派和帮伙。文人、武官、盗贼、乞丐、和尚、道士、尼姑、妇女、工、农、商、庄主以至贵族、皇帝(雍正)都可以参加在内,作为侠客。专业的只有受雇于统治者或豪门的打手、保镖,那也往往出身于绿林而为侠客所鄙视。黄天霸毕竟不如窦二墩。特别的是侠女,自唐代以来有过不少,最为人所喜爱而流传。《聊斋》中也写《侠女》。《十三妹》编成戏曲。这好象是外国没有的。可以说“武侠”在中国是独树一帜的。外国的“行侠仗义”不同,若有类似的便会受到欢迎。例如司各特的书,林琴南(纾)译为《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而流行。大仲马的书伍光建也译为《侠隐记》,后来又叫《三剑客》,其实是《三个火枪手》。中国人历来心目中的英雄和外国的不同,总带些侠客之风。从前拜伦的诗为青年人读英文时所爱好,恐怕也是因为他有点侠气。不少人喜欢他的武装肖像。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一特点现代只存在于通俗小说之中?为什么现在武打片中只见宗派少见侠义呢?就过去的小说而论,写打架和打仗的似乎无论西方或东方都没有超过中国的,正象《孙子》巍然为世界战略书最高峰一样。怎么现在不行了呢?青少年从这些既不“侠”又不“武”的“武侠”能学到什么呢?
侦探小说仅靠进口,不能自己制造,那就更加奇怪。法国人编造亚森罗频也抵制不住福尔摩斯,这不是一国情况。但各国毕竟有自己的同类型小说。苏联自有其反间谍小说。日本人更发展出独具一格的推理小说,现在又出现所谓“企业悬念小说”。英、美也自有其犯罪小说,克里斯蒂的封闭式推理风靡世界。为什么中国出不来呢?翻译的侦探小说有人看,可见不是销的问题而是产的问题。也许是我们的罪案较少,难以取材;也许可以试比一比审案的不同。外国这些小说中主要写靠求证和推理去侦破罪案,着重的不是判案。中国自从汉、唐的酷吏直到清末《老残游记》写的“清官”,都是判案靠刑具和口供。包公也不过是先做点私访,判案时照旧。所谓“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和“请君入瓮”就是古代的传统。好象是欧洲重过程,中国重结果。有证,有供词,即作判断,无须推理、考核。中国哲学思想史中逻辑也自有一套,欧洲式或印度式的《墨辩》、“名家”、“因明”并不发展。流传的是判断式。判断充满了经史子集,很少追究“为什么”,着重“是什么”。印度传来的神秘主义的《金刚经》还要再三问“何以故(那是由于什么原因)?”然而“天命之谓性”,“道可道,非常道”,“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一类都是不讲道理,不查证据,说是什么,就是什么。“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口供画押就算定案,何必费事伤脑筋去查核证据推索理由?是不是这个思想习惯传统压在身上,以致五四运动以来几十年还没有彻底决裂,竟影响到侦探小说不发达?
我国第一部文学总集《诗经》的编者(挂名孔仲尼)很高明。他的诗歌分类是“风、小雅、大雅、颂”,从民间到庙堂。这一直贯到五四运动。“骚”可以说是“楚风”。第二部总集《文选》(梁昭明太子萧统挂名主编)就分类繁琐了,但还收了《奏弹刘整》,其中有口语供词。第三部总集《玉台新咏》(梁、陈徐陵奉命编)似只一类,历来被认为格调低下,坏在那篇序文,但它还收了《孔雀东南飞》和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不坏的诗。文学作品可以有高低、优劣之分,但一个类型出现了,流行了,就很难用一纸命令或一场舆论取消它。不屑道者未必不屑一看。流行的“武侠、侦探”之类作品不高,不优,也许是能写的人不写,不能写的人要写;也许是写的人不了解所写的,或则所写的不是心里所要写的。为什么编电视剧还要乞灵于《水浒》、《西游记》、《包公案》呢?那不是古代的通俗小说吗?为什么宣扬“旧道德”和“人情味”的日本电视连续剧能在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受到观众欢迎呢?是不是可以作为问题提出来,请大家思考一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