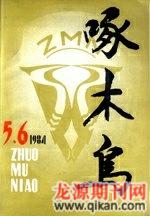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公安题材的文艺创作
仲夏的胶东海滨,海风习习,凉爽宜人。来自全国各地的四十余名作家云集烟台,参加本社举办的笔会。
为了团结广大作家,反映公安战线的斗争生活,活跃公安题材的文艺创作,本社于今年七、八月间举办烟台笔会。山东省公安厅、山东省武警总队对笔会给予了大力支持。蒋子龙、叶文玲、古华、冯苓植、白刃、航鹰、顾工、张昆华、陈屿、顾笑言、王家斌、徐本夫、邓刚、黄济人、严亭亭、晓剑、韩汝诚、中申、陈敦德、徐伟敏、李叔德、杨东明、张石山、贺晓彤、尹俊卿、周山湖、甘铁生、张廓、孙桂贞、林祁、雁宁、李迪、陈杰以及张廷竹、徐孝鱼、李杭育、楚良、李玲修、鲁光等作家和青年作者应邀参加了笔会。
笔会期间,作家们参观访问了劳改工作先进单位——山东省北墅劳改支队,有的作家还专程到山东省潍坊劳改支队和潍北劳改支队熟悉生活,同时参观了农村经济改革的先进典型——山东省牟平县西关明珠总行,笔会还组织作家就如何活跃和发展公安题材的文艺创作举行了两次座谈会,与会作家踊跃发言,发表了很多宝贵意见。(本期发表部分作家的发言。)途经济南期间,《啄木鸟》编辑部还组织了参加笔会的部分作家同山东省的作家知侠、王兆山、邱勋、张炜、高梦龄、从耸、李新民等举行了座谈会。
编者
于浩成(群众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我们邀请大家来讨论一下如何繁荣和发展公安题材的文艺创作问题。
公安部领导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前不久还专门发了文件,提出要活跃公安题材的文艺创作,并规定我们群众出版社负责公安系统的业余作者和专业作家的组织联系工作。
公安题材的文艺创作,对于向人民群众进行法制教育,提高公安干警的政治思想水平都是很重要的。而在这方面过去有不少错误的、模糊的认识。耀邦同志不久前说,现在主要的是同愚昧作斗争,而不是反所谓的什么“自由化”。我太拥护耀邦同志的话了!在同愚昧作斗争中,民主、法制、科学和文艺都是很重要的,公安题材的文艺作品也是必需的,即使是外国的侦探推理作品也不可一概否定。记得一九六二年邓小平同志有一次出差,派人到我们出版社来借《福尔摩斯探案集》,后来,“文化大革命”中这竟成了我的一条罪状,说“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为什么向你们出版社借封、资、修的东西?其实,不少外国侦探推理小说,对公安人员是有好处的,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对一般读者也没有什么害处。不允许这类作品存在是奇怪的,同样奇怪的是,这类作品禁止也是禁止不了的。《啄木鸟》一下子就发行一百八十万册,这种现象就很值得研究。《啄木鸟》是以发表公安题材的文艺作品为主,但又不限于这种题材,要保持自己的特色,但又不是单色。怎么样把《啄木鸟》办得更好,怎么样把我社的书出得更好,怎么样使公安题材的文艺创作繁荣起来,发展起来,希望大家充分发表意见。
航鹰(天津市专业女作家):
公安题材的文学作品,确实是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为什么这样多的不同层次的作家都来参加《啄木鸟》的笔会,也是由于看到了这种文学现象。我过去是搞编剧的,在写小说时,眼前就总有一种视象——坐着一排一排的观众。作家写东西时总要想到读者,时刻想到你写的这个东西,读者看了会怎么想,怎么看,会不会把你这几页翻过去不看,用戏剧行话来说叫“起堂”。
随着未来的改革,出版工作,包括编辑、创作都要发生变化,文学要适应这个变化,要研究未来的规律,完全不顾及这些是不行的。刊物心目中没有读者就很难生存,作家心目中没有读者,写谁也看不懂的东西,作品就很难流传。只有一把板斧是不行的,作家要有两把板斧、三把板斧。
现在的问题是,这类作品一般文学性较差,过于强调情节性,有些甚至是胡编乱造,不注重人物刻划,更多的是:“砰砰”两枪,一具女尸倒下,然后是摩托车驶来,发现几个破案线索,一个可怜虫被误解,然后被敌人打死,破案又陷入迷魂阵,接着又发现了新的线索,找出真正的罪犯,再来一番武打,或者是把罪犯打死,或者是逼死。人物整个淹没在情节当中。如何提高这类作品的艺术水平,我认为关键是遵循高尔基所说的“文学是人学”,应该刻划好包括公安人员和犯罪分子这两方面的人物,一定要注重写人物。其实,世界上很多文学名著都是涉及了案件方面的内容,象《复活》、《悲惨世界》、《红与黑》等,都是伟大的作品,谁也没有感觉到人物淹没在情节当中。所以,我们的作家应该也可能表现这方面的生活,写出文学性很强的作品来。
顾笑言(吉林省作家、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
据说《啄木鸟》已发行到一百八十多万册,这说明这类题材的作品是受读者欢迎的。过去社会上有一种看法,把公安题材的文艺作品当成文学中的旁门左道,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理的。有工业题材、农村题材、军事题材,为什么就不能有公安题材?为什么反映公安战线的斗争就低于其它题材?当然,我们需要在艺术上突破,要让它同工业题材、农村题材、军事题材并驾齐驱,使它在文学阵地上有一定的地位,我相信这是完全可能的,在这方面作家是大有可为的。
叶文玲(河南省专业作家、全国政协委员):
对文学作品最有发言权的,最有判断力的是群众。一个刊物,一部作品能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绝非说明它水平低下,而是说明它深受群众的喜爱。
《啄木鸟》的严肃性,在于它揭露了人民生活中低下的、卑劣的东西,啄出生活中的“害虫”。在这方面,《啄木鸟》负有其它刊物所不可能负有的使命,因此它是非常严肃的,是高档品。《啄木鸟》除了告诫生活中的不法分子以外,还提供许多美好的东西。比如第一期《啄木鸟》上的报告文学《追捕“二王”纪实》,尽管有很多人提出各种责难,提出种种的非议,但是我觉得这篇报告文学在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过程中其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它严峻地提出了生活中的问题。
有母爱的儿子是富有的,有读者的作家也是富有的,拥有广大读者的《啄木鸟》和群众出版社也是最富有的。
我现在常常感到困惑,感到写不下去了,怎样使自己适应生活的巨大变化,往往很痛苦。刚粉碎“四人帮”时,我写过去积累的生活,近来我觉得过去的生活已经不够用了,渐渐的陈旧了,而且过去的那种表现手法也不适应今天的生活了。因此我很希望通过《啄木鸟》的工作,开辟新的渠道熟悉生活,改变我以往创作上的弱点,弥补自己创作上的不足。
我愿作《啄木鸟》的热情的读者,也愿作《啄木鸟》的积极的作者。
古华(湖南省专业作家):
今年以来我写了些出访游记,小说创作则陷入一种停滞、苦恼的状态,我感到小说已经很难写下去了,越写越旧。这是我为什么要来参加《啄木鸟》的笔会的原因。
当代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节奏加快了,色彩浓烈了,我们不能不认识到生活的这种变化。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正处在上升时期,但它基本上是一种烂透了、也熟透了的贵族生活,那种生活的节奏非常缓慢。翻开那个时期的文学,所写的一个重大主题就是遗产,遗产问题本身就是反映整个贵族阶级的崩溃。
我们今天正处在蓬勃的伟大的变革时期,我们今天所讲的许多话,十年前就是反革命,就要进班房,要戴“帽子”。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节奏的加快,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对外开放有关系,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小说要是不适应这种变化了的生活节奏,再按老的一套去写,象十八、十九世纪那种缓慢的节奏,写了160多页,主人公还没有起床,读者就受不了。
恰恰是我国的古典文学节奏很快,象“三言二拍”、《水浒传》,特别是《三国演义》,八十多万字写一个世纪的战乱风云,三国时期从东汉崩溃到司马昭统一天下,群雄并举,风起云涌,节奏很快。我国的文学什么时候节奏变慢了呢?是从“五四”新文学开始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有很大成就,破除了章回体的束缚,从西方文学、苏俄文学中吸取了营养,但也带来了一个问题,节奏慢了。心理描写,静止的描写,特别是有些景物描写,虫怎么叫,露水怎么从叶子上掉下来,叶芽从地里冒出来拔节的声音,都写得很细腻。可是当代人的生活节奏、心理节奏都变了,与文学竞争的手段多了,立体声音乐,彩色电影、电视,各种舞蹈,很少有青年去啃一部几卷本的小说。人都忙起来了。为什么中篇小说盛行起来?就是因为读者的心理节奏快了,三四万字,十来万字,一口气看完。纵向看历史,横向看世界,我们还可以看看国外当代小说的情况。美国每年要评十本畅销书,这种畅销书和一般的侦探推理小说有很大区别,既有推理小说的快节奏,又有较深刻的广泛的社会内涵,二者揉合得很好。我觉得自己还写过去的那一套意思不大,想加快一点儿节奏,以尽量短的篇幅,给读者尽量多的东西,而不是抓住一点点东西,加大水分进行稀释。小说的节奏不加快就写不下去了。参加《啄木鸟》的笔会,我感到很有收获,很受教益。
蒋子龙(天津市专业作家,中国作协理事,天津市文联、作协副主席):
这两年我觉得很难,写好的写不出来,写坏的又不愿写。我曾经在故事上下了很大功夫,看了好多的作品,一开始想不要故事,我赞成这个理论,故事就象篱笆,任何作品一有故事就象跑马圈地一样,把生活圈起来了,复杂的世界,真实的世界,立体的旋转的世界,就变成一块一块的了。我很想打破故事的篱笆,故事的铁丝网,我花了一个中篇的功夫写了一个短篇,这个短篇写完以后我自己也看不懂。但是有一个编辑很欣赏,说这才是能够传之永久的经世之作。但我到现在还不敢往外拿。我发现,不要故事,我就抓不着了,无处下笔。我只好采取折中的办法,还得有一定的生活线,即使它流动,也还是有一定的渠道吧。
其次,关于写人物,我力求搞得不要雷同化,但我们写工业题材,写改革,总喜欢类型。我想到公安战线来找找,人物那么复杂,为什么到我的笔下就搞成类型?我觉得还是得写人,没有人物不行,所谓“全景小说”,我理解是把一个人写透。每一个作家都是生活的卫星,应该找到自己的轨道,找到自己的位置。公安战线天地极其广阔,我想通过这一块找到我下边写作的突破点。我曾经在蛇伤研究所蹲过,仔细观察过眼镜蛇的蜕皮。它先在一棵树或一块石头上,把嘴蹭出一个小口,然后一点儿一点儿蠕动,有时要蜕好几个小时,甚至一两天,才蜕完皮爬走了,留下了蛇皮。作家也必须不断地“蜕皮”,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但“蜕皮”非常困难,需要不断地寻找“树根”,“石头”来磨一下。
刚才有的同志提到通俗文学,我有个看法,我认为文学史向来有两部,一部是文人写的,一部是存在于读者心里的。中国的老百姓就有一部文学史,象《杨家将》、《施公案》、《济公传》、《三侠五义》,当电台一播放这些作品时,家家户户都守在收音机旁。现在国外发行量最大的也还是把文学的东西同社会、人生的东西结合得比较紧密的作品。
我觉得《啄木鸟》大有前途,还由于我们国家还没有完全走向法治,公安题材的文学作品可以对群众进行法制教育,推进我们的社会走向法治。
冯苓植(内蒙古自治区专业作家,内蒙古文联委员):
办好《啄木鸟》有个很大的好处,能改变人民群众对公安战士的形象。由于“四人帮”作祟,人们对公安战士的形象是不太美好的,通过办《啄木鸟》,就办了个大好事,可以通过文艺形式,宣传公安战线的斗争,改变人们头脑中公安战士的形象。
晓剑(北京青年作家):
公安题材的作品和整个中国文学一样,面临着突破的问题。
犯罪,破案,并不只是通俗小说描写的范畴,真正的艺术家应该勇敢地进入这块领域,透过一个犯人的灵魂,透过一个案件的表象,我们完全可以开掘出更深刻的主题。当然公安题材的范围应该扩大,应该从纯情节转化到塑造人物。
公安题材作品将以它阳春白雪的文学性,下里巴人的可读性,迅速地占领文坛的一块阵地。当然,这要靠大家共同努力,我愿在这共同努力中洒下汗水。
张昆华(云南省作家、《边疆文艺》副主编):
《啄木鸟》虽然是个新办的刊物,才出了几期,发行量便猛增至一百八十多万册。这在当前许多刊物印数不断下跌的情况下,异军突起,确实是令人高兴的现象。究其原因,我想,大概是由于你们做好了两个方面的团结工作。
第一,通过刊物,广泛地团结了作家。从这次参加烟台笔会的作家来看,不但有老作家,中年作家,还有青年作家;不但有知名作家,还有不太知名的作家;从地区上看,从京、津到华东,从东北到西南,从内蒙到湖北,从湖南到山西……几乎全国绝大多数省、市都有作家来了,这些作家写作的题材和风格,也比较多样。
第二,通过刊物,广泛地团结了读者。《啄木鸟》既注意保持以公安、政法题材作品为主的特色,又注意发表各种题材的作品;既注意发表有较高水平的文学作品,又注意发表通俗文学作品,力求做到雅俗共赏,这就使你们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办刊物,是给人看的。没有人看,或很少有人看的刊物,影响就小得多。
你们是群众出版社,你们有群众;第一有作家群众;第二有读者群众。有这两方面的群众支持,刊物就会越办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