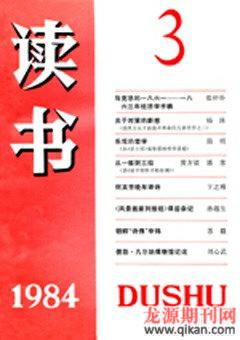孙文本和《社会学原理》
陈树德 丁 聪
提起孙本文先生,今天的读书界或许已经有些陌生了。当今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克尔斯在他的《社会学是什么?》一书中,就曾论及孙本文博士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是《社会学原理》等重要论文的著作者”。作为一位西方的社会学家,英克尔斯对孙先生的评述是有其倾向性的,这一点自不待言。不过通过他的评述,倒可以使我们知道,尽管孙先生已经去世,他却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社会学家。这里,想就孙先生及其《社会学原理》作一点介绍,谈一点粗浅的看法。因为,若要编著中国社会学史,那么孙先生及其这部最能表现其学术思想的著作,是不能不涉及到的。
一
孙本文,号时哲(一八九一——一九七九),江苏吴江人。他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一年,即一九一八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是年即到南京高等师范附中担任国文教员。一九二一年,孙先生赴美留学,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伊利诺大学、纽约大学主修社会学,兼修经济学和教育学。一九二六年,他获纽约大学哲学博士后回国,在复旦大学教授社会学。从一九二九年起,他主要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讲授社会学,并长期兼任该校社会学系主任、中国社会学社理事长,直至南京解放,整整二十年。
孙先生早年学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学,又长期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在解放前出版的十余种论著,在理论上沿袭欧美社会学,为唯心史观和资产阶级偏见所囿,乃属难以避免。在这些著作中,《社会学原理》是其中最有代表性、最有社会影响的一部著作。之所以这样说,一则是因为这部综合学派的社会学著作是集资产阶级社会学原理之大成而撰成,二则它从一九三五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迄至解放前夕止,重版达十一次之多,在当时学术界有过广泛的影响。
《社会学原理》初版时为五编二十六章,一九四○年被采为部定大学用书后,作者曾加以修订、增删,将原书第十九章分为两章,易名为“社团组织及社区组织”,并新增第二十一章“阶级组织”。一九四四年九月新版的《社会学原理》共为五编二十八章,首为总论,依次为社会因素的分析、社会过程论、社会组织与社会控制论、社会变迁与社会进步论,不仅讨论社会行为现象如何形成,如何表现,如何约束控制,如何变迁等问题,而且还包括了其它各学派的论点和学说,如态度论、人性论、人格论、文化累积论、文化遗失论、文化选择论,以及地理因素论、生物因素论、心理因素论、文化因素论,即所谓四因素论。
当时的欧美社会学,依孙先生后来的划分,可分为五个学派,即生物学派(包括社会有机论、种族决定论、优生论、人口论),地境学派(包括地理环境决定论、人类地境学、农村社会学、都市社会学),心理学派(包括模仿论、同类意识论、社会势力论、群众心理论、本能论),文化学派(包括文化社会学、民族社会学、比较社会学),综合学派。这些学派对旧中国社会学界均有着广泛影响,学者们按他们的师承关系和专长分属这些学派,孙先生自己则属于综合学派的,即综合主要各派的论点组成一个体系来研究社会现象的。
《社会学原理》的重点所在,据作者说,系介绍“欧美社会学上最新思想”,即文化学派的社会学,“注重文化与态度之讨论”(凡不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社会学原理》一书)。这种介绍和移植工作,早在一九二七年出版的《社会学上之文化论》和一九二八年出版的《社会学ABC》中就已开始,特别是作为《社会学原理》雏形的《社会学ABC》一书,更着力对“文化与态度二概念”的分析,而在《社会学原理》中则用文化和态度二因素去详尽解释社会现象。“文化与态度的交互作用,乃产生种种社会现象。文化固然常受态度的影响,而态度也常受文化的影响,二者互为因果,不能分离。”这种学术思想甚至反映在他的专著中,如他在《人口论ABC》中就认为:“人口品质问题,除身体特质外,关于精神特质,实际只是文化问题。”(见该书第112—113页)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又因袭了欧美社会学的传统说法,孙先生当时只能用他的唯心主义的文化观点来具体解释社会问题和探求社会出路。他认为,“欲从经济要素方面下手,改造社会”,是有缺点的,不圆满的;而“欲改造社会,即在改造文化。”这种忽视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恰是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通病。
毋庸讳言,孙先生的这种观点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相背离的,但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态度,却还需要我们进行具体分析。在《社会学原理》一书中,孙先生曾大胆宣称:“我人并不反对研究社会主义”,“我人并不反对研究唯物史观”。尽管孙先生当时实际赞成的还是资产阶级社会学,但是,至少那种赞成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还是可取的。其次,孙先生把唯物史观当作一个学术研究的课题提出,正象欧美社会学把马克思主义纳入社会学的一个流派——经济学派一样。孙先生据此还认为,唯物史观与文化学说有着密切关系,“也能帮助我们认识和发现社会问题”,同时,他对于马克思学说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亦有较深的理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说和阶级斗争说,竭力为无产阶级张目。劳动者遂视马克思学说为天经地义。”(《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二十一号)更为重要的是,在国民党实行反革命高压统治的年代里,孙先生却敢于写道:“马克思不仅是一位社会思想家,而且是一位社会革命家。……氏之生平,迭遭放逐;生活困苦,直至于死。”“马氏(即马克思——引者注)重视经济因素,深嫉资本主义,以实行的精神,领导革命运动,其人格殊足感后人。故其思想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几已影响全世界。甚至如苏联,竟以其理论为实行革命的指导原则。”(《社会思想》第172、176页,商务印书馆一九四七年三月出版)旧中国的社会学界研究唯物史观者不乏其人,例如索罗金的《当代社会学学说》一书中译本的译者、社会学家黄文山(凌霜)也曾自称是唯物史观的研究者,但他却在研究的幌子下,对马克思主义施以别有用心的攻击。他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实际上是为国民党反动统治服务的。与此有别,孙先生却是正直的学者,他虽然主张资产阶级文化学说,而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改造的理论”,但是,他和黄文山这一类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毕竟是不一样的。
二
尽管孙先生在解放前一度(一九三○——一九三一)担任过高等教育司司长,但他仍不失为一位爱国的学者,进步的教授。早在解放前,孙先生对中国共产党就有着一定的认识,并积极支持子女参加革命活动。他的第二个儿子孙世英同志曾和蒋南翔等同志一起参与领导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以后又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南京解放前夕,孙先生被教职员工一致推选为中央大学护校委员会主席,对保护学校、迎接解放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解放以后,孙先生一直在南京大学任教,早先在地理系讲授统计学和国民经济计划课程,嗣后调任政治系(后改称哲学系)教授,开设“资产阶级社会学批判”等课程,编写了诸如《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批判》、《现代西方哲学流派》、《论我国的人口计划》(未完成),以及统计学和国民经济计划等方面的大学教材,他还承担了《辞海》的社会学词目的主要编写工作,授课之余则从事翻译工作。孙先生热爱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一步一个脚印地为党的教育事业尽心尽责。他对社会活动和工作也很热心。他是九三学社社员,又历任江苏省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四届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理事、南京经济学会理事和副会长。
建国以后,孙先生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自己过去的学术思想也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在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中堪称楷模。他说:“我个人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学曾经长期钻研过,但是,当我初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发见了这一学科的阶级性,抛去这旧的学术思想,不仅没有丝毫爱惜,而且觉得‘悔之恨晚”。(《学术月刊》一九五七年第四期第36页)他从一九五六年起迄至一九六二年,在报刊上陆续发表了诸如《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思想内容及其对旧中国的影响》、《关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理论的本质和内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概观》等论文,表明他对资产阶级社会学完全崭新的态度。
正如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孙先生对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批判可谓淋漓尽致,鞭辟入里。他的这些文章,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起源、基本特点、主要派别,以及在旧中国所起的作用上一一作了严肃认真的分析。孙先生又把批判的重点放在二十世纪初的社会学,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上。他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学在本质上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它是从唯心主义观点来解释社会现象的,即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它力图避免讨论社会经济基础的重要性和它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只注意社会生活中的非本质问题,力图回避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本质问题。它企图抹煞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存在,过分强调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无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并否认社会发展过程在它每一具体阶段上的完整性。因为资产阶级运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所以它不是从社会现象的本质和全面出发,不是从社会联系的观点,从社会发展是量变到质变转化的观点出发。
一九五八年,孙先生还在《哲学研究》上撰文,对自己的旧著《社会学原理》进行了剖析。他在文章中着重指出,这本书显著的缺点之一,“是它的唯心主义观点”,表现在:不承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看不到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宣扬社会和社会的发展是地境、生物、心理、文化等四大因素机械作用的结果,尤其强调文化是社会成立的基本因素,“无文化即无社会”。今天看来,这些分析和自我批评大体上也还是正确的。当然,这并不排斥我们来发掘《社会学原理》一书中对我们还有启迪之处。
三
《社会学原理》一书出版迄今,已经将近五十年了。尽管作为一部旧著,它存在前述根本性的缺陷,但并非一无足取。该书中的某些观点,今天还可以为我们提供启迪,仅从资料角度看,它也具有不应忽视的参考价值。
孙先生在该书中所提倡的社会研究法,蕴含着一些自发的唯物辩证的合理成分。他在科学研究最基本的步骤上提倡“搜罗、分析与综合”的方法,认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二者不能偏废,因为定量分析“能以极简单的数字,表明极复杂的状况;能以极简要的数量,表明范围极广大的事状;能以极简明的图表,指示事实的趋势。”但有些社会行为和社会状况,“决非就是量的分析能得其真相。”所以他特别强调观察法、调查法(包括社会调查和个案研究)、统计法、历史法、实验法等基本的社会研究法的综合运用。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见解。
孙先生很早就提出了实行生育限制,控制人口增长,以建立适度人口的主张,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早在二十年代,他就认为,生育限制(广义而言应包括节制和避孕),“是最合乎人道的限制人口增加的方法。”(《人口论ABC》第55页)在《社会学原理》一书中他又呼吁“中国当然需要一种适度的人口”。由于旧中国对于粮食、耕地,以及人口增加的趋势没有一套完备的统计数字,所以“适度人口”长期以来得不到确切的数字。直到解放以后的一九五七年,孙先生经过对我国的人口增长情况、人口与生活资料问题、人口与就业问题等课题的综合研究后指出:“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之末即一九六七年时,全国人口将达七亿七千万,是可能而且适宜的。以后社会主义事业日益发展,工农业生产及生活资料日益提高,八亿人口以内,全国人民一定可以生活很好。所以,我认为,八亿人口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他不仅对此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并满怀信心地说:“如果我们有计划地实行控制生育,一定可以控制人口的增长。”(见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文汇报》)
《社会学原理》一书还表现了孙先生实事求是和独立思考的精神。例如对地理学派的社会思想家过分重视地理环境的影响而忽略其它各种影响,他就提出了异议,认为“地理环境的影响,不是无限制的;它不是决定人类社会生活的唯一根本条件;它不过对于人类社会生活发生相对的关系而已。”并进而指出:“地理环境的影响,随人类社会的进步而渐渐减弱了。”
此外,这部著作因其对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各种学说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整理,“使社会学全部知识,成为一有机的体系”,这样就为我们今天研究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发展史提供了方便;而它所引用的丰富而翔实的本国材料,包括历史事实、统计资料,以及著名学者如蔡元培、梁启超、许德珩、竺可桢、郭沫若等人的研究成果,更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社会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社会学原理》,孙本文著,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五年第一版)